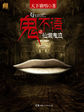这以后,焦华、潘惠英一反常态,在自己的男人或妻子面前变了样子。焦华回家时间多了,对刁秀英温柔体贴,焦妻以为丈夫回心转意,自然十分高兴。潘惠英对鲁茫百依百顺,鲁茫也给了一定回报,虽然时有打骂,但不像以前那样凶狠。潘惠英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吃了苦头找焦华诉苦,焦华尽量抚慰,她倒也勉强撑得过去……焦华本来喜欢读侦探小说,对谋杀案的过程过去就有一些了解。他去县上出差时又买了一些登载谋杀内容的刊物,研究推敲各种谋杀的细节,开始加紧谋杀的准备。
……
省市县的人喜出望外——潘惠英的口供不仅印证了他们的判断,交代了她和焦华杀害鲁茫、袁旺的情况,还说出了他们俩另外的犯罪事实。
他们压根就没想到过案情竟会这样扑朔迷离,意外的收获使刘桦等人欣喜若狂。
这场审讯结束,潘惠英被秘密关押在乡上。
刘副市长压住心头狂喜,叫来王鹏举等人,马上部署下一步工作方案,他指示:“一、立即搜查潘惠英宿舍,目前不要拘泥于什么搜查手续,慢慢腾腾必然贻误战机;二、立即拘捕焦华,要把他引出县城抓捕,抓捕后迅速进行突审,迫使其尽快招供;三、此案的侦破工作,仍须秘密进行,水落石出之前,尽量减少干扰和震动。”
王鹏举和省上两位专家点头连连赞成。
搜查潘惠英的宿舍前,张煌、胡维召集卫生院全体人员开会,提出了配合工作保守秘密的要求。搜查时首先封锁了鲁茫、袁旺住的那层楼道。搜查非常仔细,按照潘惠英交代的情况,对房间重点部位的任何一个可疑痕迹都反复勘察,终于在靠墙的那方的床方上发现了一丁点残留的血迹——这证明了金明判断的正确,潘惠英的家,才是杀害鲁茫的第一现场。
刘桦等人搜查潘惠英寝室的同时,张煌电话通知焦华,诈称其父病重,要他马上赶回千山。刚领了先进奖的焦华,接到乡党委书记电话后,心里虽然有过一番犹疑,却又不能不信。他万万没有想到潘惠英已经就范,警察已经取得一定证据。县计生办听说焦华父亲病重,主任亲自给他派了专车。焦华乘车过了小寨,便被罗霄等人截住,搜出随身携带的匕首。焦华自知事情败露,与警察挣扎了一番,被罗霄等人狠狠揍了一顿,就地连夜突审焦华,焦华只得详细交代了犯罪的全部过程……第二十八章1990年1月25日深夜两点,千山乡米乌村,焦华家的房屋突然发出一声巨响……此时,距焦家不到百米的路上,一条黑影迅速往千山方向移动。这人将手中的打火机使力甩下坡去。这个飞奔着的人,10多分钟以前,悄悄摸到焦华家房子后面的阳沟里,左顾右盼之后,在焦家房子的左角排放好炸药雷管,打燃火机,将一截长长的引线点燃,看到引线冒出的火花,确信引线不会熄火后,才反身上路飞跑……此时,这个人心里想:明天早上,乡上将得到报告:千山乡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焦华的房屋被炸了!他脸上浮起得意的冷凄笑容,嘴里骂道:“这个贱妇,与你好说歹说,你就是不干,逼得老子不得不来这一招了!”
这个人是焦华,他炸了自家的房子。
前不久,焦华与其妻刁秀英商谈离婚,遭到刁秀英拒绝后,在潘惠英极力怂恿下,他下决心除掉刁氏。俩人开始周密设计各种谋杀的方案,分析了其中的细节和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
到底用哪种方法把握大风险小,他们作了多次讨论。
潘惠英最先想到的是山村传统的谋杀方法,她建议说:“焦华,你可以想办法把刁秀英骗到山上,趁她不备,把她从悬崖上推下去,造成那个婆娘不慎摔崖的假象。”
焦华毫不迟疑地否决了这个意见:“潘惠英,你想得太简单了。干这种事,必须慎之又慎,我们不能犯低级错误,任何一点纰漏都可能招致灭顶之灾!这个办法要不得。”
潘惠英似乎没有听懂焦华话中的意思,疑惑地问:“这怎会犯低级错误呢?”
焦华解释说:“你想过没有,农村人山上摔崖死的也有,但我在场就不行。本来我就很少回家,从没与刁秀英一起上过山,现在提出与她上山,那个婆娘肯定问我怎么想转了,要约她一起上山,我怎么回答?上山是看风景,还是要去找柴烧?她如果要把娃娃一起带去,我有什么理由来拒绝。如果她起了疑心,岂不要打草惊蛇!况且,把她推下崖去,固然干净利落,但人命关天,就不能不向公安报案,警察寻根问底,我有多少理由可以解释。只要留下任何一丝破绽,必然牵出我来,事情败露的可能性极大。”
潘惠英撩着头发说:“你这样分析,我觉得这个办法是不行。焦华,还有一个办法,你看行不行?”
焦华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潘惠英——你还能有什么妙计?
他便不以为然地问:“还有哪样办法,你说说看?”
潘惠英手抠着后脑,眨着眼睛说:“焦华,我可以搞些安眠药。你拿回去,悄悄放到刁秀英的水杯里,让她睡了就不会醒过来。”
焦华摇头说:“惠英,你是医生,搞安眠药当然容易,让我老婆这样死了,舒舒服服不痛不哼,倒也比较文明。但是,我看你是吃皇粮多年,把脑壳吃昏了。”
潘惠英受了讥讽,不高兴地问:“我咋个吃皇粮把脑壳吃昏了?”
焦华嘿嘿笑了,说:“你我都是农村里出来的人,你难道忘了,这乡坝头,哪家会像城里人一样,人人都有一个专用水杯?我家里的人,除了我爹,有时会煨水熬茶外,其他人,个个都习惯喝冷水,口渴了,拿起水瓢往水缸头舀冷水喝。要吃药才喝开水。用安眠药这是个背时主意。放到水杯里,假如刁秀英没喝,阴错阳差,倒是我妈,或者我那两个娃儿抬着喝了,后果简直不堪设想,这个办法要不得。”
潘惠英不停地眨眼,自言自语地说:“吃药?吃药?”
焦华不知她又在想啥法子,只顾盯着她看。
潘惠英说:“焦华,说到吃药,使我又想起一个办法。”
焦华不屑地问:“又有哪样办法?”
潘惠英说:“可不可以把敌敌畏装进糖浆瓶子?”
“敌敌畏装进糖浆瓶子?”焦华把眼睛睁得大大的,盯着潘惠英。
潘惠英抿着嘴笑。
焦华也笑了,说:“这个办法妙,你具体说说怎么个弄法。”
潘惠英说:“你不会哄?好好款待人家一回嘛,做那事时,一定要把她弄感冒了。着了凉的人,鼻塞口干,嗅觉不灵,你多哄着她点,把敌敌畏当成止咳糖浆喝下去。”
潘惠英说罢,自己的脸兀自红了。
焦华哈哈大笑,拧了潘惠英屁股一把,说:“宝贝儿,你够宽宏大量的嘛。”
“人家是说真的。”潘惠英脸上似笑非笑。
焦华说:“仔细想想,这个办法还是不行。”
潘惠英说:“为啥子不行呢?”
焦华说:“我那个婆娘喝敌敌畏死了,死了人,警察还是要过问。他们一定要提出疑问,敌敌畏是谁买来的?为什么不放在安全的地方?这一连串的问题,我能搪塞得过去吗?这岂不要自我暴露!”
潘惠英用手指戳了焦华的额头一下,说道:“焦华,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农村里,敌敌畏拌炒饭是拿来闹耗子的,哪家不会备放一点在家头?你不会搞几个形状相同的糖浆瓶子,一个瓶子装敌敌畏,其他几个瓶子装糖浆。把装敌敌畏的那个瓶子,放到床头附近随手就能拿得到的地方。得了感冒的人,吃了也是误吃,完全说得过去的呀。这几年,我们医院,年年都有喝敌敌畏送来抢救的,其中也有喝错了的,一些人就没抢救过来,哪个过问过?”
焦华抠着头说:“乖乖,还是你聪明。”
潘惠英得意地笑了,哧哧地说:“还不是你教的,把你家那只黄脸耗子闹了,你才安逸呢。”
焦华露出愁容,说道:“惠英,你还是疏忽了,这些年闹耗子,有专门的耗子药,哪个兴用敌敌畏拌饭,老鼠根本不吃。况且,我家喂得有猫,还买敌敌畏来闹耗子,猫拿来吃素?这说不过去。”
潘惠英说:“你是咋个了?前怕狼后怕虎的,就算敌敌畏不是闹耗子的,还是一种农药嘛。”
焦华说:“说是农药,倒是正行。我爹有时也买些放在家里,但他是千交代,万叮嘱,怕我两个娃儿拿错。我看行,就这样试试看吧。”
焦华果然依照潘惠英之计,买了几瓶止咳糖浆,其中一瓶糖浆倒了一半留了一半,把敌敌畏倒进这个瓶子装满搅匀。然后请了几天事假回家,将几瓶止咳糖浆搁到柜子里,悄悄把剩下那瓶拌有敌敌畏的糖浆瓶子放到床下。当天晚上,焦华夫妇把两个娃儿撵了与爷爷、奶奶睡,他竭尽丈夫之能,把婆娘狠狠折腾搓磨了半个晚上。刁氏不知是计,难得丈夫一番美意,竭力奉迎。俩人做事时,焦华故意把被子蹬开了,他俩还滚到地上去了。果然到了下半夜,刁氏便开始咳嗽起来。天刚亮,焦华顺手摸到那瓶敌敌畏,搁在床边柜子上,便起床摸到堂屋做事,眼睛随时瞭着刁氏那间屋。刁秀英也很快起床,大声咳嗽。
焦华心里暗暗高兴,大为佩服潘惠英。
看见刁秀英伸手抓起了柜子上那个瓶子,焦华暗暗高兴,心想她中计了。哪知婆娘瞄了几眼又放下了,红着眼睛咳着走出屋来。
焦华眯着眼睛问了一声:“生病了?”
刁氏脸红了,微微笑着说:“都怪你。”
焦华有些着急,不该说的话竟脱口而出:“柜子上有瓶止咳糖浆,喝点就不咳了。”
他说罢,心里竟有些后悔,万一被刁氏识破,如何得了?
刁秀英恹恹说:“喝不成,那个东西味道不好喝,往回喝了就觉得反胃,这小病小痛,挨一会儿就好了。”
焦华点头,眼睛眨了几下说:“倒也是,你注意多休息,这两天,少做点事。”
刁氏用感激的眼光看了焦华,焦华却把惶惑的目光投到地上。刁氏便去了茅厕。焦华几个大步蹿进房间,拿了柜子上那个敌敌畏瓶子,放进了自己的挎包,回到了堂屋……回到乡上,焦华把情况与潘惠英说了,潘惠英一脸沮丧。
焦华摸着她的脸说:“你不要急,我相信一定还有办法。”
潘惠英噘着嘴说:“我看你究竟还有什么办法?”
焦华不停地挠头发,往后挠几把,又按着头发再往前抹一把。挠着挠着,突然拍了脑袋一下,眼睛盯住潘惠英,说:“有了。”
潘惠英急切地问:“焦华,究竟有哪样办法,赶快说,急死我了。”
焦华抿嘴笑了说:“看你这个样子,心头就像猫儿抓的一样,不要急嘛。”
“快一点,不要卖关子了。”潘惠英说着,吻了焦华面额一口。
焦华伸手摸额头,顺着抹到右脸再抹到下巴,伸开手掌,抖着说:“惠英,我搞的这种工作,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最得罪人。我们计生干部,年年都有些人遭到报复。每年突击手术期间,或者过年过节,一些计生干部家里不是猪被偷了,就是牛被盗了。好多计生干部不得已,在猪、牛的脖颈上拴上铃铛,铃铛一响,晓得是有人来偷牛盗猪……”
潘惠英说:“乡坝头防止盗牛盗马盗猪,在牲口脖子上拴铃铛的嘛,多得很嘛,这个与整死那个黄脸婆有啥子关系?”
焦华嘿嘿地笑了两声,说:“你不要忙嘛,我话都没说完呢。这些年,年年都有爆炸计生干部房屋的。你想想,我这些年也不知得罪了多少人,说不定哪一天,我家房子也遭人炸一回,干脆就自己炸一次吧。”
潘惠英眼睛一亮,说:“这倒是一个再好不过的主意。”
俩人哈哈笑了起来,温存抚弄了一番……
焦华急于要找到爆炸物品,他没花多少脑筋,就找到了办法。
冬季,农村总有一些农田水利基本建设。焦华寻机到各个工地转悠。他的人缘好,谁也不会想到这个平时和气工作认真的人是偷东西的贼。焦华好几次趁人不备,偷了炸药雷管悄悄放回宿舍。一个工地少一点炸药雷管,人们都没有数,焦华的行为自然没被发现,慢慢地就积攒了足够的炸药雷管。乡上计划生育手术突击工作结束后,焦华请了几天假,回家去料理家务。他给他爹说:“爹,我家房子也起了好多年了。这些年,一天到晚忙工作,也顾不上家里的房子,今年雨天,娃娃他妈住的那间就有些漏雨,我想趁着雨季没来,干脆把房子屋顶的瓦翻他一遍。”
他爹说:“焦华,家里的事你从来不管。你是咋个想转了,想起要翻房顶。我早就有这个想法了。前不久,看你工作太忙,就没提这个事,现在,你想起来嘛,就抓紧干嘛。”
焦华买了一些瓦,请人背回家,亲戚帮忙将焦家房顶翻了一遍。
焦华又给媳妇商量:“他妈,两个娃娃也逐渐大了,现在还与你睡一床,长期这样,恐怕对娃娃也不好。”
“习惯了,有啥子不好的?”焦华媳妇不以为然。
焦华说:“也不方便嘛。”
刁氏红了脸,嗔怪说:“焦华,你是爬在磨盘头睡瞌睡——想转了不是?你咋个想起做这个事了,你想想,除了这一个多月,一年到头,你回家来睡过几次?两个娃儿挨我睡一床,给我打个伴也好嘛。”
焦华用手搂了媳妇肩膀,脸贴着脸地说:“过去的事就不提了,你同意,我就找人给娃娃做一张床。你晚上怕嘛,娃娃的床就摆在我俩这个房间嘛。”
媳妇从来没享受过这样的待遇,脸上一阵热辣,把焦华的手从肩头上拿下来,脸稍稍离开一些,甜甜地说:“焦华,大白老天的,你在干啥子?娃娃看到也不好。”
焦华笑了,笑得有些莫名其妙。
媳妇又说:“两个娃娃从小到大,都挨我睡一屋。我有啥子怕的?又不是黄花闺女,一个老婆娘怕啥子?只是不睡一屋,黑灯瞎火的,怕吓着娃儿。睡一屋嘛,也好照应他们。”
媳妇应诺,焦华心里高兴,说:“好喽,就这样办。晚上,娃娃有啥响声,你辛苦点,起来看啊。一定不要再将就娃娃,习惯了就好了。”
焦华让人打了一张新床,放在房间里刁氏那张床的对面。他又寻思:自己潜回来实施爆炸,尽管是主人回家,家里那只叫“黄黄”的狗,肯定要打响声,无论如何要处置这只狗。
他试探着他爹的口气,说:“爹,县上最近说,偷牛盗马的多得很,主要针对计生干部。我看‘黄黄’已经衰了,打了呢舍不得,家里真要有事,它又抵不住。”
焦华爹说:“打?我倒是舍不得,给我做了恁多年的伴。打了,打个响声的都没有了。”
焦华说:“就是看你与‘黄黄’有感情,我才舍不得打。防偷防盗,还得另找一条。我可以与人换一条大点的。”
爹说:“哪个弄个憨,会愿意换给你?”
焦华说:“我有个朋友,答应换。”
爹说:“那就快点换回来啊,没条狗打响声,不习惯。”
焦华说:“行,爹,我会早点给你牵一条壮的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