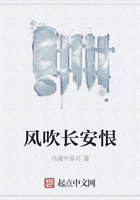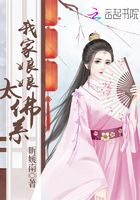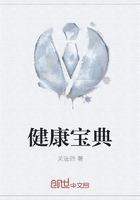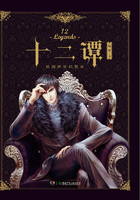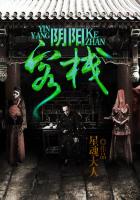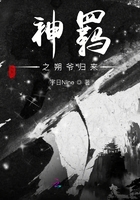元璋平东吴后,大体上据有现在的湖北、湖南、河南东南部、江西、安徽、江苏和浙江,包括长江的中游和下游,是全国最富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凭着这一强大实力,他要完成一统天下的伟业。
当时的形势是:南方则有以四川为中心的夏国明升,云南有元宗室梁王镇守,两广有元右丞何真,福建的陈友定也效忠元室,浙东还有方国珍的割据势力。北方则山东是黄军王宣的防地;河南属扩廓帖木儿;关内陇右则有李思齐、张良弼诸军;孛罗帖木儿一军镇大同。扩廓帖木儿和李、张二将不和,孛罗帖木儿又和扩廓帖木儿对立。军阀的内战又与元朝宫廷的矛盾纠缠在一起,元朝统治阶级分裂成两个互相倾轧、残杀的集团,争杀得异常热闹,造成“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
元璋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展开南征北伐。平江快要攻克的时候,也已派参政朱亮祖率浙东马步舟师攻方国珍。11月2日,又命汤和为征南将军,吴祯为副将军,率军攻方国珍于庆元(宁波)。
同时,元璋和刘基仔细商定了北伐的计划。11月9日,元璋与诸将议北伐。常遇春提议直捣大都,以我百战的精兵消灭元朝的疲卒,必胜无疑。攻下大都后,以破竹之势,分兵扫荡,其余城池可以不战而下。
元璋的计划正好相反。他指出,直接攻打大都是危险的。大都是元朝经营了上百年的都城,防御工事一定很坚固。假使我孤军深入,一时攻打不下,屯兵于坚城之下,后边的粮饷接济不上,元朝的援兵从四面八方赶到,我军进退不得,岂不坏事。不如用斫树的法子,先去枝叶,再挖老根,先取山东,撤掉大都的屏风;回师下河南,剪断它的羽翼;进据潼关,占领它的门户,东南西三方面的军事要点都在我军手里了,再进围大都,那时元朝政府势孤援绝,大都自然不战可取。大都既下,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都可席卷而下。诸将听了,都同声说好。
北伐军统帅部的组织,也经过慎重研究,选择最优秀的大将组成。徐达用兵持重,不打无把握之仗,行军有纪律,尤其重要的是他小心谨慎,叫做什么就做什么,靠得住,放得下心,任为征虏大将军,统帅全军。常遇春当百万之众,勇敢先登,摧锋陷阵,所向披靡,任为副将军。元璋担心他健斗轻敌,特别约束告诫,如大敌当前,以遇春作先锋,和参将冯胜分左右翼,将精锐进击。右丞薛显、参将傅友德勇冠诸军,各领一军,使当一面。大将军专主中军,责在运筹决胜,策励诸将,不可轻动。
元璋又再三申明纪律,告谕将士,这次北伐的目的不仅仅是攻城略地,重要的是要平定中原,削平祸乱,推翻元朝这个坏政府,解除人民痛苦,安定人民生活。
为了使北方人民明白大军北伐的道理,解除北方官僚地主对红巾军恐惧疑忌的心理,瓦解元军的斗志,发檄文谕告北方人民。檄文中提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的口号。同时又提出:“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民抚养无异。”
13日,北伐军挺进中原。同日,元璋又派部队攻福建、取广西。
2个月后,元璋军已取山东、平方国珍,进取福建,北伐南征都是势如破竹。一片捷报声,使应天的文武臣僚欢天喜地,估计统一全国已指日可待。为了适应新的局面,必须建立全国性的统治政权。由历史的经验看,王只是局部的统治者,全国性的统治者应该称皇帝,因此,吴王应该改称皇帝,王府臣僚自然也就提升一级作新皇朝的将相了。
一切的礼仪都已议好,良辰吉日也由善观天象的刘基选定了。于是,1368年的1月23日(农历正月初四),朱元璋告祀天地,即皇帝位于南郊,丞相李善长率百官和都民耆老拜贺舞蹈,三呼万岁,礼成。具皇帝卤簿仪仗威仪导从,到太庙追尊四代,再祭告社稷。然后皇帝服衮冕,在奉天殿受百官朝贺,这样就算成为合法的正统的皇帝了。
这一天,日朗风和,没有一点异样的天象,看来上天也批准了。
皇帝办公的正殿名为奉天殿,皇帝诏书的开头规定用“奉天承运”四字,表示元璋是奉天而兴的。定国号曰大明,建元洪武。以应天为京师。
大明的国号有两重的意义:一方面,它符合弥勒教明王出世的教义,让造反的农民知道明王已经出世了,好好做新朝的顺民;另方面,它又符合地主儒生的观念,是阳、火、正统、光明的象征。
新皇朝呈现出蓬勃的生机。
同年2月,南征军执陈友定,平福建。3月,何真接到廖永忠的招降书后即奉表迎降,广东平。7月,广西平。
北伐按计划顺利推进。9月10日,明军入通州,元顺帝夜半开大都健德门,由居庸关逃至和林。14日,明师入大都,元朝亡。
1371年(洪武四年),明军入川,夏主明升降,四川平。1381年(洪武十四年),傅友德率军入云南,次年凯旋,云南平。1387年(洪武二十年),冯胜、傅友德、蓝玉攻辽东元朝残将纳哈出,纳哈出势穷而降,金山平,全国重归一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