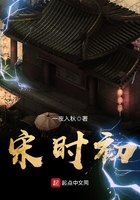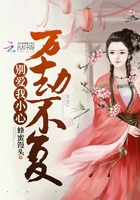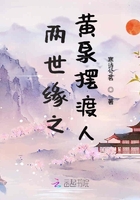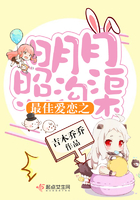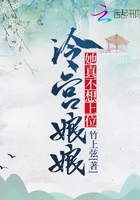稳健务实是仁宣政治的显著特征。
外交上,这一时期的明朝政府放弃了永乐时好大喜功的政策。朱棣发兵征交阯,派郑和下西洋,五伐蒙古,营建北京宫殿陵寝,已将明朝财政弄到崩溃的边缘。1421年(永乐十九年)冬,朱棣计划大征沙漠,命户部尚书夏原吉与礼部尚书吕震、兵部尚书方宾、工部尚书吴中等人商议具体的安排。大家认为不应该出兵。朱棣召问方宾,方宾力言军兴费乏,朱棣很不高兴。又召问夏原吉。夏原吉说:“近年师出无功,军马储蓄十丧八九,灾眚迭作,内外俱疲。况圣躬少安,尚须调护,乞遣将往征,勿劳车驾。”朱棣听了大发雷霆,立即命令夏原吉到开平管理粮储。朱棣又召问吴中,听到的言论如出一辙,益发怒不可遏,将夏原吉和曾经署理户部尚书的大理寺丞邹师颜一并逮捕下狱。方宾恐惧自杀。朱棣死后,仁宗把夏原吉从狱中放了出来。夏原吉建议赈济饥民、省赋役、罢西洋取宝船及云南、交阯采办诸道金银课,仁宗一一接受。
1407年(永乐五年),永乐帝将交阯(今越南北部)并入明朝版图,设立交阯布政司。但此后的二十多年中,明朝在这里的统治一天也未安稳过。仁宗在位时曾计划放弃这桩劳民伤财的事情,但因不久去世而作罢。宣宗登基后,即与杨士奇、杨荣等人商定放弃交阯的方案,终于在1431年册封黎利“权署安南国王事”。
对于北部的边防,仁、宣时期仍积极经营,但放弃了主动出击的战略,基本处于防御状态。
在内政方面,仁、宣时期对洪武、永乐以来的政制和政策作了一系列调整。
政制上的调整体现在宣德时确立的内阁与司礼监的共同辅政体制以及各省巡抚的专设。票拟与批红的决策程序,比朝堂论决的方式更加合理一些,因为它可以给君臣双方比较充裕的思考时间。各省巡抚的专设,则适当地扩大了省级政府的权力。巡抚原来是一个动词,是皇帝或臣下代替皇帝巡视安抚地方的意思。到1430年(宣德五年)9月,宣宗提升六位中级官员为六部右侍郎,前往巡抚江西、浙江、湖广、河南、山西、北直隶、山东、南直隶苏松等府县,“总督税粮”,“使人不劳困,输不后期”,与地方官员及巡按共理诉讼,有利国便民事宜,奏闻施行。这一举措标志着明朝开始在各省专设巡抚;从此,巡抚一词也就变成了官职名称。
在派遣各省巡抚之前的5月间,宣宗已特别选拔九个精明强干的地方官出任苏州等重要府郡的知府,其中苏州知府况钟(1383—1443年)最为知名。
这些巡抚、知府的派遣,有效地改良了地方政治。他们能力出众,富有热情,又得到朝廷的长期信任,在地方较有作为。他们的任期长,在明朝历史上是十分独特的。六位巡抚,除浙江巡抚赵伦因用重刑督征税粮,被朝廷取回,任期不足3周年外,其余五位,任期最短是9年,而于谦任山西、河南巡抚长达18年,周忱任南直隶应天、苏州等府巡抚更是长达22年,一直到1451年(景泰二年)。九位知府的任期都在6年以上。其中况钟知苏州达13年,莫愚知常州达12年以上,陈本深知吉安达18年。他们的政绩突出,口碑甚佳。周忱与况钟、莫愚等人合作,改变了洪武以来对江南实行重赋和压抑的政策,大大降低了这个地区的税赋;又与陈瑄合作改善了江南漕粮运输,从而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消除了江南从明初以来就存在的,并且日益严重的税粮拖欠现象。陈本深知吉安,“为政举大纲,不屑苛细”,人民生活安定,“耻争讼”。何文渊知温州,“治最,增俸赐玺书”。
在经济政策方面,仁、宣时期很注意压缩开支、减轻人民负担,与民休息。永乐时,南征北伐,工役频举,支出浩繁,物力耗费,人民疲敝。仁宗一即位,就下令停止各地为宫中采办宝石、金珠、马匹以及烧铸进贡等等。北京、山东两地每年要交枣80万斤供宫中做香炭之用,这是常赋,并不是额外采办。仁宗也令只征一半。以往政府修理军器、盖造房屋的物料都是征自民间,而不管该地的物产情况。人民须筹资购买上交,其中要受奸商、猾吏的多重盘剥。仁宗下令以后官府所用物料,于产地计价购买,科派病民者,严惩不贷。仁宗对地方的水旱很为关切。通政使奏请将全国各地报告雨泽的章奏送给事中收贮。仁宗说:“祖宗时定下各地及时奏报雨泽的制度,本来是为了解各地的水旱情况,以便行恤民之政。雨泽章奏堆放在通政司,就已失去了作用,现在又要收贮在六科,是要让上位之人终究无法得知。从今以后,雨泽章奏送达,立即奏闻。”凡是地方受灾,仁宗都下令蠲免田赋,发放官粮赈济。1425年(洪熙元年)夏天,山东和河北一带闹饥荒,地方官却照旧催征夏税。仁宗得知后,即命杨士奇起草诏书,蠲免该地当年夏税与秋粮的一半并停置一切官买物料。杨士奇认为这件事应该通过户部和工部。 仁宗说:“救民之穷当如救焚拯溺,不可迟疑。二部如果得知蠲免,怕影响国家费用,一定会迟疑不决。”于是让杨士奇立即起草诏书。仁宗看了诏书后,很满意,就盖上玉玺,发出执行。然后,他对杨士奇说:“现在可以告诉户、工二部了。”
宣宗继位后,继续执行仁宗的与民休息政策。他对民间的疾苦有一定了解,并赋予同情。他曾陪侍母亲谒陵,途中见到农民种地,便下马问农事,并亲自操耒耕地。他对侍臣说:“朕推了三下,就已不胜其劳,更别说常年干这种活了。人们常说,劳苦者莫过农家,确是如此。”他曾亲作《织妇词》一篇赐给朝臣,并让人配上画,张挂在宫中,教官员和妃嫔知道并记住百姓的艰辛。
宣宗的生活较为节俭。他刚即位时,有人提出宫中御用器物不足,必须到民间采办。宣宗制止他,并说:“汉文帝的衣服帷帐没有文绣,史称其恭俭爱民。朕也须以俭约率下。”有个和尚要修寺为他祈求长寿,被他训了一顿。他还引用历史事实驳斥了长寿术的妄谬。1428年,锦衣卫指挥钟法保建议派人到广东东莞采取珍珠,被宣宗治以“欲扰民以求利”的罪责。宣宗也反对朝廷费用和工程建设中的奢侈浪费。在修建仁宗的陵墓献陵时,他遵照乃父遗嘱,厉行节约。他亲自规划,仅3个月就完成了工程。献陵在规模和华丽方面不如永乐帝的长陵,以后几位皇帝的陵墓都以它为楷模,只是到世宗营建永陵时,才又开始奢华。宣宗一朝没有兴建大规模的建筑工程,匠户的劳役比以前大为减轻。这个时期减免赋税的数额也相当大。16次大数额的减免中,1430年和1432年两次减免的税粮总数即超过150余万石,使老百姓得到了实惠。
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人民的休戚,国运的兴亡。宣德时期虽然不像洪武时期那样采取法外用刑的手段严惩贪官污吏,但对吏治仍抓得很紧,注意用法制来保持官吏队伍的清廉。宣宗将贪墨不法的太子少保、左都御史刘观贬谪边塞,起用清正刚直的通政使顾佐任左都御史,官场风气为之一变。又规定官吏犯贪赃罪,不许以赎(罚款)代刑。
仁、宣时期的政治较为安定。虽然有汉王朱高煦的叛乱(1426年),但很快平定,也没有因此而广加株连。这个时期没有压倒一切的内部和外部危机,没有党派之争,也没有国家重大政策方面的争论。政制和政策得到了及时调整,政府能够卓有成效地工作。在安定清明的政治下,人民生活得到改善,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仁、宣时期是明朝历史上第二个社会经济的恢复期,既缓解了永乐时的困境,又为明代中期的社会发展奠定了基础。
不过,在稳定与发展中也蕴藏着危机。仁、宣二帝是明朝历史上善纳谏言的皇帝。但当翰林侍读李时勉毫不客气地批评仁宗行政中的缺失时,仁宗大怒,命侍卫用金瓜打他,立时将他的肋骨打断三根,险些要命。宣宗颇事游猎玩好。他爱好斗蟋蟀,令地方官进献,结果弄出“一虫杀三人”的悲剧。清代作家蒲松龄的名著《聊斋志异》中的《促织》一篇就是根据这段史事写成的。当然,与宣德以后的明朝皇帝比起来,仁、宣二帝算是贤主了。但贤主尚且如此,不贤者就更勿论了。可见,君主专制政治下,贤主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贤主的出现并不是必然的,而昏君、恶君的出现倒是理所当然。宣宗又开启了宦官干政的合法途径。他在位时尚能约束宦官服务于文治政治,到他儿子时便养出了明朝历史上第一个乱政的大宦官王振。仁、宣时对军官贪赃枉法、私役军士、私占屯田弊端的治理并没有多大成效,正统时的武备废弛实际上是这一状况的继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