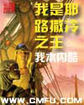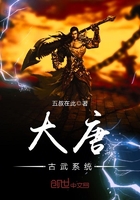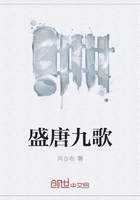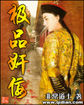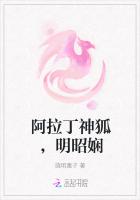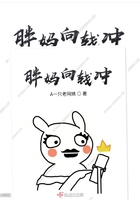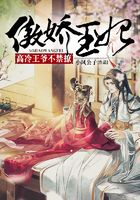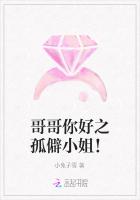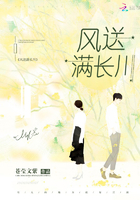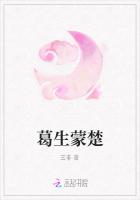1402年(建文四年)7月17日,燕王朱棣拜谒孝陵(朱元璋的陵墓)后,在群臣的山呼万岁声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宣布革除建文年号,将当年剩下的时间改称洪武三十五年,以表明他的皇位并不是从建文帝手中篡夺的,而是直接继承了他父亲的遗产;改明年为永乐元年,恢复洪武时期的旧制度。
20日,永乐帝埋葬了建文帝,既不给他议谥号,也没有为他修造陵墓,更没有让他的牌位在太庙中供奉。后来永乐帝的子孙修《实录》,也不记载建文一朝的史实。建文帝的历史地位被完全抹杀。直到1644年7月,南明君主福王朱由崧才定建文帝的庙号为“惠宗”,谥号为“让皇帝”。后来不久,南明被清朝所灭,福王给建文帝追封的庙号谥号也就不为清朝所承认。1736年,清朝的乾隆皇帝追谥建文帝为“恭闵惠皇帝”,并在敕修的《明史》中列(恭闵帝纪)一卷,肯定了建文帝的历史地位。
朱棣用最残酷的手段来对付忠于建文帝的官员。他本想取得知识分子的支持。在他最后一次南征的出发前,道衍和尚告诉他,要保留方孝孺那颗“读书种子”,争取儒士的支持。方孝孺是建文时期儒臣的精神领袖。他是浙江宁海人,少年时从学著名学者宋濂,文章德行备受名家的推崇,曾被蜀王聘请为世子的老师。建文帝即位后,召他做翰林侍讲,后升文学博士,参与大政方针的制定。朝廷讨伐燕王叛乱的诏令檄文大都出自他的手笔。燕王占领南京,建文帝自焚,他也在同一天被捕。朱棣要他拟写登位诏书,他放声悲哭,震动了宫殿。朱棣说:“先生不要怪罪自己,我只不过是想效法周公辅佐成王罢了。”孝孺说:“成王在哪里呢?”朱棣说:“他放火把自己烧死了。”孝孺说:“为什么不立成王的弟弟?”朱棣说:“这是我们老朱家的家事。”示意左右递上笔,说:“这诏书,非先生草拟不可!”孝孺接过笔往地上一撇,一边哭一边骂:“死就死,诏书不能拟。”朱棣大怒,命令将他分尸。孝孺赋诗一章,慷慨就死。
朱棣把方孝孺分了尸还不解恨,又将他的家人和所有的亲戚朋友、学生抓起来,统统杀死,一连杀了好几百人。朱棣进入南京后,列了一个50多人的“奸臣”名单进行大搜捕,然后就是大清洗、大屠杀。列入“奸臣”的人都受到了和方孝孺一样的待遇。不但己身遭屠戕,而且与他有牵连的家人、亲戚、朋友也都遭牵连,被屠杀、关押、流放。这种残酷镇压的方式就像顺藤摸瓜一样,被称为“瓜蔓抄”,又称为“株连十族”。由于杀人并不以当事人为界限,他的家族、亲戚、朋友都要受株连,甚至收藏方孝孺诗文的人也要被处死,所以,尽管列入“奸臣”名单的人并不多,而实际上遭杀戮的人则成千上万。
建文帝为什么用全国的力量不能战胜一个僻处一方的藩王呢?关键在于他的核心领导集团缺乏军事方面的实际经验,不能够将全国的力量协调一致,形成足够有效的武力,给燕王势力以及时地毁灭性打击。而燕王的成功,就在于他极大地发挥了自己的军事指挥才能,利用朝廷不能协调一致、用人不当的缺点,采取灵活机动的战术,抓住要害,终于以小胜大,以弱胜强,四载而成就帝王大业。
永乐帝登基以后,虽然打出了恢复祖制的旗帜,但是他不能允许别人效法他的行为,再由一个握有军事实力的藩王,运用武力夺取帝位,他不得不继承建文帝的削藩政策,制造各种罪名,囚废有实力的诸王,削夺他们的护卫。到他的孙子以后,朝廷对诸王的限制越来越严密。二王不得见面,出城扫墓都得经过朝廷的允许。除了个别的亲王在皇帝缺乏子嗣时有机会登上皇帝的宝座(嘉靖帝、崇祯帝出身藩王),个别的有能力造反(安化王朱寘镭在1510年、宁王朱宸濠在1519年发动叛乱)外,绝大多数既不能当官,也不能经商、务农、做工,只能坐待人民的供养,当一群寄生虫。而且每朝的新皇帝都要分封新的藩王,而藩王的子孙又要层层分封,各王室的人口按照几何级数往上翻,到1550年,总数达到10万人,给明朝政府造成严重的财政负担。1562年统计,全国每年供应京师的粮食是400万石,而王府禄米一共853万石,比供应京师的多出一倍还多。以洪武后期明朝岁收粮米最多时的数字作基数,王府禄米竟占全国田赋收入的四分之一以上。朝廷无法应付,只能减发禄米,那些疏远的皇族就不免啼饥号寒了。地位高的亲王郡王,凭借与皇室较亲近的关系,不但凌虐平民,也侵暴官吏;疏远卑下的皇族穷极无聊,对老百姓敲诈勒索,无恶不作,扰乱破坏社会秩序。到明末,政府感到让皇族只当寄生虫不是办法,就把科举向他们开放,让他们有机会做官。但是,不久明朝就被农民起义军推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