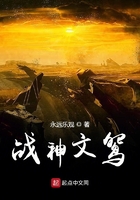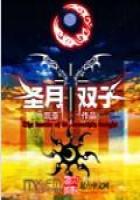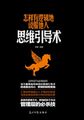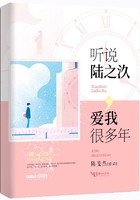前面说过,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了让江山在自己的血胤中永世流传,废除丞相、杀戮功臣,还分封自己的儿子为藩王,作为朝廷的屏翰。分封制是已经被历史淘汰了的制度,朱元璋却又捡了回来,遭到关心国家长远利益的儒臣的批评。有个名叫叶伯巨的教官上书指出:分封容易造成尾大不掉,最终威胁朝廷,汉代的七国之叛,晋代的八王之乱,都是教训。朱元璋认为,这是离间他们父子的骨肉亲情,居心不良,就把叶伯巨抓了起来,关进监狱中囚禁死了。
可是,明朝后来政治形势的发展,却不幸让这位叶教官说中了。
到洪武后期,朱元璋大杀功臣,北方边防重兵的统帅权就转到了塞王的手中。塞王中的晋王朱、燕王朱棣,是兄弟,又足智多谋,英勇善战。他们曾经多次带领诸王和统率各将领出塞作战,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建立了崇高的威望。其中燕王尤其突出。
燕王是老四,他和在开封的周王朱木肃,是同母兄弟。都是碽妃所生。石贡妃是蒙古族人。正因为燕王有蒙族血统,所以长得隆须长髯,与朱元璋的小胡子有些区别,也更威武一些。燕王不仅军事才能杰出,兵强马壮,而且雄踞北平。北平是元朝的故都,元朝就是以它为中心,完成一统全国伟业的,所以它在地缘政治上有着明显的优势。
塞王军事权力的增长,引起了与皇太子有利害关系的大臣的不安。骁将蓝玉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小舅子,而皇太子的正妃常氏则是常遇春的女儿,也就是说,蓝玉是皇太子正妃的舅舅,所以蓝玉对皇太子地位是否稳固就很关心。他经常在北方前线作战,对燕王的所作所为很清楚。有一天,他对皇太子说:“臣看燕王不是一个甘居下位的人。外间传出谣言,说燕都有天子气。殿下要认真对待这件事。”
蓝玉跟皇太子的谈话,奇迹般地传到了燕王的耳朵里,燕王听了又恨又怕。1392年5月,皇太子病故,燕王揣摩老皇帝的心理,决定伺机报复。这年8月,他从北平到南京朝觐,元璋问他:“民间近来对朝廷有什么议论?“燕王说:“只是诸公侯专横不法,令人忧虑。不杀几个尤甚者,不足以平民愤,也怕有尾大不掉的危险。”此番话语,正中元璋心病,几个月后便发生了蓝玉党案。
皇太子死后,16岁的儿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作为皇位的继承人。诸王都是皇太孙的叔叔,不把他放在眼里。蓝玉党狱以后,功臣收拾得差不多尽了,北方重兵的统帅权转到塞王的手里,朱元璋以为天下江山可安全保持在孙子手中。他对皇太孙说:“朕将抵御胡虏的任务交给诸王,可令边尘不动,将平安留给你。”皇太孙说:“胡虏不靖,诸王去抵御,诸王不靖,又谁去抵御呢?”元璋一时说不出话。稍停,他问皇太孙:“你看该怎么办呢?”皇太孙说:“以德怀之,以礼制之;不可,则削其地;又不可,则废置其人;又甚,则举兵伐之。”元璋说:“也只有这么办了。”
朱元璋是一位英主,诸王权势的增长可能会对未来的皇帝构成威胁,他是预想到了的。
他曾经编了个《永鉴录》的历史读物教育诸王遵纪守法,忠于朝廷。晚年又修订《祖训》,对诸王的权力作了些微缩减。但分封诸王作为朝廷的屏翰是他既定的政策,他相信诸王与皇帝的矛盾是家里的矛盾,皇位落到诸王手里还是不出他自己子孙的掌握,总比落到异姓手里强。因此,他只是苦口婆心告诫诸王与皇太孙,要知亲亲之义,不要挑起内斗,以免让他人钻了空子。
洪武末期形势的发展,对燕王越加有利。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秦王朱樉病死。1398年3月,晋王朱又在他老父的前边离开了人世,燕王便成了元璋存世诸子中的老大。这时古稀老翁朱元璋已是日薄西山,皇太孙也要考虑将来如何对付诸王威胁。他在东角门(宫内便门)召见翰林院修撰黄子澄,问道:“诸王都是我的长辈,手握重兵,不守法纪,怎么办?”子澄说:“诸王护卫兵数量不多,仅够自卫,倘若发生变故,朝廷以六师相临,谁敢相抗。朝廷讨伐叛藩是以大击小,以强击弱,以顺击逆。西汉吴楚七国力量并非不强,最终不都是自取灭亡了吗?殿下不要过虑。”
黄子澄这番话说得好不轻松乐观。他是江西分宜人,1385年(洪武十八年)的会元。当过翰林编修,还做过太子伴读,所以和皇太孙的关系很密切。
1398年6月24日(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乙酉),朱元璋病死。临终前,他嘱咐驸马梅殷替他讨伐违背天命的人。这种临终受命的人就是“顾命大臣”。梅殷是宁国公主的丈夫,天性恭谨,精通经史,有谋略,擅长骑马射箭。
同受顾命的大臣还有黄子澄和齐泰。齐泰是江苏溧水人,是黄子澄的同年进士,做官没有出过差错,曾被朱元璋挑选做大祭天地的陪祀官。他对边将的姓名、军事图籍都了如指掌。1395年(洪武二十八年),朱元璋破格将他从兵部郎中提升为兵部左侍郎。皇太孙对他很尊重。
然而,饱读经史的朱允炆和他的几位顾命大臣,对朱元璋死后他们所面临的政治任务,没有清醒的认识,特别是对削藩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没有及早制定周密的削藩计划。朱允炆本人也没有确定削除强藩的坚定决心。因此,一开始,他们对诸王采取的措施就显得软弱。
老皇帝去世,往往是当权者铲除政敌的一个好机会,这种事例,在历史上不胜枚举。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朱允炆君臣曾在这类史实中受到启发。朱元璋死后,朱允炆马上公布了遗诏,遗诏中规定:“诸王各于本国哭临,不必赴京”,“王国所在文武衙门军士,今后一听朝廷节制。”遗诏名义上是老皇帝的遗言,实际上反映的是新皇帝的意志。元璋死后第七天,朱允炆就将老皇帝匆匆安葬,同时举行登基大典,改年号为“建文”,历史上就称他为建文帝。
燕王早在南京安排了坐探,不等接到朝廷的诏书,就得知了父皇的死讯,立即带兵南下奔丧。快到淮安,遇上朝廷的使者令他遵遗诏返回封地。燕王大怒,仍要前进,见交通要道已有官军把守,才无奈退了回去。建文帝要是有心除掉燕王,完全可以在南京布下一张罗网,让燕王自投其中,束手就擒。但他白白放弃了这个机会。另外,这样做也不符合天子梓宫停放七个月,待宗亲会齐再下葬的传统礼仪。禁止藩王奔丧的诏书发了下去,结果诸王认为齐泰矫改遗诏,离间他们的血肉亲情,一下就把朝廷与诸王的关系搞坏了。
建文帝即位后就提拔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寺卿兼翰林学士,同参军国事。建文帝对子澄说:“先生还记得在东角门说的话吗?”子澄说:“不敢忘!”回去就与齐泰商量削藩的具体方案。齐泰认为应该先从燕王下手。子澄反对,他说:“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就有许多不法行为,削之有名。今天要问罪诸王,应该先从周王开始。周王是燕王的同母弟弟,削除他就是剪断了燕王的手足。”方案就这样定了下来。
建文帝即位后的第三个月,逮捕了周王朱木肃,将他流放到云南的蒙化。
燕王在淮安受阻,感到朝廷已猜疑自己,便让三个儿子都到南京奔丧,自己在北平装起病来,以解除朝廷的怀疑。这时,手足兄弟被废,他感到大难就要临头。举兵造反,儿子们又全押在南京,令他顾虑犹豫。他的高参道衍和尚要他坚定信念,推翻幼主,自己做天子。燕王说:“民心向他,怎么办?”道衍说:“臣只知天道,不知民心。”
这里所说的道衍和尚,俗姓姚,是苏州长洲人,精通阴阳术数,对诗书儒经也有相当造诣。长着一对三角眼,体形就像一只病虎,神情阴险。朝廷曾经选拔通儒书的和尚当官,他嫌官小,只接受了一套和尚服。马皇后去世,朱元璋选高僧陪侍诸王,为皇后诵经荐福,道衍被选中。燕王见到他,谈得很投机,就请示元璋,将他带到了北平,住持庆寿寺,做自己的谋士。
道衍还向燕王推荐了一位叫袁珙的相面师,为他预卜未来。袁珙说:“殿下是异日的太平天子。”燕王说:“估计在什么时候?”袁珙说:“年逾四十,紫髯过脐,当是时,拨乱反正,万邦一统。”燕王听了,大喜,决心造反。于是秘密而迅速地选拔将领,补充部队,招收勇士。燕王府宫院深邃,便于隐蔽,燕王就利用这个条件,将后苑作为道衍的练兵场。又在地下挖成两层的地下室,让工匠在里面昼夜不停地轮班打造兵器,地面上筑起又高又厚的墙,墙上甃满尖锐扎手的陶瓷碎片,防止有人攀越。院中养一大群鹅鸭,让它们的呜叫掩盖打造兵器的声音。
当年12月,建文帝安排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布政使,谢贵、张信掌北平都司,监视燕王的行动。
1399年(建文元年)的年初,削藩继续进行,岷、代、齐三王被废黜囚禁,湘王全家被迫自焚而死。为了探测燕王的意向,或是震慑燕王,建文帝让燕王给周王议罪。燕王在上书中请求朝廷顾念亲亲之情,不要伤了骨肉之恩。建文帝看了上书,很是难过,他那根“亲亲”的仁柔心肠,被燕王拨动了,他对臣下说,削藩的事情应该停下来。齐泰、黄子澄说事情已进行到这种地步,不能再犹豫,当断不断,反遭其乱!又说朝廷担扰的只不过是燕王,应该乘他生病来个突然袭击。建文帝还是犹豫不定,说:“朕即位不久,就连黜诸王,如果又削夺燕王,何以向天下人交待?”
建文帝的犹豫,既反映了他的优柔寡断,没有坚定信念,也说明黄子澄的削藩策略一开始没有抓住燕王这个重点,而将打击对象放在势弱诸王身上,扩大了打击面,将本来可以争取的力量都推到朝廷的对立面去了。
不过,事情既然开了头,就没有了退却的余地。建文帝君臣决定调整策略,全力对付燕王。于是将燕王护卫的精壮士兵抽调到朝廷控制的部队,又在北平附近的开平(在今内蒙古正蓝旗北)、临清、山海关部署军队,对燕王势力形成包围。
形势越来越急,燕王顾虑三个儿子无法回到自己身边,便上书朝廷,说自己病得快要死了,求朝廷怜悯,放他的儿子回去跟他见上最后一面。齐泰认为应该将燕王的三个儿子扣下,使燕王造反有所顾虑。在朝廷的部队已布置到燕王鼻子下面的情况下,黄子澄却故作聪明,坚持放回燕王的三个儿子,以为可以打消燕王的疑心,取得袭击的成功。
三个儿子意外安全归来,燕王没有了顾虑,决定尽快起事。一场同室操戈的战争迫在眉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