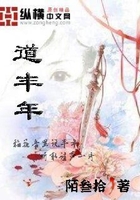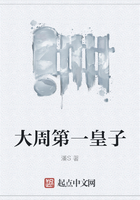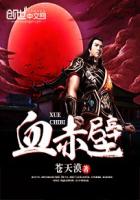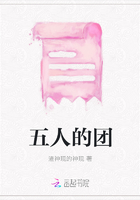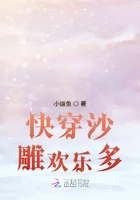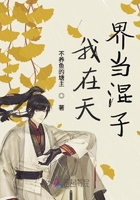明朝的建立是通过武力的征伐实现的,这一点,与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王朝并没有什么不同。不过,明朝还是有些特别的地方。那就是它的开国皇帝明太祖出身的贫贱,为中国历史上仅见;另外,由农民起义军首领建立的王朝,除西汉外,明朝是第二个。
那么,何以出身社会底层又曾做过丐僧的朱元璋会成为明太祖呢?
他的成功取决于他自身和元末政治、军事、社会大环境两方面的因素。从他自身的因素看,目标远大而能稳扎稳打,善于利用时势,既不患张士诚的狭隘,又不患陈友谅的浮躁;恩威并施,赏罚严明,善于用人,既没有宽于笼络以致受人蒙蔽的失误,也没有刻薄寡恩以致部众离心的过错。所以,他在元末群雄中能够由小变大,由弱而强。从当时的大环境看,红巾军主力在中原与元军的厮杀,形成了对他的一道保护墙,让他有机会坐大,同时又消耗了元朝的力量;元朝虽然扑灭了红巾军主力,却陷入了军阀割据,自相残杀,无力再构成阻挡明太祖一统天下的势力。
1368年,大明王朝宣告建立。新王朝比以往各朝更为集权和专制。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源不在于明初的阶级矛盾比以往更尖锐,而在于明朝创立的独特历史过程、明初各政治社会势力间关系的性质,以及人作为万物之灵会从以往历史中学习的能力。
明初功臣多出身农民,只会冲锋陷阵而不懂舞文弄墨;明初的文臣则大都来自江浙一带的地主富户,原本把红巾军作盗贼看。所以,作为统治阶层两大集团的武将和文臣之间,就难于沟通、融洽,易为皇权支配。而明太祖出身贫贱,做过云游和尚,不像唐太宗、宋太祖做皇帝前与功臣间已形成主从关系,也不像汉高祖在功臣中有一帮过去的哥儿们。因此,明太祖与功臣的关系,贫贱时与富贵时的反差就特别大,他对功臣也就没有一种约定俗成的信任,于是只有借助于礼法。但是,礼法越是细密,功臣那种哪朝哪代都一样的依仗特权追求财富、不守规矩的行为,在他看来,便越是难以忍受,于是屡兴大狱,把功臣杀戮殆尽,残酷程度超过历代开国之君。
明太祖广揽儒士,善于向历史学习,在历代开国之君中也是非常突出的。鉴于历史的教训,他废除了丞相,兼任国家元首与政府首脑,将丞相的职能分散于六部、都察院、翰林院、通政司、给事中、宦官等衙门,在国家权力机关的设置上充分贯彻了“大小相维、内外相制”的原则,使皇权在各官僚机构的互相制约中,获得高度的稳定和强化。
永乐以后,中央出现内阁,宣德时形成司礼监与内阁共同辅政的体制。内阁不是中书省,首辅也不是丞相,因为内阁不能统辖六部与百官。它只不过是翰林院“密勿论思”(作皇帝裁决政务的顾问)职能的专门化。内阁、司礼监对掌“票拟”与“批红”,把皇帝决策的过程程序化和制度化了,有利于正确决策,同时也将皇帝从琐务中解放出来,却丝毫不影响皇帝乾纲独揽。正统以后出现的权阉和嘉靖万历时出现的权辅,都是皇权异化的产物。是司礼太监权大,还是内阁首辅权大,依皇帝的好恶为转移。然而权阉和权辅对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都构不成威胁,这正是明代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重要表现。
明代的君主专制也是建立在中央集权基础上的。明太祖废除行中书省,改设三司,三司间互相牵制。但这种体制使得省级政府缺乏必要的自主权。宣德中期,明廷开始向各省派驻由朝廷大臣出任的巡抚,使得省级政府获得了必要的自主权,又不致脱离中央的控制,在某种程度上改善了地方政治。
明代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的强化,表现为官僚政治与皇权政治的高度发达,而前者又构成后者的基础。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又表现出“法治”的特征。《大明律》制定的审慎,尤其是行政法典的完备,超过以往各朝;而科举制成为选拔官僚的主要渠道,既使入仕者具备了一定的从政能力,又能有效地传播爱民、特别是忠君的观念,也使官僚队伍的社会成分经常处于流动之中,扩大了统治基础。这正是明朝皇帝从宪宗以后多不上朝,而国家机器却照样可以运转的重要原因。
但是,这种高于历史水平的“法治”也是高度的人治。因为这些法只施之于臣民,而对皇权却没有丝毫的约束力。与“法治”形成鲜明的对照,明朝皇帝比历史上任何朝代的帝王更加借重特务与法外用刑。锦衣卫和宦官二十四衙门,是两大特务机关;廷杖、东厂、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即诏狱)是明朝皇帝行使法外用刑的四大工具,“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利于法”。所谓“不利于法”,就是用刑不以法律为依据,听凭锦衣卫的校尉、东西厂的宦官肆意妄为,滥用酷刑。明代专权乱政最为猖獗的宦官刘瑾和魏忠贤,就是集司礼监的批红权和东西厂、诏狱的法外用刑特权于一身,形成明朝历史上最黑暗的宦官专权统治。正因为如此,明代的皇权统治比以往就更为反动。
明朝中央集权虽然高度强化,但与历朝一样,仍是一个天高皇帝远的社会。中央和省级政府都很庞大,府、县地方基层政府都很弱小,地方财政也很为脆弱。基层政府除了应付最基本的任务,即征税和审判人命案,此外一般谈不上发展地方经济,组织地方社会。对地方的统治,必须依靠乡绅和豪强。明朝的各级官僚和准官僚都拥有不同程度的赋役蠲免权,使得他们形成一个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在本乡就称为乡绅,他们往往是一方势力。
明朝的行政立法虽然比以往显得发达,地方的行政技术却仍然是简朴而粗糙的,并且很难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明太祖建国伊始,便追求一个建立在小农经济之上,在官僚机器严密控制之下的强控制的、高度稳定的社会,又以强控制、高稳定的小农社会为模板去改造社会的其他部分。他制定了一些奇怪的政策,如不是向市民课税,而是让南方市民到经济残破的中原服劳役,还让市民为官府养马等等。这些政策从中国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看来,是不奇怪的。正因为大规模立法的洪武时期是以通过强控制达到高度稳定的农业社会为模板去塑造整个社会的,所以,明朝政府的社会管理技术不但一如既往的简陋,在明朝前期还有所倒退。
简朴而停滞的行政技术,使得政府很难将地方势力的发展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于是,政府的政策就处于矛盾的状态。一方面,政府造成了乡绅这一拥有特权的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他们过分扩张,不时运用强制力对地方势力的过度发展予以扼制、打击,如此,中国传统社会的资本积累就很为不易。明朝的闭关自守政策正是应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
明朝闭关自守政策表现为“朝贡贸易”和海禁的结合。它的作用是双方面的。一方面,将海外贸易的利益紧紧抓在皇室的手中,避免因此造成大的地方势力;另一方面,又借此作为笼络远人的一种手段。郑和下西洋是“朝贡贸易”的最高峰。但是,“朝贡贸易”的高成本须臣民付出,而它的绝大部分利益却为皇室独占,因而遭到官员们的反对。为了避免再次出现郑和下西洋的劳民伤财之举,他们甚至将郑和下西洋留下的技术档案也付之一炬,于是郑和下西洋这一空前的壮举便成了中国航海史上的绝响,而地理大发现却为航行设备远比郑和船队简陋的欧洲探险家所完成。
集权与专制制度不允许私人从事获利巨大的海外贸易。但是,随着明朝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地理大发现,把中国也卷入了世界经济的潮流,海外贸易的机会和利润也就更多更高了。于是,走私贸易在16世纪中叶便猖獗起来。明朝政府禁之愈严,走私愈是厉害。终于酿成嘉靖年间的沿海倭乱。倭寇中的真正日本海盗不能说没有,但不占大多数,占大多数的是中国的走私商人和依赖海外贸易为生的普通百姓。在走私势力的强烈反抗下,明朝不得不开放了海禁。但这种开放是很有限的,而就明朝政府的主观意图看,不过是“寓禁于征”,并且明政府的镇压造成中国海商势力的中衰,等于把海外贸易的权利拱手送给了西方殖民者。海禁开放后,中国海商的势力并未得到政府有效地保护,在菲律宾的华商屡遭西班牙殖民者的残忍屠杀,而明朝政府却幸灾乐祸。明后期中国与西方关系的历史,已预示着二百年后中国的屈辱命运。
近代初期,欧洲人的海外拓展都受到了王权的保护与支持。王权之所以要保护与支持海外拓展,无非是基于对东方财富的贪婪。明朝皇帝的贪婪不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国王之下,当大量的美洲白银由马尼拉中转源源流进中国后,万历皇帝对贵金属的贪婪欲也被极大地刺激起来,因此而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对臣民财富的疯狂掠夺。他也曾派使者到马尼拉去勘查金山银山,但是,这一举措除了诱发西方殖民者对华商的大肆屠杀外,别无其他好处。之所以有这种差异,乃是由于欧洲的王权尚有封建领主势力以及历史悠久的议会制度的约束,在海外的拓展上,王权易与民间势力达成妥协,分享利益,从而促成了海外事业的大发展。而明朝的皇权建立在中央集权的基础上,并不存在有效的约束。皇权只知如何最大限度搜刮民脂民膏,却不懂得与民间势力妥协,共享利益,共求发展。于是,不仅好事难成,而且反添祸殃。
明太祖属权力欲最强的皇帝之一是毫无疑问的。为了保证江山在朱姓子孙中永传不坠,他加强了皇权与专制,杀尽了功臣。而另一方面,他又捡起了已被历史淘汰的亲王分封制。二十余年间,藩王坐大。他的尸骨未寒,便有强藩之乱。兵强马壮的燕王朱棣夺取了侄皇帝的宝座。为了酬谢兀良哈骑兵协助他夺取天下的功劳,并防备建文帝残余势力的反抗,他把大宁都司南徙,收缩北部边防,并迁都北京。然而,在处理与蒙古的关系上,他既没有能够建立彻底的和平友好,而五征漠北也并没扫穴犁庭。他在武功上的建树,甚难与洪武名将徐达、李文忠、蓝玉诸人匹敌,也难免穷兵黩武的恶评。迁都北京对明朝历史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不但造成了后代天子守边的不利形势,也使明朝的基本国策更为内向,更为鲜明地显露出经济落后地区的北方大贵族地主对南方经济发达地区的中小地主和工商业势力的压制。靖难之役后,削藩仍继续进行。到宣德以后,除了几个藩王能继大统,三两个藩王能试演蹩脚的“靖难剧”,某些藩王能发展高雅爱好,在艺术与科技上取得成绩,绝大多数则成为明朝财政的一大赘疣,社会的弃物。
朱棣靖难,中断了洪武以来社会经济恢复发展的过程。直到仁、宣二帝继位后,才重新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明朝的社会经济出现第二次恢复发展。这一时期的政治也相对安定和清明,历史上称为“仁宣之治”。
然而,仁宣治世犹如昙花一现,明朝随后进入了动荡不定的时代。童懵天子信任宦官王振,不但把朝廷上下弄得乌烟瘴气,而且也让自己做了瓦剌的俘虏。幸亏还有于谦这样的干国英才,砥柱中流,力挽狂澜,明朝才避免了宋朝的命运,而明英宗也没有成为宋徽宗第二。可是,专制政治总与阴谋、政变有着不解之缘,重造大明江山的英雄竟然死于野心家之手。
自15世纪中叶开始,明朝国内不断有人民的起义。当时南北经济的差异很大,北方旱作农业地区由于积累性的过度开发,生态环境遭破坏,水旱灾害连绵不断,农业经济本已很脆弱,加上难以负担的赋役剥削,大贵族地主凭借特权兼并土地,农民被迫背井离乡。如此,明初确立的强控制社会秩序便难以继续维持。但明朝政府仍是抱残守缺,紧抓住原来的户籍制度不放,用惨无人道的方式遣散聚集在荆襄的流民。流民走投无路,只得揭竿而起,用无数的鲜血与生命,方才换取了专制政府允许流民在当地落户的政策。
社会矛盾在明朝政府日益因循、腐败与反动的统治下继续恶化。北方以皇帝为最大头目的大贵族仍在凭借特权兼并土地,垄断各项利业,而南方的缙绅大地主也同样是贪得无厌。皇权的腐败,意味着约束贪官污吏最基本力量的消失,表示着明朝政府从头往下烂。于是,不能照旧生活下去的农民只有拼死一搏。而腐败的政治无法将丰富的人力物力资源转化成巨大的国防力量,明朝的边疆危机也在不断加深。
那些对儒学忠君爱民思想抱有虔诚信仰的士大夫,以世人皆昏我独醒的气概,力图扭转乾坤,刷新政治。清官海瑞与“权臣”张居正都属于这种人物。海瑞更多的是以个人傲霜立雪的高尚品节去感化与振作,而张居正则侧重运用纵横捭阖的铁腕,实际上是以摄政者的权力对政治进行刷新。然而,他们在事业上不能取得成功的结局都是一样的。海瑞这位热血满腔的清官,最后只能“镇雅俗,励颓风”,充作当政者装饰门面的摆设。而权倾一时的张居正,身后更遭家破人亡的悲惨清算。这个王朝已病入膏肓,不可医治。
清算了张居正的明神宗,最集中体现了专制皇权的腐朽反动。他贪得无厌,不惜动用宦官,越过法定的官僚机构,对全国人民,特别是对工商业者,进行史无前例的直接大掠夺。他不守君道,不理朝政,丧失皇权的基本政治职能,听凭统治集团不同的利益派别互相倾轧,把明王朝引向了灭亡的深渊。于是民变起于内地,后金崛起东北,逐渐形成埋葬明王朝的力量。
昏君明熹宗崇信乳母客氏与太监魏忠贤,使统治集团的派别之争演成生死大搏斗;陕西农民首举义旗,展开了以武力埋葬朱明王朝的斗争。明王朝在覆亡的深渊中越陷越深。
有志中兴而刚愎自用的崇祯帝,无力回天,在“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无奈中,上吊煤山殉了国,存在了277年的明王朝宣告灭亡。
李自成领导大顺农民军长驱直入北京,推翻了明朝的统治。但他既对时局认识不清,没有看到处理明朝残留军阀吴三桂的重要性,以致有山海关战役的失败;又没有建立可靠的根据地,于是一败涂地,江山落到了清朝的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