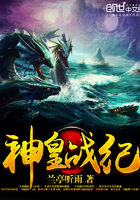刀思管低头一看,猛吓一跳。廖元吐出的污物里竟有一团团的羊毛和烂纸,羊毛和纸团中间,有一粒被长一寸的细麻绳缚住的黑子。
老六说:“呶,这粒黑子就是蛊了。”
细看之下,这麻绳一头打结,一头散放,上面粘了无数的小乾虫,看得人浑身毛孔竖起,那鸡皮疙瘩象是还四周游动起来。
刀思管不自主地打了个寒噤,双手一环抱紧两臂,手掌上下来回地抚了好几抚。
廖元突又叫肚子痛,爬起来要去大解。周老六将他牵往摆在房间后侧的便桶处,扶他坐好,塞一把手纸予他,便退到一旁。
刀思管问:“方才你给他吃的什么?”
老六故作神秘,“绝活秘方,不可与外人道也。”
刀思管一撇嘴,秘方就秘方,不问就是。
待廖元解决完毕,老六走过去看了看,说:“好了,解出来了。”
刀思管好奇地凑上前去,见解下的蛊长有半寸,白色蛇形,好几条浮在秽物上面,还可以瞧见青蓝色的蛊口。
“太恐怖了,活的物怎么下得进去?”
“下时应是末状,入则成形。蛊之由饭酒中毒的,分外难治。以后你出行记得带几颗大蒜头,酒饭前先吃几粒,有蛊必吐。”
“蒜头这个功用我倒是知道,刚我也嚼了,一会要到岳凤处。不过常说蛊妇蛊妇,那岳凤他……?”
“席间可有妇人出入?”
“只有侍女。”
“嗯,极有可能假手他人。”
……
廖元早就自顾自爬上chuang又自行躺下,听便其二人在便桶前作分析研究。
二人回到床前,见廖元仍是虚弱无力,脸色苍白泛着铁青。
刀思管问:“解清了吗?”
老六答:“还没。”
老六从背包拿出两根小木棍和一个小黑布包,弯腰将廖元吐出的羊毛和烂纸夹进布包里,又将便桶里的蛊虫夹了进去,布包外又复包了好几层黑布,捆绑好搁至墙角。然后唤门外的下人进来说:“便桶拿出去倒了,再给我热些烧酒,用干净的木桶装了来。”
过了一阵,下人将一桶热浇酒搬进来,又退了出去。
老六回身翻出一大块青布,包了些橘黄色的晶状药末,接着又加了些甲片状碎末和扁片状植物碎末,捆成一个圆锤状。这三样东西刀思管认得,那是雄黄、山甲和皂角。老六将廖元的衣衫解开,廖元马上打了个冷颤,身体直打哆嗦,拼命挣脱想往被窝里钻。刀思管用力摁住他肩膀不让动,老六用布包蘸了热烧酒,替他遍擦全身。
擦前后心的时候,先擦一个大圈,后擦一个小圈,反复地擦了好几遍,竟然擦出满身的羊毛来,耳朵里也有羊毛伸出来。
刀思管在边上瞧着,眼都瞪直了,惊异得说不出话来。
老六用布包不停地蘸了烧酒,逐处细细地将羊毛擦拭下来,又取出一块黑布将之捆包好,与先前那黑布袋一起搁着。然后深深地长呼一口气说:“唿~~~,终于清了。”
说来也奇怪,这热烧酒一擦,廖元的脸慢慢就显出了些血色,不再如先前那般死白。刀思管与周老六正低声商量着事情,忽听见廖元微弱地唤了一声:“咦?刀大人,您什么时候来了啊?”
刀思管乍闻,喜盈于色。这老六果真不负厚望,终是将人给救过来了。
刀思管坐到床边将事情始末快速地陈述一遍,廖元连忙向老六拱手致谢。然后刀又将刚与老六商量之事转述给廖听,三人又埋头计议了一番。
刀思管突然高声呼道:“来人,送大夫~~~”
下人进来,见廖大人还是病恹恹的躺在床上,一地污物发出奇怪的气味。大夫周老六挎着背袋垂手站在床边,刀大人正拿着银子对他说:“周老六,有劳你跑这一趟,这是诊金,我也知道你尽了力,廖大人他就安随天命吧。”周老六忙着推辞,“没治好坚决不收诊金,这是我数十年行医的规矩。刀大人,很抱歉没能帮上忙。告辞!”说完便跟随下人出去了。
另有下人进来收拾脏物,床上的廖元口齿不清地说:“我要回家,送我回家!”
刀思管问下人,“廖大人要带回去的东西收拾得怎样了?”下人回答说昨天大人早就自己收拾妥当。刀思管哦一声,唤随从进来。
“你走一趟,护送廖大人回雷弄,到了那边让他家人再找医生替他治治。你家里我会差人替你招呼一声,你现就动身吧。”
随从领命备车去了,廖府下人则忙着打点行当,替廖元洗浴更衣等,诸如此类琐碎在此就不再详述。
送走廖元,刀思管策马直奔宣抚司府。岳凤不在,下人备茶,刀思管在会客厅悠闲地边品边候。岳凤回来,他忙上前拜见。
岳凤问:“廖元大人走了?”
刀思管答:“刚去送廖大人,他酒醉未醒,大夫说是酒喝多了导致中毒,开了药吃下去却又全吐了出来。我本建议他等酒毒全部解清之后再上路,但廖大人坚持要走,我只好派人护送他回去,现特来向岳凤大人您报告此事。呵呵,岳大人您说这廖大人是不是象个小孩儿?一生病就盼着可以呆在父母身边,归心似箭呢。”
岳凤眼内精光一闪,笑说:“可惜啊,不过走了也就算了。如果他没走,我这儿正好有一种很见效的醒酒药可以给他试试。既然是你差人护送,我便放心了,呵呵,很好,很好。对了,你马上到差房那边报到去,我已交待下去,去到自会有人给你安排。”
刀思管谢过,起身前去前院班房。
此处暂且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