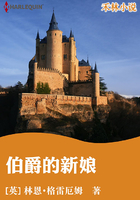王定红在一旁插嘴道:
“管束,你当然没有人家季老总那份风度喽。”
说完两人交换了一个眼色,心领神会的样子。
耶利亚十分不解地说:“说什么哪,你们?”
王定红并不回答她什么,而是用嘴角抿住一个似笑非笑的表情,把菜汤哗的一下全部扣进饭碗里,然后站起身,走了。“她到底在说什么,我怎么一点也不明白啊?”
管束道:“其实也没什么,只是一些传说而已。”
“传什么呀传?我刚到这里没多久,会有什么传闻?”管束说:“那好吧,我告诉你,你可千万别生气,定红说她听人家说季老总很喜欢你。”
耶利亚笑道:
“是吗?连我自己还是第一次听说呢。”
饭堂里的人渐渐走空了,空剩下桌子上的残羹剩饭,一摊一摊地腻在桌子上,让人看着很不舒服。房顶上吊着几架叶片很长的大吊扇,好像几架倒置的直升机的螺旋桨。耶利亚忽然想到,这么冷的天怎么还开着电扇呢?像是为了配合她这个偶然间冒出来的想法,电扇在霎时间转速减了下来。耶利亚听到有人噼里啪啦扳动开关的声音。
五
老季到外地出差,特地给耶利亚带回一瓶进口香水。老季回来之后耶利亚才想起已经有些日子没有见到他了。耶利亚想起那天管束告诉她的有关她和老季的闲言碎语,便特地将房门紧闭,以免再生是非。
耶利亚对老季这个人根本谈不上什么感觉,耶利亚工作以后交往的朋友很多,全都是跟她差不多大的二十出头的小伙子,老季对于她,既是领导又是父辈,在她眼里是什么事情都不可能发生的。
但是,事情偏偏发生了。
老季给耶利亚送香水那天,见耶利亚的房门关得紧紧的,里面传来耶利亚用电话跟什么人聊天的声音。
老季急促的敲门声显然把耶利亚吓着了,她慌忙放下电话跑来开门,门口站着面色和蔼的老季。老季手里拿着那瓶包装精致的香水。
“喏,我是给你的。”
老季一进门就把东西放在桌子上。他说他前一阵子到外地出差去了,回来的时候顺便捎了件小礼物。
耶利亚坐在椅子上没动,把礼物慢慢拆开来看。耶利亚今天穿了件宝蓝和绿相间的宽条紧身衫,下身穿了条A字形短裙,下配黑色半腰方跟皮靴。她坐在线条圆滑的红皮转椅上,拆那锦面纸盒包装的时候,耶利亚一向灵巧的手不知怎么一下打了滑,扁圆形的香水瓶从纸盒中滑了出去,无声无息地落在地上。
奇异的香味在空气中迅速弥散开来,耶利亚感到自己仿佛被什么东西击中了要害,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事情,比如说不拆那个纸包或者根本拒绝他的礼物,那么后面的事情也许就不会发生。玻璃碎片飞溅了一地,香水在看不见的空气里蒸腾上升,耶利亚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她蹲下身想拾起那些碎片,这时候,有人把她抱起来放在了膝上,用嘴堵住了她的嘴,使她的叫喊根本发不出声音来。
中午时分,楼道里静得出奇。耶利亚静静地靠在老季怀里,既觉得委屈,又有一种慵懒的满足,连她自己都感到奇怪:她为什么要让他达到目的呢?她其实完全可以不听他的,如果当时喊起来,肯定会有人听得到的,那么她为什么没喊呢?到了现在这一步,以后该怎么办呢?
那一天,整幢楼里的人们都闻到了那种奇异的香味,他们相互询问道: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老季走后,耶利亚独自一人愣愣地看着她的打字机,心想:“看来,管束他们说的都是真的啦?”她想起那个中午,电扇在头顶呼呼啦啦旋转时的情景,所有的人都离去了,却把那句话丢给了她,硬硬的,莫名其妙的一句话,完全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几天以后竟然成为事实,耶利亚越想越不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老季是耶利亚性的启蒙和开发者,他不分白天夜晚的纠缠把耶利亚身体内部某种欲望撩拨起来。老季每次来找耶利亚打字,办公室里只要没人,他就要情不自禁地做一些小动作,抚摸她的肩膀或者头发。她站起来去够架子上的东西,他便不失时机地把手伸到她裙子底下。有天耶利亚在书架上寻找一份老季需要的文件,老季坐在她的红椅子上等着。那天耶利亚穿了条牛仔背带裙,老季的手从她的小腿一直往上走,耶利亚装做没这回事,继续找她的东西。
耶利亚把找到的那份文件交给他。
“这么快就找到啦?”老季有些不舍地抽出手来接那份文件。
老季和耶利亚这种不明不白的关系使耶利亚感到有些讨厌,但有的时候想起来却又有点喜欢,他毕竟很会疼人,对她又是百依百顺,真要跟他翻脸好像有点不忍心。
超能所里流传着各种各样有关耶利亚的传闻,一向清静的打字室一时间热闹起来。有的人有事没事就往耶利亚屋里跑,或者打那种莫名其妙的电话,耶利亚想,她也许该找一个像模像样的男朋友了。
有一天,耶利亚发现自已看中的人竟是王定红的男友管束。
管束的舞跳得相当好,每回所里开舞会都有不少女孩缠着他请他带舞,他的那位老同学王定红更是使出浑身解数,好像橡皮糖一样粘在他身上。等到下一支比较难跳的探戈曲子响起,管束忽然转过身来小声问耶利亚。
“咱俩来段探戈如何?”
耶利亚抬起头来望他一眼,两人相视一笑,笑容里有了一种用语言很难表达的默契的成分。耶利亚站起来,把手搭在他的肩上。
“看你这么忙,我都不好意思跟你跳舞了。”耶利亚凑近他耳边小声说。
管束说:“我是想要的得不到,不要的大把大把地抓。”
听了这话,耶利亚心里有点得意。她说:“要不要我明天到你们办公室去找你?”
管束说:“你别去,我们实验室一般人是不让进的。”
“为什么?”
“我们实验室有辐射,Q射线可能对人体有害,我们都是穿着厚重的防护衣在里面工作的。”
耶利亚并没有把管束的话当真,左耳朵进去,右耳朵就冒出来了。
耶利亚说:“我什么都不懂。”
管束笑道:“我知道你不懂。”
有一束神秘的紫光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绕着管束的头顶打转。尽管此刻舞厅里的灯光很暗,耶利亚还是在人丛深处看到了那双被嫉妒烧灼、几乎要淌血的眼睛。
“管束,今天晚上有人要睡不着觉啦。”
管束故意装傻,问道:“是谁呀?”
“王定红呗,还能有谁。”
耶利亚原地转着圈,裙子高高地飞扬起来。这时候,舞场上的音乐正达到一个高潮,管束不知是有心还是无意,故意让耶利亚来了一个“下腰”的动作,同时俯下身去作吻状,音乐在这时也恰好收了它的最后一个音符,连那束紫光也被它收去了,舞场上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寂静和黑暗。耶利亚这时忽然有一个奇怪的想法,她觉得有什么人在跟他俩搞恶作剧,音乐和人群转瞬间都不见了,舞场上空空荡荡的,什么也没有,好像秋天收割后的田野,热闹过后愈见空旷苍凉。
闷雷一样的掌声和尖厉刺耳的口哨声是在短暂的沉寂过后响起来的,这时候,灯也亮了,一张张人脸从黑暗中浮凸出来,耶利亚再一次看见那双因嫉妒变得丑陋而且血红的人眼。
耶利亚凑近管束的耳朵小声对他说:“哎,你那位老同学王定红,她会不会杀了我?”
管束耸耸肩道:“有这种可能,她是研究生命科学的。”
“那么你呢?”
管束用食指点了一下耶利亚的嘴唇道:“这是秘密,不能告诉你的。”场上的光线忽然又暗下来,那束紫光再次出现。耶利亚看到王定红愤然离去的背影。
“这下好了,我们可以撒欢儿跳了。”
“为什么?”
“明摆着嘛,管你的人走啦。”
“我?有人敢管我?真是天大的笑话。”
管束带着耶利亚像陀螺般地飞转起来,把那束紫光远远地甩在了后面。
舞会上遇到的每一位科学家都很神秘,耶利亚的好奇心导致了“Q射线事件”的发生。
一天下午,耶利亚到管理很严格的保密区去玩,她是趁着门卫上厕所的时间溜进去的。在保密区内耶利亚看到狭窄的、像迷宫一样的过道,几个身穿褐色防护衣只露两只眼睛的怪人正在过道内机械地行走,他们面无表情,像机器人一样不通情理。耶利亚本想向他们打听一下研究生管束的实验室究竟是哪一间,可现在她又改主意了,心想既然来了就该四处走走看看。
保密区内迷宫一样的设计让耶利亚感到很有趣,这里和耶利亚工作的那栋小白楼完全是两个世界,里面找不到一丝自然光,取而代之的是紫而微蓝好像舞会上用来做底色的那种光线,灯管的形状是圆环形的,一个挨一个地钉在走廊的天花板上,好像一只只暗淡无光的死鱼眼睛。
耶利亚也没想到自己会迷路,可是走着走着她就辨不清方向了,她像一个在森林里迷了路的孩子,转了一圈又一圈,把来时的路都给忘了。这里的每个房间都有着相似的色泽幽蓝的玻璃窗。门是敞开的,凝住不动的,里面没有一丝风。耶利亚甚至怀疑这个神秘的高科技工厂是不是在地下建造的。可是回想起来耶利亚好像并没有走过明显的台阶和楼梯之类的东西,那么,她是怎样从地面上走到地下来的呢?耶利亚百思不得其解,只得机械地迈动双腿继续往前走,其实她已经完全没有了目标,也辨不清方向,她只是懵懵懂懂往前走,走到哪儿算哪儿。
此时的耶利亚已是又累又渴,可是这里面连个人影都见不到。耶利亚越想越害怕,这下她真的有点儿慌了,她推开一扇又一扇式样相同的门,没有人没有人没有人,到处都没有人。
“管束,管束――”
她听到自己纤弱苍白的声音很快就被死一样的沉寂吞没了,耶利亚很快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她想,外面的天很快就要黑了,如果到了下班之前她还没办法走出去,那么今天就只能在这森冷幽暗的地方过夜了。
不知是什么原因,耶利亚腕子上没有戴表。所以她这回不仅迷失了方向,同时还迷失了时间。地面上没有人知道她上哪儿了,老季一定还会四处找她,耶利亚想起三天前自己曾经答应过今天晚上陪他去听音乐会,可现在她就这么不明不白地失踪了,就是死了也不会有人知道。一想到这儿,耶利亚忽然感到很伤心,自己怎么会落到这般田地呢?几个小时前一切都还是好好的呢。
耶利亚走不动的时候,就不再强迫自己继续往前走了。这时,她发现自己正站在一间敞开着的银亮耀眼的金属门前,她探头往里看了看,见里面又深又大,便迈腿走了进去。
眼前出现了奇妙的色彩斑斓如同幻觉一样的景象。
这是一间像天文馆或者三百六十度环幕电影院一样的圆形房间,四周围的墙壁上满是图片或者投影,还有些浮动在空气中的影像高高悬挂在头顶。耶利亚弄不懂这是一间什么性质的实验室,觉得好像是一座迷幻花园。
那些彩色波纹挂图炫目的色彩迷住了耶利亚的眼睛,她感到有些睁不开眼。耶利亚眯起眼来四处张望,她看到屋子中央有一个不锈钢支架制成的高出地面的平台,不知为何,这个平台使耶利亚想到了“手术台”之类的字眼,谁都明白,这是个很不吉利的字眼,可是这会儿耶利亚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她困得睁不开眼,又累又渴,她感到自己好像被什么力量控制着,抬腿走上台阶的时候身体轻飘飘的,仿佛电影里的慢镜头,又宛若一支轻曼柔美的蒙古舞。蒙古舞在耶利亚的心中一向是一种勇猛阳刚的舞蹈,有天她和老季一起去看了一场独舞晚会,改变了她的这种印象。
耶利亚走上平台,就像那个蒙古舞演员走上舞台一般。天幕是黑的,四周也许是茫茫的草,也许是无边的海,也许是赤 裸的荒滩。耶利亚觉得她浑身上下的骨节好像脱了臼一般,身体酥软如泥。她躺下来,把身体放平,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舒适与眩晕,她想她就快要睡着了。
耶利亚醒来时发现自己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身上插了无数个电极,医生护士正在进行紧张的测试。所有人都戴着超大的白口罩,脸上的五官几乎全都不见了,只露两只眼睛。
耶利亚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正努力使自己的思绪回到沉睡着的轨道上去,可是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她为什么会在这里,能够回忆起来的倒是那些断断续续的梦境。在梦里她看见蒙古舞者的红头巾在灰暗的背景上像火苗一样鲜亮,那穗子留得很长,每动一下它就跟着在风里飘。不知怎么,蒙古舞者的红头巾又变成了给耶利亚蒙眼睛的红绸子,那是他们第一次做 爱,维东把她的眼睛蒙起来,她什么也看不见,看不见……
耶利亚看到的第一个熟悉的面孔就是管束。
管束说:“你沉睡了三天三夜,总算醒来了。”
耶利亚第一次离这么近观察管束的脸。她发现他是一个眉眼都十分经得起推敲的小伙子。他鼻翼薄薄的,鼻梁很直。“干吗用这种眼神看着我,不认识我了吗?”
管束坐在床沿上,刚才那些电极已经被护士拔去了,不过他们说过一会儿还要再来测量。
“管束,能告诉我,我到底怎么了吗?”
管束说:“你别多想,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是不是快死了?”
“别胡说八道。不过是对你进行一下全面的体检,检查完了就没事了。”
耶利亚把头歪向一边,窗户上拉着窗帘,看不出来外面是晴天还是阴天。耶利亚渐渐回想起她在保密区迷失方向找不着出口的事。耶利亚从管束口中得知,她被一种代号为Q的射线照射时间过长,又没有穿防护衣,身体内部的某些“秘密开关”可能会被改变,目前这家医院的医护人员正在进行紧张而全面的测试工作,等测试结果一出来,证明耶利亚的身体没事,她就可以出院了。
耶利亚听了管束的话,反而觉得放心了。她不知道这种“Q射线”的厉害,没有这方面知识的人反而无所畏惧。她说生老病死都是天意,是她母亲说的。说到这儿耶利亚忽然笑了起来,管束问她笑什么,她反而掩住笑不肯说了。
管束坐在床边上,伸过手来拉住她:“不行,话不能说一半。你母亲还说什么,你得告诉我。”
耶利亚看到自己放在被子外面的左手被他攥住了,攥得紧紧的。正在这时,王定红拿着一束蔫巴巴的花走进来,看见他俩拉着手,她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耶利亚没想到一个研究生竟会这么没风度。她怒气冲冲地把那束蔫巴巴的花扔在了管束漂亮的头颅上,管束还在发懵,她已经一阵风似的旋了出去,只闻咯哒咯哒的高跟皮鞋的声音不见人影了。
“她这是怎么啦?”管束用手撕扯着头发上丝丝缕缕的碎花瓣花叶子,很是摸不着头脑地问耶利亚。
耶利亚伸手帮他摘掉眉毛上的一根草叶子,似笑非笑地说道:
“你问我我问谁呀?”
停了一下又道:“你还不快去追她?”
管束用力甩着脑袋上的碎叶子说:“好好的,我追她干吗?我有病啊?”
“你就不怕她也像我一样,中了你们所说的Q射线,闹个寻死觅活?”
管束忽然间低下头来,眼睛定定地看着她的脸。
“如果你真的那么希望我去关怀她,那我可就去了啊?”耶利亚伸手拉住他:
“哎,我告诉你刚才没说完的那句话。我妈说,生老病死都是天意;我妈还说,一个人一辈子遇到什么人也是天意。”他俩正要继续深入探讨这个问题,大批的医生护士又来了,他们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仪器仪表,来势汹汹。他们面无表情,大口罩遮住了大半张脸。耶利亚身不由己,浑身上下重新被绑上无数电极。管束俯在她耳边小声说:“别怕,一切都会过去的。”
给他这样一说,耶利亚内心反而充满恐惧。
他俩的手在空中用力交握了一下,然后就松开了。
指针摇摆不定,数据噼里啪啦在显示屏上做出快速反应,医用计算机在以人脑难以想象的速度高速运转着。
耶利亚闭上眼睛,只觉得奇怪的命运就要临头了。
六
耶利亚回到所里去上班,人人拿她当怪人。躲着她,或者看耍猴似的远远地盯着她看,她一走近那些人就轰地一下散开了。中午她到食堂去打饭,大师傅给她打饭时大勺直颤,好像她得了什么传染病一般,生怕接触到她的餐具或者别的什么东西。
耶利亚总是孤零零地坐在饭堂中央那张餐桌旁,头顶上吱吱啦啦吊着一架半转不转的旧电扇。
中间那张桌曾经是全所最热闹的一张桌,全所最年轻的追求时髦的那帮人个个喜欢在那张桌旁登场亮相。现在不同了,因为耶利亚的缘故没人再来凑热闹了。耶利亚想,自己又不是得了麻风病,干吗用这种看怪物的眼光看自己呢?可是她又没办法钻到别人心里去,左右别人的思想,她只有表现出一种超出常态的高傲来“以毒攻毒”。她是那么美丽绝伦,却又十足一副反叛女孩的神情,她目光冰冷,新理的发型从前到后统统只有寸许长短,显得怪里怪气。她用一种带荧光的口红化妆,眼皮上涂着银灰色眼影。人们暗中对她指指点点,都说“你看耶利亚病得不轻呀”,“瞧她那样儿”,耶利亚渐渐与人群隔膜开来,成为一个孤独的人。
惟一与她亲近的人是管束。
管束三天两头往耶利亚工作的那幢小白楼跑,在打字室一坐就是一下午,就像耶利亚出事之前老季的表现一样。耶利亚出院之后老季就没再来过,偶尔在楼道里碰上了,老季便很生硬地冲她笑笑,然后逃跑似的脚底抹油一下子就溜掉了。耶利亚觉得很肉麻,心想,好像谁要赖上你不放似的,也不照照镜子看看你自己那样儿!耶利亚一想起他在这间打字室里的种种劣行来就感到恶心。她想起他火苗似的红舌尖狗一样地舔来舔去,想起他摘掉眼镜时瞎猫糊眼儿满地爬那样儿,想起他赤条条地跑去接电话,缩头缩脚,脚尖点地,动作猥琐之极。一想起这些来,耶利亚恨不得用刀把自己的身体刮去一层皮,只有这样才能洗清自己对自己身体的厌恶感和嫌弃感。
幸好还有管束。
管束是年轻干净的,笑容里有一种单纯洁白的味道。管束的到来使耶利亚的心好像被人举着大皮管子结结实实用水冲了一番,从里到外又透亮起来。
“怎么把头发剪得这么短?”
“我还嫌它不够短呢。”
“你那脖子上丁零当啷挂了一串什么玩艺儿?”
“你看它像什么,它就是什么。”
“我看它什么都像,又什么都不像。”
“这就对啦……”
他俩的谈话基本上遵循这种模式,一句一句简短而有劲道,从不拖泥带水。好像在玩一种智力游戏,又像电影里修剪得当的精妙对白,话里有话似的。耶利亚已经不在乎别人对她怎么看了,一味我行我素,与周围的环境越发隔膜起来,能与她对话和交谈的只有管束一个人,真正关心她的也只有管束一个人。
但是,耶利亚与管束的关系也遇到了一定阻力,这阻力主要来源于管束的前任女友王定红。
王定红虽说受过严格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理工科教育,但女人的本性是很难被“教育”这种外在人工打磨方式给阉割掉的。王定红被嫉妒烧红了眼,日思夜想也想不明白。她不明白那个打扮得妖里妖气的打字员到底有什么好?放着她这个堂堂的女研究生不去爱,偏偏要爱上她?这个问题一直像一道难解的数学题那样缠绕着王定红,吃不香睡不着,直熬得两眼发花,嘴唇乌紫,皮肤失去了原有的光泽,变成干巴巴的毛孔粗大的橘子皮。王定红心想,这样下去可不行啊,自己每时每刻都在油锅里煎熬着,而他们却像没事人似的。
王定红决定采取行动:跟踪管束。
王定红跟踪管束的想法一旦从脑海里冒出来,便像小苗破土而出一样不可遏制。她买了一双便于走路的平底鞋,走起路来像猫一样轻软无声,无论在所里还是在街上,王定红来无影去无踪,连她自己都觉得自己像个幽灵。
有天中午,太阳在天空中白得晃眼,王定红穿着她那双软底布面的小白鞋走在没遮没拦的太阳地里,她看到自己的影子小得可怜,就像传说中的灰色小矮人一般,轻飘飘的没一点质感。那幢小白楼在烈日下白得就要冒烟了,王定红觉得那仿佛是一座虚幻的楼阁,里面空无一人。她用力推了一下那扇玻璃门的黄铜把手,听到门里仿佛有人在笑,待她侧耳细听,又什么声音也没有了。
王定红是第一次到这幢小白楼里来,楼道里的寂静和一扇接一扇紧闭着的房门使她感到不安,好像非法闯人别人的领地,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
王定红什么也没看到,当她破门而人,想要抓住他们的时候,反倒扑了个空,他们根本没在屋里,打字室里空无一人,电脑开着,屏幕上没有一个字:一片空白。
王定红拿走了耶利亚桌上的一张照片,不是连镜框一起拿走的,而是把镜框背后的三颗小螺丝卸下来,抽走照片,留下镜框。她的动作快得惊人,事后连她自己都想不明白自己是怎样在没用任何工具的情况下把那三颗深凹进去的、带有十字槽纹的小螺丝拆卸下来的。她把耶利亚的那张照片拿在手里,伸长胳膊稍微拿远一点,眯起眼睛来仔细看了看,像在鉴赏一幅画的真伪。
中午的阳光使得耶利亚的面孔出现变形,她的眼睛忽然散发出一种奇异的光,刺得王定红睁不开眼。王定红慌忙把那照片藏进兜里,然后把镜框放回到原处,把桌上的一切归了归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