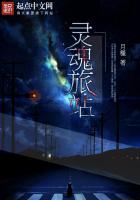春寒料峭,苏北地区一片萧瑟,破败的村庄,光秃的树枝,干涸的河沟,枯黄的茅草,正是青黄不接,万物待苏的时候。
突然,从一片坟堆里蹿出一只雪白的动物,兔子大小,尖尖的耳朵,短小的四肢,灵活的身子一蹦一跳地跃上沟岸,接着“吱”地一声快速穿过方圆几十平方公里的萧瑟平原,一路向北,转眼间消失得无影无踪。
正在这时,沟岸上的村庄里,一个妇女正躺在床上,她浑身鲜血,极度痛苦,而一双大手正从她的肚子里硬生生地抱出一个血淋淋的婴儿。
妇女艰难地看了看她的孩子,勉强挤出一丝笑容,闭上了双眼。
婆婆手忙脚乱地擦干净婴儿脸上的血污,掏出嘴里的秽物,朝他脸上拍了几巴掌,又抓住双腿倒吊,朝他脚心弹了几下,做完这些,仍然没有听到婴儿的哭声,婆婆急忙倒过来一看,顿时大惊失色,扯起一床布满血污的棉单,裹紧婴儿撒腿就跑……
琉璃镇医院顿时乱作一团,刚刚送来一个背后被扎个血窟窿的男人,这会儿又送来一个浑身青紫不哭不叫的婴儿,到处都是慌乱奔跑的家属和面色严峻的医生。
医院外车水马龙,人们行色匆匆,烦恼着鸡毛蒜皮的小事。医院内活人与死神上演着艰苦卓绝的战争,演绎着一幕幕惊心动魄的画面。
一天一夜之后,婴儿的心脏恢复正常跳动,呼吸平稳,只是整个小人儿被盖在一个大大的玻璃罩子下面。
旁边床帮上端坐着一个男人,尖嘴猴腮,眼睛似睁微闭,手撑一根木棍,脸上表情复杂,欣喜而又不无担心。
走到门口的婆婆身形一震,脸露不悦,“你来做什么?”
男人微微一笑,扬了扬眉梢,尖声尖细地说:“如果不听我的劝告,这孩子活不了!”
婆婆瞥了他一眼,不无嘲讽地讥笑道:“不要装神弄鬼,别人不了解你,拿你当神算子,我还不知道你?会被你轻易糊弄?哼!”
男人脸色一沉,低声劝道:“这孩子与其他几个不一样,大善大恶都在他身上,如果不能正确地引导,孟氏一族将会悉数灭亡,包括你,和你的孩子!”
“李叔,你说什么?”不待婆婆回应,门口走进来一个年轻男人,正是婴儿的父亲,他听闻此言,悲伤的脸上又增添一层恐惧。
睁不开眼睛的男人抬起头来,扬了扬手中的木棍,勉强笑道:“孟老八,你过来!”
婆婆有心阻止,但看了看被唤作孟老八的婴儿父亲,又看了看睁不开眼睛的男人,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你的孩子,如果想让他成活,必须听我几句劝:一、十岁前不准生活在孟庄,抱去外姓家抚养……”
半个小时之后,睁不开眼睛的男人拄着木棍走出医院,孟老八神色凝重地趴到玻璃罩子上盯着婴儿,眼睛里流出悲伤而期盼的神情。
婆婆又轻轻地叹了一口气,仿佛自言自语,“老八,听他的吧,他也算是为了孩子好!”
婴儿的父亲流下两行眼泪,无奈地点了点头。
这时,病房外一片吵杂,几个年轻人和一个老者气势汹汹地冲进来,看到玻璃罩子下面的婴儿,老者上去一把掀开,伸手就抓……
“住手!”婆婆大喝一声,飞奔上前一下把他抱住,同时大声呼救:“快来人啊,快来人啊,杀人了,杀人了——”
孟老八眼疾手快,“嘭”地一声盖上玻璃罩子,然后身子往上一趴,死死地压在上面。
老者气得大吼:“贾明明,你给我松开,都是因为这个死孩子,他一出生,我的女儿就,就,”他突然停下,接着大哭起来:“女儿啊,我的女儿啊…......”
此时,几名医生和护士跑进来,弄清情况后大声斥责老者和几个年轻人,并把他们推出病房,同时加强了防备和治安。婆婆和孟老八则一刻也没有离开过婴儿,轮流守候,仔细照顾。
三天后,了无气息的妇女被一辆骡子板车从孟庄拉出,后面跟着那名冲到医院闹事的老者和几个年轻人,悲伤、愤怒而无奈。
七天后的深夜,病房里,婴儿身上的玻璃罩子已经取走,他脸色红润,面露笑容,不谙世事地伸手蹬腿,啊啊轻叫。
那名老者和几个年轻人坐在床沿,孟老八却跪在他们脚下,低着头默不做声,空气凝结,气氛压抑。
良久,老者终于叹了一口气,无可奈何地摇了摇头,压低嗓门说道:“孟老八,我答应你把这个孩子抚养到十岁,但我只能管他穿暖吃饱,至于其他的,淹死也罢,摔死也罢,我可不负责,你要考虑清楚!”
孟老八抬起头来,眼眶里浸满泪水,“爹,我谢谢你们,我替孩子谢谢你们,只是……”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老者明显愠怒起来。
“这孩子与其他孩子不太一样,我求求你们一定要保密,他的藏身之处,他的身世还有性别都要保密,千万千万要保密……”
“够了,啰里啰嗦,不像个男人,怂蛋!”老者未待他说完,气愤地站起来,指着婴儿扭头命令道:“老大,把他扔到板车上去!”然后看了看仍然跪在地上的孟老八,冷哼一声,抬脚就走。
“爹,大弟二弟三弟,我求求你们,要待他好一些,待他好一些,我求求你们……”孟老八的哭声从病房传出,但立即就被几人沉重的脚步声淹没。
一辆骡子板车,一个被布单裹着的小小婴儿,几个年轻人和一个老者,就这样,在四十年前的那个深夜,从苏北琉璃镇医院的门口悄无声息地走出,消失在漆黑的夜色之中。
第二天,婆婆和孟老八抱着妇女和孩子的遗像返回孟庄。从此,在孟庄,理所当然地死去了一名孟家爱字辈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