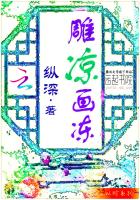王坨子说,就是刚才的那个骑车的少年,风一样的破门而出,所以门就此关不上了。可是——这又怎么样呢?自始至终,我才是那个靠着门来算时间的笨蛋罢了,唯一确信的一点是——在没有认识江沁以前,我不会犯这种低级错误的。她是一个真的笨蛋,和李沁一样的笨蛋,如果说——笨,也是一种会遗传的病。
等下,可是为什么,她不在这里,我不能打电话给她?脑子生锈了,我是在这么晚的时候才想起来擦。我决定把电话拿出来,它就在我整洁的衬衣口袋里。一打开屏幕,总会有蓝色的光。
我把它掀开,一股猖獗的光开始变成海啸。我成了难民,一个给予迫切知道上天何时回给我救赎的乞讨者。
她是李沁的女儿吧,然而这一点,我现在莫名的期待着最后的证实。问题是——我知道了,然后呢?我不确定我是否真的要为这个可笑的原因去报复她,然而这却与心软无关。她的眼睛里总闪着那么无辜的光,那么所以呢?
我矛盾的觉得,我其实也不会因为这另一个可笑如此的认知就把她当做那和印度恒河一样神圣的水。她很傻,却和我一样有污点。这些兴许都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必须亲耳听到,她和她妈妈曾经的故事。这这是一个无聊的证实。
我敢无聊地向您保证——仅此而已。
“打给女朋友呢?”
王坨子把水烟宝贝一样地环在臂弯里,见我没答应,他又八卦地问我说:
“是打给女朋友吧。”
“嘘。”我的嘴唇距离食指很近,我小声地说:“您,请安静。”
他笑着沉默掉,牙渍透过咧着的嘴,泛着旧镜子一样又黄又恶心的光。
我有些厌恶,不由得别过头去。
电话在这时候接通了,我能听出,那就是江沁的声音,她在对着听筒说‘喂’,有声的线条像是水里的鱼,噗通一下滑动了如水的夜空里那么深的浆:“汪……老师?”
“喂……”
手心有些湿了,不晓得是不是为着夜里太凉的缘故。
我在右手上擦了擦,之后把手机又重新放在左耳边:“为什么不等我?”
我问她:“不是说好一起的吗?”
“对……对不起”
那头的她似乎连走路都很赶时间,这一句道歉,像是毫无意义的冷风,吹得人心凉。
“我下楼的时候才发现我的脚踏车坏了,”她忙着同我解释:“很晚了,我一直看时间,可是你一直没有来,我怕爸爸担心,所以……”
“所以就不打招呼地了?”
“我……。对不起。”
她又道歉,似乎她总是以为,一句对不起,真的可以神奇到解决这个世上所有的问题。
“不要对不起。”我不得不告诉她:“这样子没有用。”
“你无端消失了,我也会担心,所有像爸爸一样关心你的人,也会担心。”
我不假思索地说:“答应等了就要做到,等不到了起码也要打个电话。难道你妈妈没有告诉你无端浪费别人的时间无异于谋财害命吗?”
她又再一次地沉默了,记得上一次沉默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我能想象那头的她是怎样委屈地嘟着小嘴儿,一提起妈妈这个温暖而生涩的字眼,似乎全世界都欺负了她一样。
我又欺负了她一次,尽管我不大确定我是否是成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