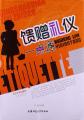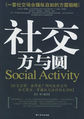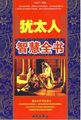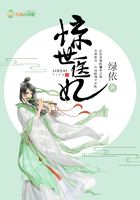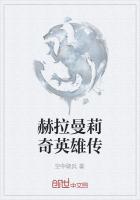作者虽然寄情山水,不时为大自然的神奇造化所陶醉,但他并没有超然世外。联想到居住在一些深山老林间的山民,眼前虽有优美风景,但交通不便,生活艰苦,他不禁为之叹惋,从而为其表现山水情愫的作品增添了一份难得的人文关怀。
读过熊宗荣的散文,总觉得那种淡雅的色彩之中潜藏着某种比较独到或者说属于他自己的散文品质。就像一个人,看上去并不生疏,也没有外露的特征,很难把握他的性格。初读熊宗荣的散文,就是这种感觉,似乎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的,一五一十地向你讲述着他的见闻,并且很少流露自己的感受,也看不出作者的刻意追求,所以让人一时说不准他的散文风格。
熊宗荣作品的特质,蕴含在其文字的血脉之中,只有细细品来,才能慢慢体味到他这种散文所具有的“原生态”特色与美感。
熊宗荣先生是一个地市的党政领导干部,因为文学情结,使他得以长期坚持业余创作,勤奋笔耕,曾经在湖北地区和其他省市的报刊上发表过不少作品,出版过多部个人专集。近些年来,他的散文创作主要致力以山水游记,他从吐鲁番的葡萄架,写到漓江风光,从长白天池写到台湾的日月潭,还专题出版了一部记录域外风情的游记。
无论写到哪里,他总是那样娓娓道来,自然亲切,那么沉稳,那么坦诚,保持着从容淡定的散文风格。
“草原的上空,天蓝得耀眼,朵朵白云无依无托,缓缓飘移,有几只苍鹰在白云下自由翱翔。草原的远处,有莽莽群山,山与山的深壑间,有浩如烟海的白云缭绕。山的阳坡长着茂盛的青草,阴坡则长着大片葱郁的森林,森林碧绿苍翠,青黛一色。”这是作者在《最后一方净土》中描写喀纳斯风情的一个片断,看上去不动声色,平静叙来,却能让人感受到浓郁的诗意,让人随着他的描述走进那一幅幅山水画图,走进奇峰异水之间,心灵情不自禁地产生一阵阵悸动。
又如,他写大海,不但描绘了海洋的辽阔无垠和蔚蓝深沉,而且还细致地观察了海浪袭岸的情形。他说:“海浪像一字长蛇阵,横亘千里,由远及近,由缓到急。快到海岸时,那海浪犹如运动健将,来一个猛烈冲刺。”写到此处,作家的笔墨并没有停留在海浪的自然形态上,他说“大海只是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知疲倦地重复做着无数次相同的游戏。那海浪看似凶猛,其实倒挺温柔,它排山倒海而来,凶强狭悍地搂住那静若处子的银滩,在她秀美腼腆的脸上猛亲一口,旋即松手,缓缓而退,回归大海。”短短一段文字,并且还是那种淡淡的语气,却以拟人手法写出了海洋的性格和规律,写得生动可爱。
因此,我们认为熊宗荣的作品具有自然天成的“原生态”散文审美特点,当然不是将它等同于那种缺乏激情,缺乏技巧的平铺直叙,他的高明之处在于“藏巧于拙”,他所追求的是一种平淡中见奇崛的艺术境界。比如,面对西域的古国废墟,他是这样表述的:“我们站在古城遗址那残留的土夯城墙下,透过眼前的断井颓垣,和满目萧瑟破败的黄土,一阵阵地感受到那遥远悠久的苍凉,和波澜壮阔的历史烟云演示的震撼!”这样的段落,在熊宗荣的文字中大概是比较激扬的,但依然没有改变他作品的总体艺术风格,依然波澜不惊,却使读者从他勾画的苍凉废墟中领略到历史的沧桑。他的这种“平静”,往往更能产生出艺术冲击力。
当然,我们说熊宗荣的作品里储积着静若秋水的美感,也不等于说它没有起伏。例如,在记述清江漂流的过程中,对于这里的滩急水险,作者在进入正面描写之前,通过船工的动作和神情进行了渲染。当船行驶到“虎三跳”时,他这样写道:这时,“坐在船后的两位船工立即提起桨板,坐正了身子,眼睛紧盯着前方。那神态,活似两位即将展开决斗的武士,弄得全船的人都紧张了起来。”这种从侧面着笔的表现手法,更能起到扣人心弦的效果。
作者虽然寄情山水,不时为大自然的神奇造化所陶醉,但他并没有超然世外。联想到居住在一些深山老林间的山民,眼前虽有优美风景,但交通不便,生活艰苦,他不禁为之叹惋,从而为其表现山水情愫的作品增添了一份难得的人文关怀。
熊宗荣的散文看似不事雕琢,但字里行间你仍然能够感觉到他对于文字的精细化处理的重视,感受到他遣词酌句的工夫。为了表达山水之美,他不说“留恋”,而用“贪恋”;他形容山峰的姿态,用了“羞怯万状”,一下子就把静态的群山写活了,写得富有灵性。这样的文字,有利于增强作品的诗性,也能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熊宗荣的散文,不但意境开阔,情感充沛,而且文字细腻优美,达到了较高的诗化程度,散发着一股兰草般的淡雅幽香;既实现了他对名山胜境的忠实记录,又赋予了作品较高的审美品位。品读他的作品,自始至终有一种宁静之感,在宁静中享受他笔下的碧山秀水,享受他为我们营造的诗情画意,享受他那如淡淡水墨的文字。他有些篇章还注重从文化角度进行考察着笔,具有一定的文化意蕴、文化含量和思想深度。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
——《古诗十九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