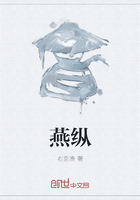历史学不会同政治学争地位,政治学也不会同历史学比高低。它们之间是不同学科之间的平等关系,然而史学家与政治家之间的关系就比较复杂,特别是与那些有权有势的政治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微妙。
我相信,史学家与政治家主观上都是想友好相处、互相合作的,因为一般说来,他们不仅有共同目标,而且还有许多共同利益,大家毕竟都是生活在同一国土上与社会中。史学家其实是最好管理的公民,他们多半老实巴交,既不想升官发财,又不爱惹是生非,充其量无非是想拥有一片可以独立研究与自由思考的空间。政治家当然比史学家伟大得多,他们不仅要忙于安邦治国,而且还要努力实现政党的和自己的宏伟目标,掌握政权的政治家的一言一行都关系着国计民生。不能说他们不重视史学,但他们更为重视的是史学家应该如何协助自己安邦治国,特别是为自己的政治方案及其实践寻求历史借鉴。史学家也许会受宠若惊,但随之而来的是对于独立研究空间缩小的担优;他们希望保持史学本色,尽可能避免泛政治化。
史学家并非不想与政治家保持一致,但他们多半恪守培根的箴言:“真正的同意乃是各种自由的判断通过恰当的考验而归于一致。”学者在其学术领域应有自主权利,他们不希望有过多的政治干预与指令约束,并以“苟从与附和”为耻。即使是“自由的判断”,史学家也比其他一些学科专家麻烦更多,因为他们不仅需要掌握大量史料,而且还需要有较大的时间跨度以供宏观审视。法国年鉴学派是强调长时段研究的,哲学家保罗?利科认为这是由于受到经济学家的启发:“经济学家的趋势和周期概念启发了历史学家,使他们学到了长时段概念,而这种时间概念也是政治体制和政治态势的时间。”(《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中译本,上海,1995)有些历史的是非功过,并非短时间内所能判断,往往需要十几年、几十年或者数百年,才能作出比较合理的解释与判断。古人常说的“盖棺论定”,就是这个意思,而即使盖棺也难以论定的历史人物岂非也大有人在!林则徐150多年以前发出的“青史凭谁定是非”的喟叹,至今仍然感人至深,特别是容易引起我们历史学家的共鸣。
因此,历史学家常被讥刺为迂腐,不通人情世故,简直是呆头呆脑。在当今这个功利主义泛滥的世界,史学与史学家受到冷落是必然的。但史学家历来并不缺乏自信。司马迁早在2000多年以前即自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何等气概,何等担当!西方史学家,特别是近世史学家,虽然没有什么载道、资治或惩恶劝善之类伟大传统,但也有不少情深意挚的自我期许。马鲁说:“我赋予历史的一项基本功能是:使往昔的文化价值历久常新,从而丰富我的内心世界。”(《论历史认识》,转引自利科《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把生命奉献给社会主义的布洛赫对史学更是一往情深。他说:“历史学以人类的活动为特定的对象,它思接千载,视通万里,千姿百态,令人销魂,因此它比其他学科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伟大的莱布尼兹对此深有同感,当他从抽象的数学和神学转向探究古代宪章和德意志的编年史时,和我们一样,亲身感受到探幽索奇后的喜悦。”(《历史学家的技艺》,中译本,上海,1995)
我毫无王婆卖瓜之心,因为史学的价值已是客观存在,且为古今通人所理解。我只想唤起政治家们的注意,史学是一门具有独立品格的学科,决不是一种可以任人随意摆布的小玩意儿。我们过去曾批评过胡适,说他不该把历史比做一串大钱或百依百顺的女孩子,但就在我们这些批评者中有些人比胡适走得更远,把历史看成单纯是一种编纂手艺,而不必考虑是否有充分的史实依据。所谓史学为政治服务,就是意在把史学变成宣传,变成为某一时期政治中心任务的舆论造势,或者是为某一政策的出台作“学术”注解。
我在评论《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时曾经指出:“作为一个史学家,如果没有自己真诚的科学追求,没有维护历史真实与坚持科学真理的勇气,甚至随时要看某些有影响的人士(甚至是外国人)的脸色办事,那就是徒有其名而无其实。十年浩劫期间,由于极不正常的政治环境,许多人(包括我们史学界)或多或少说过一些违心的话,内心的痛苦自然难以言说;而科学的尊严也受到肆意践踏,其痛苦更有甚于自己在人格上所蒙受的羞辱。这样沉痛的教训,难道还不足以使我们警醒过来吗?”(《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重提这段往事,并非为了重新挑起政治家与史学家之间的争吵,仅只为了敦促政治家进一步理解史学家的内心衷曲,更加尊重史学自主与史学家的独立人格。我相信,只要加强相互沟通,增进彼此理解,政治家与史学家之间一定能够建立良性的互动关系,而那将是我们民族很大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