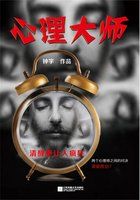立春刚过,阳光明媚,照得房顶、草坪上的积雪斑驳如素描,专业作家柳宛如心中一喜,头刚伸出窗外,一股冷风扑面而来,冷得她打了个寒战,忙缩了进来。整整一冬天,除了上班和非去不可的应酬,她基本上都待在家里,听听音乐,看看书,然后写作。再然后,跟那个伦理学教授约几次不咸不淡的会。
刚上网,手机短信嘀地响了一下,她正在看英国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啤酒谋杀案》,五个嫌疑人都有可能杀人,她不忍留下悬念,没有理会。短信嘀嘀嘀地不时提醒着,她打开手机一看,一下子停住了翻书的手:天不冷了,周六到森林公园寻春如何?号码是陌生的,但语词却传递出非常熟悉她的信息:天不冷了,知道她怕冷。到森林公园寻春,知道她平素的爱好。这个短信激起了她的好奇。她没有急于回复,继续看罪犯是谁,结果一个字都看不进去了,脑子被一个念头环绕着,这人是谁?心乱了,再紧张的故事也提不起兴致。她关了电脑,走进客厅,放了一盘她喜欢的CD《春江花月夜》,然后半依在沙发上,用牙签扎着草莓,边吃边思考着如何跟这个陌生人斗智。她喜欢这种游戏调动起的高涨情绪,因而不想轻易让它消失。
草莓的味道鲜嫩,这在冬天少见。新鲜而饱满的汁液、再加上春江花月夜的浸润,调试得她的心灵也莫名的妖娆起来,她回复的手指变得灵活而多情:雪天没有月下挑琴的司马相如,更无千里共婵娟的苏东坡,了无生趣。写完,想了想,按了发送键。然后又挑了一只草莓放进嘴里,边吃边走上踏步机。
短信提醒很快响了,她为了拖延猜测的乐趣,继续在踏步机上消耗热量。
身上微微出汗了,她停止锻炼,拿起手机,短信是这样的:贾宝玉踏雪访梅、张岱驾舟湖心亭看雪,趣味多多。
这样的回答,在柳宛如看来虽然对得马马虎虎,可并非自己想象中那么妥帖,但这个人看来还是蛮有情趣的,我再逗他一逗:贾宝玉踏雪访梅见妙玉,张岱看雪遇上了金陵知音,森林公园会的又是何人?
发送完后,柳宛如的心跳快了,再也无心听音乐,也不吃草莓了,闭着眼睛静等回复。
恼人的短信一直到柳宛如的肚子饿了,也没有再来。
柳宛如吃了个汉堡,喝了杯纯牛奶,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把那个陌生电话调出来,查了半天通讯录,也没查出这人是谁,一阵困意袭来,倒头就睡。刚睡着,短信响了,她仍然闭着眼睛,不到五分钟,就坚持不住了,打开一看,不禁笑出了声:我不是银样镴枪头,汝也非多愁多病身。我是使君有妇,卿也定罗敷有夫。
还跟我掉书袋子了,想摆出自己读过几本书,那我再撩拨他一下。柳宛如借用刚看的古典名剧《牡丹亭》里的唱词回复道:
莫不是莽张骞犯了你星汉槎,莫不是小梁清夜走天曹罚?发出后,才知自己以书生柳梦梅的口气说的,对方若读过此剧本,一定会嘲笑自己的称谓错落。可是信已发出,覆水难收了。
对方没有马上回,柳宛如极其得意,想着一定是去查书了。正想着短信来了:
俺不是赵飞卿旧有瑕,也不似卓文君新守寡。落尽梨花月又西,当时只道是寻常。
这人还喜欢纳兰容若?沉吟片刻,回复:谁翻乐府凄凉曲?
回复:小姐,我曾伴你西岳石下眠。
原来是他!他!他!
柳宛如心里一阵搅痛,脸色苍白,手捂胸口,再也没有心情斗智了。
离周末还有整整一周,她想对方是想折磨自己。一直到晚上,她也没有回。
单位的事不多,要是忙就好了,可是机关永远是:清茶一杯报纸几份,从上班翻到下班。到了第三天,她回了:没空。
她等着对方的回答,一天没有回音。
到周五了,对方的信息来了:我去森林公园了,严冰已经融化,鸭子在水中游戏。真的春来也。
她情不自禁笑了,回复:严冰还在冻着。
跟你相恋三年零一天,我何时骗过你?
柳宛如看了两遍,删掉。
见还是不见,她真的没有主意,就打电话给闺密李可儿。只要心中有了烦闷,好朋友李可儿就是最佳的诉说对象。她俩虽不是同学,可是同乡,有许多的共同回忆,而且李可儿喜欢看书听戏,有时还写些小东西让柳宛如找报纸发发,这使得她们就有了很多的话题。李可儿在一家大医院当妇产科主任,快人利嘴,心地善良。最主要的是所有的话说给李可儿,就像进了保密室的文件柜,绝对不用担心她会给你泄露出去。
李可儿刚一拿电话,就开始诉苦,儿子学习成绩一般,没考上重点中学,丈夫刘铭忙着搞科研,整天不着家。李可儿知道柳宛如一般打电话,就是心里烦了,要给她倒苦水。便适可而止地草草说完自己的烦心事,静听柳宛如诉说。听完,她说这样的约会我建议不去,一个人不能两次蹚进同一条河流,再好的爱情中间有了裂缝,照出的人影都变形。
我……
你这么多年还想着他,对不对?
柳宛如被李可儿点到穴位上了,只能沉默。
那就去见见,也无妨,只是不要让男人几句好话就骗得不知所以然了,这样到头来吃亏的往往是我们女人。
柳宛如得到好朋友的鼓励,却并不踏实。任何人,别人的意见永远是参考的。一会儿这么想,一会儿又那么想,最后还是拿不定主意。
第二天上午九点,她发了一条:我今天有事。
对方回道:上午有事下午见,下午有事晚上见。
晚上能看到春吗?
可以,坐在水边咖啡厅就能看到窗外水中涌动的春影。
柳宛如想了想,回复:下午我尽量吧。
不见不散。
柳宛如先到经常去的美容店做了皮肤护理,然后把衣柜翻了个底朝天,总算找了身满意的衣服。出门并不急于去公园,又到平常爱去的一家叫彼岸的书店消磨了一个小时,最后才到达公园,比预定时间晚了半小时。
咖啡厅没人,她走出门,湖面真游动着七八只鸭子。已经有二十年没有见面了,她还是一眼认出了坐在湖边的他,他在专注地盯着水中的鸭子,是没发现她的到来还是故意装着?
柳宛如犹豫了一下,走到离他约有一米的地方,停了下来。不该心跳的年龄,她的心跳得竟比平常还要快。
他仍然望着湖面,说,我没骗你吧,春天来了。
原来他已发现了她,只是她没想到她想象了很久他们二十年第一次相见,却是以这样静默的方式开场,让她甚为诧异。原本热热的心瞬间凝固,冷冷地说,找我啥事?说,我还有事。
他仍然凝视着远处结冰的湖面,说,你看到没,那冰层下有鱼。
她思索着他的话意,想了一想,回答,我回了。
他站了起来,这是他们第一次四目相对。二十年前他们分手后,虽然她远远地注视过他,都是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留在她脑海中的他,还是年轻时的模样。现在她看到了一个标准的中年男人的模样,头顶毛发稀少,眼袋突出,身材渐胖。
他也打量着她,想必感觉跟她一样。
我是不是老了?
我不也一样!
我们不该见面。
我很想你。他说完,快步走进了咖啡厅,她犹豫了一下,感觉自己是被一股说不清的力量推着跟在他身后。
咖啡喝完了半杯,俩人谁也没有主动开口,音乐轻柔地响着,他们像两尊雕像一样,木木地各自坐在桌子的两边,一个望着窗外的湖面,一个不时地打量着咖啡厅的四周,尽量不跟对方的目光交融。这样的相会实在了无生趣。柳宛如从窗外蛋青色的冰面收回目光说,我回去了。
他这才扫了她一眼,右手指轻轻地划着桌面,划着,划着,手就移过来了,她快速地收回了放在桌边的胳膊。
这么多年,你是不是一直恨我?
她回过头,望了他一眼,摇了摇头。
我恨我自己。真的,这二十年来,我一直在恨自己,恨得年华都已远去。那天我一个人到这个公园去散步,看到冰已融化,忽然就想跟你联系。趁我们还算年轻,趁我们身上还没有散发出老年的体味,趁我们还没有老到让对方讨厌的地步,心平气和地谈一谈,像朋友般那样。
她仍然没有说话。
男人说着,从手提包里掏出一张油印小报,递给她。她机械地接过,报纸发黄,折痕处已看不清字,有些地方已经断开,然而像捧一张珍宝似的,她双手接过打开来,思绪一下子拉回到从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