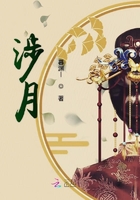老板掀开白布盖着的一幅画,对曲清歌说:“曲同学学的是游戏人物设计,原画的功底自然是有的,我这里有张油画需要转成彩铅画,送到美院附中给学生当范本用。本来是要我的一个学生画的,但是他临时有事,这一耽搁就得好几周,我被那边催了几次也不太好意思再拖下去,画廊最近又忙的厉害,我的人一个当好几个用,你要是方便,能不能帮我把它画下来?”
那是一副静物油画,标准的入门临摹范本。
曲清歌记得,只要老板觉得哪幅画适合做教材,就会把它用各种画法‘翻译’过来,既能给自己人练手,发现失误的地方,又能方便他特立独行的‘癖好’。叶柠以前就经常帮老板转水彩,素描和彩铅,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老板的这个习惯还是没变。
曲清歌很想说好,很想在彻底离开前再感受一次,但是,只要她动笔必然就会露馅,老板可不会相信什么模仿,学习,单单几个动作就能让她原形毕露。
无奈之下,曲清歌只能用最沉重的伤口还拒绝他的请求。
她把袖口撩起来,让支老板看到她手腕处的伤口,“老板,我的手受过伤,现在大多数时间是在做理论研究,除了必要的作业我已经很久不画了,您还是另寻他人吧,抱歉。”
那道伤从手心往上蔓延了大半个小臂,就算时隔多年再看,依然能想起那蚀骨的疼。
老板被那道可怕的伤痕震惊,久久不能言语,那么突兀的伤口该是受了多重的伤?一个画家伤了手就等于要了她的命!
“这是......?”
曲清歌用左手沿着伤疤的痕迹一路抚过,不在意的说:“每天画半个小时就是极限了。”
每多一分钟,疼痛就会加深一分,找不到根源在哪里,像是从骨缝里渗出来一样,疼到了神经深处。
老板无不惋惜的问,“意外?”
是意外吗?曲清歌这样问自己,或许应该是她的意料之外,他的意料之中。
“不是。”
淡淡的两个字让老板再次惊讶,“那是......?”这么深的伤口,若有人有意为之,那是打算要她的命吗?
曲清歌感觉得到老板的惋惜和慢慢滋生的心疼,轻笑了下说:“我还活着。”
我的‘意外’,让我活了下来,那么,我的活着就会成为你的‘意外’,我们谁也逃不掉。
老板重重的叹了口气,拉起白布重新把画盖了起来,又走到窗边把半合着的窗帘拉开,最后,才回到原处对曲清歌说:“都过去了。”
简单的算不上安慰的四个字,让曲清歌的伪装消失殆尽,她压抑着喉间快速涌起的酸涩,狼狈的低下头。
爱会散,恨会生,可是再多的怨恨还是比不上那些仍惦记着她的人的一句安慰,她还是她,就算心死了,还是当初那个善良的她。
“老板,我先出去了。”曲清歌低着头说,嗓子里发出来的声音软若的让她害怕,她不能再接受这种类似温柔的东西,只能逃也似的躲开。
出口,曲清歌匆忙的朝着来时的方向跑去,听不到那名员工和她打招呼,看不到有人对她微笑,感觉不到身体撞上画框的疼痛,所有的感官都聚集到了不远处的那个出口,那是可以给她安全感的地方。
“叮呤......”车钥匙掉在地上发出清脆的声响,曲清歌不安的情绪模糊了她的视线。
她找不到她的车,找不到她的钥匙,打不开她的车门,进不去那个可以给她安全感的密闭空间。
曲清歌靠着车门蹲下来,双手紧紧的抱住自己,无意识的轻喊,“尔焓,尔焓,尔焓......阿亦......”
是谁说的忘记?是谁说的报复?到头来,还是会在茫然的时候不自觉的想起他的好,想起他的怀抱。
“小姐,你没事吧?小姐......”
迷迷糊糊中,曲清歌好像听见谁在叫她,隔着迷雾,恍若隔世。
“阿亦......”
“阿姨!”
急切清晰的‘阿姨’,掩盖了曲清歌口中试探模糊的‘阿亦’,他们看到了曲清歌没有焦距的眼睛,可谁也不知道前一刻她多怀念的喊过一声‘阿亦’。
“阿姨,您没事吧?!”依旧担心的语气,让曲清歌有些想笑,她什么时候变得让人这么避之不及了?可是僵硬的四肢和表情冻结了一切,她笑不出来,更哭不出来。
高贵的女人回身拍拍那人的手说:“阿亦,就是个小姑娘,我能有什么事。”
女人是苏齐的母亲,齐玥,亦如沈亦杋的母亲,而那个将曲清歌视为蛇蝎的男人就是沈亦杋,是曲清歌在潜意识里想起来的人。
“阿亦,你帮我找钥匙好不好?我把钥匙丢了,那上面有家里的钥匙,尔焓说他不在的时候我要带好钥匙,不然,我会回不了家的。”
曲清歌低头诉说,她不清楚自己说了什么,只是下意识的觉得应该找那个‘阿亦’帮她,他是她的整个世界。
可是,她的‘下意识’没有告诉她,她的‘整个世界’要加上曾经才是完整的,他,曾经是她的整个世界。
齐玥推开挡在自己身前的沈亦杋,想要帮曲清歌找钥匙,她是个眼皮很薄的人,见不得别人这样。
沈亦杋却深知曲清歌的乖僻和冷情,她可以笑着说杀人是因为她高兴,可以毫不犹豫的毁了一副让人沉醉的画作,甚至差点在校门口故意撞到阿柠,这样一个心肠狠硬的女人绝对不能靠近,也许她现在的虚弱就是下一刻出击的伪装。
得不到回应的曲清歌抬起头,一双迷离的双眼突兀的撞进了沈亦杋眼里,痛苦,依赖,思念,煎熬,那里面包含了太多的情绪,多的他抓都抓不住。
“阿亦,我要回家......”
眼里,声里是挡也挡不住的委屈,难过。
沈亦杋一直认为她喊得是阿姨,可当她的眼睛对上来的时候,他有一刹那的错觉,那不是阿姨,是阿亦,但那份错觉仅仅只是一闪即逝,他忘不掉她次次刻意的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