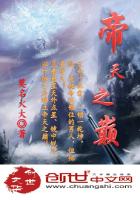我蹲在地上研究那个草人,可能是我自言自语的声音惊动了香哥,他诧异地喝道:“什么草人?那是蛹人!”
蛹人?闻言我们都吃了一惊,老二哥更是诧异,饶是他见多识广,也没有听说过蛹人是甚么。香哥稍一犹豫,停住不说了。可是我看他的神色分明是心有不甘呐。
毛毛当然也看出来了香哥的尴尬,凑上前去小声问:“香哥,这真是什么蛹人?它是干什么的?”
我听见香哥叹一口气,说:“小毛,这种蛹人,实在是歹毒不过的了,它是……”
香哥还没有说出这种蛹人到底是什么,那边哈猜已经叫喊起来:“哎呀,哎呀,看看呀……”
我气恼不过,这个哈猜总是在别人的关键时刻出来搅局,可是且慢,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香哥也停住不说了,和毛毛快步跑了过去,三两下来到了水边。
这里的水已经像滚开的沸水,在不停地冒着气泡。哎哟,我都感到了熏脸的热气直往上冒,似乎热气里含着硫磺,我的鼻腔里闻到了一股难闻的刺鼻味,“啊!”我捂住了鼻孔。
“快后退!”香哥马上醒悟过来,“这是地底废气,有毒的。”
一听是这样,我和哈猜,还有老二哥都跑得远远的了,毛毛是不是不太相信,还在那里一个劲够头朝水里望,很快他就跑回来说,“水里开锅了,八成是水底有火山,要爆发了,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这时候谁都不敢再多说,忙着躲避火山即将涌出来的热浪。可是,好一会儿也不见动静,那些气泡一直只是在冒,冒泡,山洞里都已经充满了烟味了,没办法了,我们现在连喘气都成问题了。
“戴上氧气面罩吧。”老二哥劝我们道,他这一说,我们才醒悟过来,是呀,氧气面罩呢?我一摸背包惊呆了,其实我和哈猜的氧气面罩早就弄丢了,都不记得丢在了哪里。
看我们慌乱的样子,老二哥把自己的氧气面罩塞到我手里,说:“你们快撤,跑到拐角的那边等着。”他自己却撕下衣服的一角,用石壁上的水浸湿了捂住口鼻,趴在地上朝水边爬去。
“哎,老二,你做什么?”香哥大吃一惊,连忙去扯老二哥的脚,可是只抓到他的鞋子。
“呜呜——”老二哥不敢松手,嘴里呜呜着,朝我们打着手势,那意思是说,叫我们快跑,他一会就回来。
“好吧,你们过去,我看看。”香哥说着,也学着老二哥的样子做,只有毛毛顺从地走了。
我们三人躲在拐角的地方,看着老二哥和香哥的身影隐没在了黄雾中,不一会儿,就看不见了。
呀!我惊讶地捂住了嘴巴,这可怎么办?我知道,硫磺的气体是有剧毒的,弄不好的话,他们的呼吸道会被腐蚀的。
哈猜早不知道所措了,毛毛也是一脸焦急,“这样吧,”我说,“找一找,看有没有解毒的药的。”
我知道,一会儿要是他们还不回来的话,就只有过去找,然后喂他们吃药了。
希望他们不要有事。
“金,”哈猜忧虑地说,“我们要不要帮帮他们?”
我摇摇头,是呀,我们帮不了的,我无奈地叹口气,却见毛毛鼓起了眼珠,嘴里哼道:“当然要帮的!”
对呀,我灵机一动,对毛毛说:“毛毛大叔,嘿嘿,现在,你有什么好主意呀?”
“我?”
毛毛鼓起了眼珠,一副不相信我的样子,“我还会有什么好主意?”
唉——我低下头,灰溜溜想往回走,毛毛却说:“我还不是只有冲过把他们拖回来……”
啊!我吃了一惊,这……这也太危险了,我刚想这样说,毛毛已经真地行动了,他咬住手里的长刀(不知道他到底带来了多少武器,连阿昌族的长刀也抽出来了),把衣角塞进了裤子里,弯下腰,就像一个蛤蟆一样,挪动着一歪一歪地没入了硫磺烟雾中。
哎呀,我想起来他没有氧气面罩,这要是呛着了怎么办?其实我多虑了,还没等我和哈猜醒过神来,毛毛已经拉着老二哥跑回来了,老二哥脸上一片焦黄,很像是被硫磺烟雾熏的。这种时候谁又会在乎这些呢?我帮助老二哥休息,他已经虚脱了,脸色难看,像是大病了一场。毛毛则又去救香哥了。
等毛毛返回来,老二哥已经没事了,只是精神萎靡不振,香哥则更加糟糕,已经是半昏迷状态了。
毛毛着急地呼唤香哥的名字:“香哥,香哥,冯……”
老二哥拦住毛毛,意思是这样喊叫没有用的,他换作了药膏,用一种黑绿色的药膏抹在了香哥的人中穴,他做的这一切,在我和毛毛看来是再合适不过的了,可是哈猜却像是看外星人一样,眼珠一眨不眨瞪着,一直到老二哥做完了这一切,他才缓过一口气,一连串的问题喷薄而出。
“老二哥,你这个是什么灵丹妙药,有什么用处呀?”
老二哥疲惫地望一眼哈猜,还没有回答,香哥就醒来了,很显然,他的伤势并不重,主要是被硫磺烟雾熏的。他听见了哈猜的问题,也看到了老二哥的爱答不理,就说:“哈猜,你别问了,这是老二哥自己的秘密,其实,我们中国古代很早以前就有人使用这种理论治病了,这就是中医的妙处。”
哈猜点着头说:“中医,我知道的,我们那里也有中医的,他们管那不叫中医,叫……”
“叫巫医,对吧?”老二哥插嘴说。
“对对对!”这一次哈猜不结巴了,嘴里顺流起来,不停地介绍着在泰国他遇见的巫医治病是如何的神奇的事情。
我感到忽然之间胸口憋闷,一忽儿又没有了,毛毛坐在一边,对我们的对话并不答理,但是,我的眼前怎么模糊起来,我记起来了,这是中毒的征兆……哎呀,我还没来得及说一声,就倒了下去,失去了知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