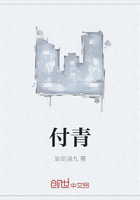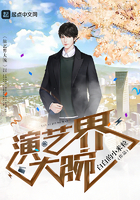苏阳波不愧是经事多年的市委书记,只见他抿了口茶,才慢腾腾地说:“干部任免提交常委会议酝酿讨论,充分听取各常委和每个参会成员的意见,最后做出决定,是我们一以贯之的组织制度,也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集中体现。一些同志有个人的某种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嘛。但是,个人的这种想法,不能感情用事,不能置于组织之上,尤其是对个别提议选拔对象的一些看法,更不能转嫁为对用人导向、对用人路线的某种不正确的看法。”说到这里,苏阳波的目光扫视了会场一周,像是垂询富有同感的班子成员。只见大家神态各异,有的随即附和点头,表示赞同,有的却回避他期待的目光,不摇头也不点头。苏阳波接着说:“如果大家没有新的意见,就可以形成决议。下面由组织部负责,及时履行任免手续。”
会议结束后,柳子奇回到自己的办公室里,已经是中午十一点多了。回味起刚才常委会议的味道,他倏地对“组织”这个概念感到陌生起来。作为党的干部、组织上的人,他以为组织就是党,党就是组织,忠于党就是忠于党的组织,难道还有别的解意吗?想着就从文件柜里抱出厚厚的《辞海》,查阅到“组织”条目——
【组织】①安排分散的人或事物使其有一定的系统性或整体性:~人力/~文艺晚会/这篇文章~得很好。
②系统:配合关系院~严密/~松散。
③纺织品经纬纱线的结构院平纹~/斜纹~。
④机体中构成器官的单位,是由许多形态和功能相同的细胞按一定的方式结合而成的。人和高等动物体内有四种组织,即上皮组织、结缔组织、肌肉组织和神经组织。
⑤按照一定的宗旨和系统建立起来的集体:党团~/工会~/向~汇报工作。
柳子奇感到自己可笑,还有几分悲壮,竟然为此查阅起资料来了。不过不需要引经据典,有一点他是清楚的,这就是组织肯定是一个集体,而不是任何个人,市委书记不是组织,组织也不是市委书记,最起码要有三人以上,才能构成一个组织,譬如《党章》规定,有三名以上正式党员,才可以建立党的基层组织。但在现实中,尤其是在以民主集中制为党的组织制度下,书记要绝对地代表一级组织,实现一定程度的意志和主张,那他必然要通过一定的手段,组织或者说团结一批人,而这批人又是非常可靠、忠心耿耿为我所用的人,才可以合乎法规、合乎情理地实现自己的主张(亦可叫做组织意图),这就是所谓的权力——具有几千年封建烙印和“中国特色”的政治。柳子奇记得不知哪本书中写到,一百多年前,美国工人运动出现了几大派别,而其中的第二派别就是由劳动骑士组成的。这个以无数次“集会”形式扩展到全国广大地区的庞大团体,起初就是在乔治·亨利等几个人的操纵下,打着代表工人阶级内部各种色彩的旗号,以地方利益特别是集团个人的意志为目标,骑士般举起火炬迅速燃遍了北美大地。想到这里,柳子奇感到自己并不可笑。
柳子奇一般是不吸烟的,这时他合上《辞海》,点燃一支香烟猛吸几口,头脑顿时酥酥的,有一种沉醉的惬意。以至中午下班急促的铃声,也没有将他唤醒。魏宏冰刚刚走进柳子奇的办公室,郑守正也跟着走进来了。郑、魏二人大概已经知道上午市委常委会议的情况了,所以没有多说什么,就招呼了柳子奇,一起去了机关小灶就餐。
午餐后不待上班,柳子奇就召集民政、财政、农业、商务、经贸、粮食等几个部门的一把手开了一个短会,安排了春节前贫困人口和下岗职工慰问的事,会后便分头“下访”去了。每年的这种慰问活动,一般是市委办和市政府办通盘安排,几大组织统一行动。对此,柳子奇也是知道的,但在市委尚未考虑这事之前,他想先跑几个地方,为老百姓早日送去党和政府的温暖。郑守正见此举有些不妥,在短会前提醒过柳子奇,但他态度强硬,郑守正就不好再啰嗦什么了。于是让魏宏冰安排了电视台、广播电台和报社的记者,随柳子奇一路而去。
当天晚上,苏阳波在家里看了本市电视台《日泉新闻》,才知道柳子奇“作秀”作到一线去了,很是恼火,于是一个电话叫来了市委常委、宣传部长董海涛。董海涛此刻正在他管辖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圈子里作“艺术指导”,接到苏阳波的电话,才依依惜别,不到十分钟就赶过来了。
苏阳波大发雷霆,董海涛愣愣忽忽,半晌才弄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于是主动请缨,表示要连夜召集新闻口的负责人,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解决好这一问题,为市委分忧担愁。说罢,就和苏阳波告了晚安。
出了苏阳波的私宅,董海涛掏出手机,让市委宣传部新闻中心马不停蹄地通知宣传口的负责人召开了紧急会议,迅速传达了市委主要领导的指示精神。与会人员随后飞速赶往各自媒体,将即将付印和滚动播出的柳子奇心系千家万户的新闻稿作了淡化处理,忙完已经是午夜时分了。其实苏阳波和董海涛并不知道,这件事让新闻口的老总们两面讨了好了:柳子奇最反感新闻“作秀”,曾明令市内各媒体不传媒或少传媒有关自己的“新闻”,但出于职责所在,这些老总们纵使有斗大的胆量,也不可“怠慢”了柳子奇这位日泉的二把手。所以柳子奇强调归强调,但他作为本市媒体的“明星”,却是不争的事实。得知市委对此事的态度,老总们感到自己再不会如履薄冰、如火焚心了。
有关这一“新闻事件”,在不经意间就悄然过去了,柳子奇一直蒙在鼓里。一天的怅惘和忙碌,使他是夜早早地进入了酣畅的梦乡。
日泉的隆冬多雾,漫天灰蒙蒙的,能见度很低。这天是个星期日,柳子奇起了个大早,拉开窗户,大雾慢慢散尽了。柳子奇什么人也没通知,只叫了魏宏冰和司机,就一路驱车,不久便到了日广高速公路建设工地某标段。现场的五号隧道继续向前掘进,三三两两的工人进进出出,工地的大小头头都不在,没有哪个工人喜欢答理驱车而来的首长。在他们眼里,县官不如现管,也许一个普普通通的工头,就是他们的衣食父母,就是他们的命运所在。魏宏冰见状,掏出手机就要给交通局局长路文华打电话,责问为什么工地没有负责人,不想却被柳子奇挡住了。魏宏冰总是琢磨不透柳市长的思维方式与工作方法,就合上手机,同他踏着泥泞,穿梭浓雾,肩并肩走了大约一两公里,随处看了看,又主动询问了几个憨憨的泥水工,方才知道了更多的情况。其实,柳子奇此时最关心的,不是工程进度和质量,而是施工安全。近来中央越重视抓安全生产,似乎不安全事故越多,反之越是不安全事故多发,安全生产越重要。这样便形成了一种安全和不安全的周期性现象。所看所闻,从安全方面讲,柳子奇感到基本满意,也没有发现不安全隐患,于是他们便沿原路驱车返回。
十点多钟,柳子奇一行返至城郊,迷雾渐渐散开了。从高处望过去,整个日泉城区像披了一层薄纱,朦朦胧胧的,间或灯火闪耀,才透出几分灵气。由于历史原因,市区建设缺乏长远布局规划,每年总是在修修补补、停停建建中轮回,放大了整个轮廓。柳子奇记得,从城区详图上看,日泉市区就像一个被推倒的宝葫芦,西边是大头,南面是顶部,再往东南边,便是蜿蜒的泉江了。柳子奇提议说,到市区转转看。司机便沿几条主要大街慢慢行驶。一旁的魏宏冰则随柳子奇的目光所视处,介绍城区建设情况。走着走着,车就到了东南的泉江边了。
几个人下了车,顶着刺骨的寒风,来到泉江河滩地。但见宽阔的河床上,沙丘漫野,一望无际。只有河床的中部,才是蜿蜒的河水。柳子奇说:“宏冰,你说,为什么这样大的泉江,水流这么小呢?”
魏宏冰说:“水土流失,资源浪费可能是主要原因吧。”
柳子奇说:“应该说还有全球变暖,植被减少,矿地开发等综合因素。”
魏宏冰点了点头。
柳子奇转过身,向城区方向看去,说:“多好的泉江啊,为什么城区建得离它这样远?”
“主要是防止水患,1981年发大水,淹了半个日泉城。”魏宏冰道。
“你看这沙石堆积,河床抬高,加之河堤垮的垮,断的断,一旦发大水,能不殃及城区吗?”柳子奇有感而发。
“是的,应该对泉江进行治理。”魏宏冰说。
“如果说把泉江治理好了,再把城区向南发展,使它紧靠泉江,会是什么效果?”柳子奇说。
“诗情画意,赏心悦目……”魏宏冰道。
“你说得没错。”柳子奇说罢,陷入了沉思。
回到凤园吃罢午饭,柳子奇坐在办公桌前批阅文件,发现文件夹下面有一个大号公用信封,取出来看了看,是一沓百元面值的人民币,里面还有一张留言条。从署名的短信中,他知道了送钱的是什么人。这几天前来凤园拜见柳子奇的人很多,这些人有的提上名烟名酒,有的干脆装了红包。他记得烟酒实在推辞不过,就放下了,而信封装的红包,他是坚决不收的,怎么办公桌上就偏偏多出了个红包呢。柳子奇叫来了容小翔帮他整理房间,又意外地发现了十几个装钱的信封。他把那些信封码在一起,掂了掂分量,沉甸甸的。他顿时感到有些冒汗。从留言条或信封下的单位落款上,他得知这些人大多是县级领导干部,有几位还是刚刚通过市委常委会议被提拔的干部,当然也还有没具名的。具名的好办,他想这是可以通过适当方式退还回去的,哪怕不惜伤情动怒。没有具名的,就只好有劳容小翔登记了。
柳子奇接到电话,是九月打来的。她说要来看望他,这阵正在凤园院子里,不知道他住哪个房间,也不知道他在不在屋子里,就先打了电话。柳子奇一忙碌起来,就忽视了九月的存在。于是不假思索地说:“我在三楼,上楼便是,你来吧来吧!”
“有客人要来吗?”容小翔问。
柳子奇说:“是啊,阳羊宾馆的老总九月就在楼下。”
容小翔有些惊奇,看了看柳子奇,笑道:“她又是要送什么来的?!”说着麻利地将礼品拾掇到了里屋。
“是啊,她要来送什么呢?”柳子奇笑道。
容小翔狡黠地看着柳子奇。
“她是我大学的同学。”柳子奇解释道。
“哦!”容小翔吱了一声。
说着响起了敲门声。柳子奇开了房门,九月走进来,见房间里有一个年轻不俗的女子,多少有些意外。柳子奇见状,道:“哦,介绍一下,她是凤园的楼层服务员,叫容小翔。”说话间,柳子奇的脸竟然红了。
容小翔冲九月恬静地一笑,点了点头,算是打了招呼。然后倒了一杯清茶递给她,说:“你们聊吧!”说罢就出了房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