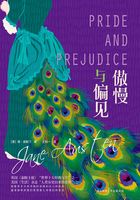张大顺一拍桌子站起。“球的毛,你别支支吾吾的,咋就是咋,痛快一点。看你这尸从包样,我都替你害羞。”
见石柱痴愣着不言语,就又说:“看样子,你真的没动过她,也不想动她。那好,我今天来就是这个意思——既然你没动过她,那她就还不是你的婆姨,你又不想让她成为你的婆姨,还要把她交回到人贩子手中。与其那样,还不如转卖给我兄弟二顺好了。前几天我就给我二大说了,让他想好了给我回个话,可他硬是没给我回。没回也好,今天我主动来提亲。这几年我们也替二顺攒下了一笔买婆姨的钱,正打算让人贩子再贩一个过来。可眼下有个现成的放在我们张家,我何必让人贩子再贩呢?于月姣那样一个美人坯子,哪能随便让别人捡了去?肥水不流外人田,咱们留下自家用。”
张大顺说罢,从怀中掏出两摞钱拍在桌上。“二大,这是二万块钱,你当面数数——当初你买于月姣时,也是这个数。”
石柱这才明白过来。他说:“大哥,咱不能这么做,这样做不是让外人耻笑咱张家吗?买来的女人又在自家兄弟间倒卖,这都成啥事了……”
张大顺说:“你把人再交给人贩子,那才叫惹人耻笑呢。现在村里就有人放出话来说,看张大顺日能的,他能成全别人家买来的婆姨,却成全不了自家兄弟,买来的婆姨至今还是个摆设。你快把钱收起来,我们这就到那窑里去领人。”
天哪,这叫什么呀!这个叫张庄的村子,头顶依然有天,脚下仍然有地,天地共存,咋就没个法度呢?我并非猪呀狗呀驴呀马呀一类的畜牲让人随便驱赶奴役随意倒手贩卖,我是立于天地之间的人——有血有肉有尊严的人——受国家法律保护的人,可你看……
那时刻,张大顺带着几分酒意,就要带着二顺、三顺到偏窑里来领人。可怜的张石柱,不顾“男儿膝下有黄金”,扑通跪在张大顺面前,连声哀求:“哥,你不能,你万万不能呀!我和于月姣是当着众人拜了天地结过婚的人,怎么能随便转让呢……大哥,这事千万不能……”
张大顺根本不听。张大顺说:“现在你倒拿拜了天地结过婚来糊弄我,那天你让我把她交给人贩子再贩买时,咋不说‘拜了天地结过婚’?你要是眼里还有咱张家,还有咱张家兄弟,你就让二顺娶了她。你娶了当摆设看,等于没娶。”
张大顺说着,顺势一推,将石柱推到一边,一步跨出窑门,直向偏窑扑来;他的两个兄弟尾随其后也冲到了窑门前。
他们踢开门正要进窑,不想有人一声断喝:“你们给我站住!”把三人阻在门外。
是断腿老汉。断腿老汉单腿独立一身子堵在窑门前,右手攥着一把鎯头——那是他砸石用的一把特大鎯头,攥在手里沉甸甸的。他俨然像一个独腿将军,威武地立在门前,怒视着三个莽汉,扬言谁敢再迈进一步他就砸烂谁的狗头。
张大顺是个说一不二的人。他借着酒劲,大喊:“二大你走开,小心再把你的腿跌断。我可是给你付过钱了,人已归我,你管不了了。”
他以为断腿老汉是摆样子吓唬他,未必敢动真,喊罢又往窑里闯。没想断腿老汉挥起鎯头就是一家伙,张大顺本能地扬臂一挡,啪!鎯头落在胳膊上。他“哎哟”一声喊叫,转身撒腿就跑。张二顺、张三顺见势不妙,也跟着跑了。
断腿老汉使横的来硬的,让张大顺着实没想到。在他眼中,断腿老汉是个硬不起来的绵羊,手中的那把鎯头只会用来砸石头,哪能砸向人?可他偏偏就砸了。以我所想,断腿老汉那阵子肯定是被逼疯了。面对一个蛮横得过了头的人,一个拿人不当人看的人,谁能不疯呢?一个人疯了,做事是不计后果的。断腿老汉挥起鎯头的份量着实不轻,虽没将张大顺的胳膊砸断,却也让他饱尝了疼痛之苦——听说被砸的胳膊肿胀青紫十来天,淤血不散,疼得夜夜无法入睡。
断腿老汉一鎯头砸伤了张大顺,也伤了他自己——他抡起鎯头砸人时,由于气怒过盛加上用力过猛,身子失去平衡,重重摔了一跤。他摔倒时右臂着地撞在门前石板上,筋骨损伤。我和石柱扶他起来,他咧着嘴直喊胳膊疼。
胳膊伤了,他无法架拐走路,只能凄苦地躺在炕上,吃喝拉撒都得人侍候。
这天,我做了一碗面条端给他吃。我做面条时颇费了一点心思,这也是我到张家后主动、自愿做的第一顿饭。我精心地和面,精心地擀面,又精心地切成条下到锅里。为了让面有味道,我在汤里撒上葱花和姜丝。我把饭端到他面前,极其温柔地叫了声“大叔”,我说:“大叔,吃饭吧。”我又说:“大叔,你胳膊疼抬不起来,就让我喂你吃吧。”
断腿老汉看我做了饭端给他吃,本就十分感动了,又听我一口一个“大叔”地叫,还要喂他吃,激动得不知说啥好了。他挣扎着坐起来,很吃力地伸出手臂来端饭,却疼得一个劲皱眉,额上也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我说:“大叔,你别动,还是让我来喂你吧。”
他执意不肯。他说:“娃,你把小炕桌搬来放到我面前,再把碗放到炕桌上,我自个吃。”
我照他的话把炕桌搬上炕放到他面前。他左手握筷,很别扭很费力地吃完了那碗面条。
至今我也弄不明白,老人为何不肯让我喂他吃饭。是感到别扭还是不好意思?抑或有更深层的考虑?
吃着饭,他说:“娃,看起来,你在你家也是常做饭的,不然,你不会做出这样薄细的面条。”
我说:“做是做,但不常做,主要是我妈做,还有我姐。”
他说:“是呀,一个有妈又有姐的娃,咋会常做饭呢?有妈有姐,幸福呀!”
吃罢饭,他说:“娃,你别走,就坐在这,坐这咱俩好好拉拉话。”
我只好坐下。可坐了半晌,他却一句话不说,就那样凝神望着我。我忽然发现,他的布满血丝的眼睛有晶亮的泪水在闪动。果然,那泪水越聚越多,最终顺着眼角滴下来,噗簌噗簌打在胸前衣襟上。他用巴掌抹了下,哽咽着:“娃,大叔不好,大叔让你受罪了,一切都是大叔造的孽……可事到如今,我又想不出一条法子挽救你……娃,你……,你……你就委屈一下,干脆留在咱张家吧,我这个断腿老汉就是受苦受难把命搭上,也要尽量让你的日子好过。娃,我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求你了……”
面对他的真诚,他的无奈,他的哀求,还有他不断流淌着的泪水,我真想一口答应下来,可我又不能。我早就下了决心,即使是死,也不能把自己的一生交给这偏僻、穷困的山村。我一旦答应下来,就不好更改了。若答应下来再更改,这个可怜的老人,不定又会承受多大的痛苦呢!我思忖良久,道出了我认为对他对我都再合适不过的一席话。我说:“大叔,我看这样吧,你和石柱都跟我走。这个家,这个破窑,你都扔了吧。你们一辈一辈的人守在这里,除了穷,还是穷。你们跟我走出去,在我们那里重新安家,照样过日子,而且过得肯定比这里好。不信,你出去就知道了。我向你保证,你们到了我家,我会让我大哥把石柱接收到他的厂子里工作,每月至少拿四五百元工资。你们就跟我走吧。”
断腿老汉沉默不语。半晌,嘟嘟哝哝像是对我,又像是对自己:“外边再好,也是别人的家乡;这里再穷,也是生我的地方,怎么能说走就走呢。”
随后,我把我与断腿老汉拉话的内容讲叙给石柱听。我说:“石柱,你也该好好考虑一下这事,我认为你们跟我走,是顶好的一件事,也是你我最好的选择,呆在这穷山沟里,一辈子都是穷,有啥意思呢?”
石柱说:“你让我好好想想,我再跟我大慢慢商量商量。”
这天,我又跟石柱下沟驮水了。路上,石柱对我说:“妹子,上次你说的那事,我跟我大商量了,他说走不是不可以,关键是我们还不是一家人,如果真的是一家了,走到哪儿都行,是福是祸都认了。可我们……”
我心中不禁犯了嘀咕。看来,要实现我的主张,我就得跟石柱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夫妻,就必须跟他发生实质性的关系,不然,就……我不能说他们的想法有啥不对,放在谁身上,都会这样想。可我……我和这个张石柱……唉。
石柱看我半晌不语,又说:“妹子,不瞒你说,在我们村里,也有举家迁走的,跟你说的一样,是跟着被买来的女人走的,可那女人,人家都已生下两个娃儿啦,村里人早就对那女人消除了戒心。那女人和自个的男人带着他们的娃先回了趟娘家,然后迁走的。妹子,你说外边千般好,可我又没亲眼见,又不能随了你去见,只有咱们真正过到一起,村里人看着我们是实实在在的一家人了,那时,怕是才能走得脱。”
我说:“那晚张大顺重重挨了你大一鎯头,胳膊都被打伤了,他会不会……”
石柱说:“我那个大哥,过去对我一直很好,我们感情也深;对我大也很尊重、孝顺,只是我们向他提出要把你退给人贩子,他才动了邪念。这也能证明一个事实——他太看重你了,舍不得你走。只是他的做法太不讲究,太让人看不下去,我大才动了怒,才不顾一切地……只要咱俩好,他是不敢再动什么邪念了。”
看来,摆在我面前的路只有一条:我得认拐认卖,认面前的这个石柱做丈夫。只有踏上这条路,明天的路才有希望。
这条路,我是该走不该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