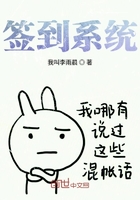〔英国〕莱·亨特
此刻,曙光女神从她那橘红色的闺楼里慢慢地撒下了玫瑰色的万道光芒,湿润的空气抵抗不住她魁力的诱惑而聚集在她周围。女神在空气的掩跌下,尽情地呼吸着,舒展着身子,直到威力无比的太阳神到来。太阳神驾到了,他居高临下,俯视下物,在光的王族里,他有着不可侵犯的显赫地位。这当儿,割草人开始减慢了修剪速度,不时地停下来,咂两口啤酒。一个赶车人在满载于草的车顶上好像昏然入睡一样,或许他只是疲惫不堪地拖着双肩并未入睡,两只眨巴着的眼睛在遮阳帽下直往远处瞧着什么,嘴巴上还叼着一条牵牲口的套索。这时,一个小姑娘坐在祖母家的门口,注视着来往的车马,她把一只手举到额前,以避开刺眼的阳光。身着白汗衫的庄稼汉们,在啤酒馆的屋檐下歇息,显得轻松愉快。阳光下,一棵榆树,枝繁叶茂,如伞如盖,树下有一张乘凉的椅子,几匹马贪馋地伸长着脖子,在马槽里饮水,颈上的套绳都拉得紧绷绷的;一位过路人要来了啤酒,不到十分钟就喝完了一杯。他的坐骑在旁边不停地躲闪着蚊子的进攻,皮肤不时地剧烈地抽搐着,那条短尾巴徒然无用地甩来甩去。店家的女儿——贝蒂·威尔逊小姐,身穿大花衣裳,两只耳垂上坠着耳环,她用纤细的手,拈着一杯泡沫四溢的啤酒从里面飘然而出。过路人喝完后,她不屑一顾地接过杯子,然后又带着另一种神态——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向过路人要了两个便士。
此刻,蚱蜢像Dryden在维吉尔的田园诗里写到的那样在“蹦跳”,而牛却跑下河了,河里的鸭子更使人羡慕。路边的人群和树木都已遍布尘土。人们把几条狗扔进河里抢树枝取乐。它们上岸,在地上打几个滚后,往围观的人们的脚边乱窜,直吓得他们发出阵阵嘘声。那边,一个赶路的人,脚穿一双过小的鞋子,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因为他还要走三里多路呢。烈日当空,屋子热得不堪忍受,愁眉苦脸的学徒正回想着孩童时曾经常常在学校里洗澡嬉戏的那汪水塘;那些头上搽粉的人,特别是粉层较厚的人,嫉妒那些没有搽粉的人,并且,停步狠命抽打头上的粉,完全一副与命运抗争的架式。调皮的孩子们聚集在村里水塘周围,用一把木勺在那儿戏水,湿透了各自脚上的鞋,这些孩子还用皮革做了一些叫“吸皮”的小玩艺儿。他们整天泡在河里和水塘里,挖空心思捉丝鱼。蜜蜂嗡嗡作响的声音也像是在抱怨气候的酷热难忍;就连门和砖墙也变得灼热烫手。靠近砖瓦场的那条高墙窄巷里面,四处尘土,遍地碎玻璃,更热得令人不敢想象。然而,恰恰相反,那条榆树成行的绿色小巷,却成了世界上最使人流连忘返、让人身心畅快的地方。那里还不时地发出小溪流水的“哗哗”声,正像斯宾塞在其著作里写到的那样:
“小鹅卵石在水里发出嗒嗒的响声。”
同一时间里,城里多舌的家庭主妇们更关不住她们那永远是多嘴的话匣子,不管在房子里,在门道里,还是在窗外,她们总是憋不住要说上几句话,而且一开口总是说“简直热得不堪忍受”。家家户户的百叶窗降到了窗下缘。门大大地敞开着,法兰绒的外衣被搁置一旁。冷肉总是那么抢手,而热的却无人问津。人们觉得奇怪怎么茶总是像刚泡开一样烫嘴,他们喜欢把莴苣切成片放进碗里。店铺里的学徒用水罐在楼道上不停地洒水,仅能使少量尘土不再飞扬,而运水的水车在街心隆隆而过,把车上水箱里大量的水摇晃在地上,倒还真正做了件好事。
此时,光临水果店和奶品店的人特别多,有幸接触到冰块的人,真有些爱不释手。妇女们则泡在澡盆里打发时间;香气宜人的鲜花成了最好的礼物,有色酒里放上了冰。那个晚上饭后出门兜风的人从长颈瓶里取出香水往头上洒,以此取乐。他忍不住去骑上那匹新买的马,也觉得靴子里一阵灼热。鹿皮衣再也不像高斯岛的细麻布,赛马的骑师穿上厚厚的大衣作他们通常做的减肥运动。而此时也热得嘴里不停地抱怨。坐在公共马车上的五个胖子此时最怨恨的是刚上车的那个胖子,他们觉得他不该古据如此大的空间。那些坐在办公室里的职员,什么也干不成,只是边喝汽水或松针酒,边看报纸。收旧衣的小商贩对着街对面那一片空旷灼热的地方,有气无力地叫喊着。面包师露出难看的面容,厨师也显得好动怒;酒店冒出的炉烟在我们看来也像地狱里出来的妖气一般。此时,蚊虫包围着细嫩的肌肤;顽皮的孩子们用一面镜子将正在熟睡的伙伴搅醒。铁匠的身躯犹如占铜一般,皮匠躲在棚子下直想为自己植一层皮。奶酪也融化了;骑兵们开始怀疑古罗马的兵士们如何穿戴得住他们那笨重的头盔;经常炫耀自己的富妪们也不得不卸下头上的装饰物,走在街上显出一副破败相,女仆们生怕她们由于热而显得出格。这时,本文作者要来一盘草莓,也觉得该就此搁笔了。
(李光荣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