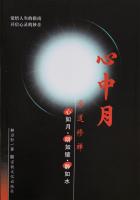前几天,在《白虎关》和《西夏咒》研讨会上,我跟某学者有过一个争论。他认为的“英雄”,大多是我认为的罪人。
目前,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在赞美自己的英雄,而这些“英雄”几乎都在国家、民族、信仰的旗帜下屠杀过另一群人。
世界史如此,中国的历史同样如此。如金朝的金兀术,这样的“民族英雄”被金朝捧出来后,就可以带着金朝人屠杀宋朝人;而宋朝人推出的英雄岳飞也要带人去屠杀金朝人。每个朝代都有这样的屠杀,每个朝代的文人都在赞美这些“英雄”。
2009年,我到法国参加中法文学论坛的时候,法国人仍然将拿破仑当做神来崇拜。而我在发言中却说,拿破仑无论怎么样,当做神来崇拜也罢,当他作为一个人类,到俄罗斯屠杀另一个国家的人类的时候,他是罪人。赞美拿破仑的文化会培养出更多的“拿破仑”;赞美希特勒的文化也会培养出更多的“希特勒”。同样,讴歌拉 登的文化,将会培养出更多拉 登似的“暴力英雄”。但历史上有一种规律,就是崇尚暴力者,必为暴力所灭。拉 登之死正说明了这个道理。拉 登的暴力是强大的,但世上还有比他更强大的暴力。所以,必须有一种声音,告诉人类:我们不要屠杀,不要暴力,我们需要爱。
正是在这种目光的观照下,我才写出了长篇小说《西夏咒》。
我想,在民族、国家这类词语之外,人类应该有另一种声音,来告诉世界:暴力是最大的恶。虽然这个声音非常弱小,但我觉得这是黑暗中的一点烛光。讴歌暴力英雄的“屠夫文化”是非常可怕的,因为暴君可以死去,屠夫也有寿命,拉 登的肉体也会被另一种巨大的暴力摧毁,但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人类文化中会有一种邪恶的暴力基因,它会滋长出一代代无数的“屠夫”。
成吉思汗无论多么强大,拉 登无论多么可怕,他们都会死。但这种“屠夫文化”却能培养出新的“成吉思汗”,培养出新的“拉 登”,培养出新的暴君和屠夫。要知道,民族也罢,国家也罢,它们是有局限性的。日本人的“英雄”正好是屠杀中国人的屠夫,中国人认为的“英雄”成吉思汗,被称为“上帝惩罚人类的鞭子”,他灭了四十个国家,这些国家中有多少无辜者死于非命,他们的头颅像戈壁上滚动的乱石,那些寡儿孤母的眼泪像黄河一样流淌着。当然,我们允许蒙古人赞美成吉思汗,允许中国人称成吉思汗是英雄,但是对于那些被屠杀国家的人来说,他其实是罪人。
我的《西夏咒》就写了这种反思——站在人类的高度上来反思这些许许多多的“英雄”,他们屠杀另外一群人类对吗?
古代某年,西部出了一个暴君,屠杀了大量的佛教徒,造下了无数的罪恶。有一个非常勇敢的僧人,他化装之后,来到这个暴君跟前,一箭射死了他,然后逃走了。那僧人当然拯救了很多无辜的人,但西部有这样一种文化理念:杀人是有罪的。无论你杀的是暴君也好,坏人也罢,杀人的行为本身是有罪的。所以,后来那僧人一直没有资格给别人授戒。当别人让他授戒时,他说自己没有资格授戒,因为他已经杀过人了。杀人这个行为本身就已经犯戒了。
西部有一种文化认为,无论什么样的生命,我们都应该尊重,都应该敬畏,无论你带着什么样的理由,去剥夺另外一个生命的时候,这个行为本身就是罪恶。因为你的理由会由于你的宗教哲学、人生哲学以及国家的教育变化出不同的花样,可以制造出不同的“正义的”理由和借口。
每一个政治家有不同的理由,每一个时代有不同的谎言,但我们必须有一种理念和文化告诉人类:杀人是罪恶,人类不应该杀人。无论以什么样的理由来杀人,都是罪恶。
当然,我的这种理念与我们目前所受的教育也许有一点点不一样,但五十年之后、一百年之后,再反思一下今天,也许我的声音是对的。“文化大革命”中许多被认为正确的,现在发现错了;那么,现在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五十年之后、几百年之后是不是仍然认为是正确的?这个问题,很值得我们研究。
所以,我觉得应该从“人”的角度、从人类生存的角度来反思,不关乎政治家,不关乎哲学家,只关乎“人”本身。因为无论什么民族的寡妇,当她的丈夫被人杀掉的时候,她都会非常痛苦。任何一个人都没有权利去剥夺另外一个人的生命,无论他有着什么样的理由。
《西夏咒》中的这种反思会不会被世界认可不要紧,至少表明这个时代还有一个人这样想,还有这样一种声音,还有我这样一个萤火虫。虽然这个萤火虫在黑暗中照亮不了多大的空间,但有一点点光就行了。至于这个萤火虫的光能不能赢得世界的喝彩,我不在乎。我当然希望它不要被黑夜所淹没。
愿所有的暴力英雄别再出现在人类的喝彩声中。
(刊于《文学报》2012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