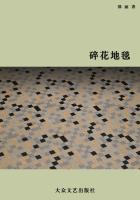也有人觉得,我的写作是为了一种社会责任感,或者是想达到一种救世的目的,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我在明白之后,从来没有把任何人当成我的敌人,也不想超过任何人,我的对手永远都只有死神。从年幼的时候开始,我就在跟死神赛跑,我想在它追上我之前,升华我自己,升华我的生命价值,让自己成为一个能令自己看得起的人,同时多做一些我该做的事,不要给人生留下遗憾。此外,我不在乎自己能拥有多少东西,是不是能拥有一个世界,能拥有多少的粉丝,能拥有多少的喝彩,能拥有多好的名声,我不在乎这些东西。
写作仅仅是我生活的一种方式,也是我与死神赛跑的一种方式,是我建立一些岁月毁不去的价值的一种方式。所有的救世之说,往往是别人加诸我的。我不想改变这个世界的什么东西,我想拯救的只有我自己,我只追求一份灵魂的安详,只传递一份明白和清凉,再没有别的东西。事实上,每个人能做到的也仅仅是这样:拯救自己。但是每个人的救自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救世。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人类整体中的一部分,就像一滴海水与一片大海之间的关系一样,你没必要把它们看成两个独立的个体,它们事实上也不是独立的个体,因为人与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永远都在互相影响着——人与世界也是这样。
所以我常说,有时候真正的利己其实也是利众,当每个人都改变了自己的时候,他其实也是在改变世界。因此,我们每个人都不用去考虑自己有没有改变世界的能力,这个世界能不能被改变,什么样的世界才是真正美好的世界。你需要去考虑的,仅仅是你愿不愿意改变自己,你愿意付出多少努力去改变自己,你是否知道应该怎样改变自己。你真正需要关注的仅仅是这些问题。此外的好多东西,困难也罢,黑暗也罢,得失也罢,都不是最重要的。因为,一切都会过去,一切都会变成记忆。当你进入下一个人生阶段,再来回顾今天的一切时,就会发现所有的乐与苦,本质上都一样,都不过是一些曾经发生在你生命中的事情,它们会给你未来的生命历程带来一些影响,但它们本身却是必然会过去的,留不下多少东西。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你就不要再去在乎现在有没有人懂你,有没有人认可你,你的付出是不是得到了相应的回报,你不要去纠结于自己的这些小情绪,不要让情绪影响了你的成长。你要牢牢记住自己追求什么,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并且时刻保持一种警觉,观照自己心灵的状态,不要有一点点的自欺欺人,不要给自己任何借口。这样,你才能保持清醒,时刻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自己的行为将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自己的选择将会给下一刻的人生带来什么,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在成长,还是在倒退。你应该明白,只有不断成长,一切才有实现的可能,如果你总是停留在想的层面,总是不肯踏出第一步,那么梦想就永远都会是一个实现不了的“梦”。这个成长的过程或许会很苦,但不经历这种苦,不超越这种苦,就不会有后来的甜,更不会有终极的宁静。
刚开始写《大漠祭》的时候,我没想到这个过程竟然会如此漫长。我只是在写的时候,才忽然发现自己想做的事情,原来是一个十分艰巨的工程,要写出这样的一部作品,作家本身必须经历一番灵魂的洗礼。因为,没有那样的一个过程,你就很难进入老百姓的灵魂,如果你无法洗去心灵上的污垢,就贴近不了老百姓的心,你永远都会和老百姓隔着一层。我明白,这是一种脱胎换骨般的历练,但是我始终没有放弃。
在写《大漠祭》、《猎原》、《白居关》的二十年里,我一边禅修,一边练笔,屡败屡写,仅手稿就有数百万字。要知道,我自小就跟农民摸爬滚打在一起,经常参与他们的活动。我的父亲是个马车夫,他告诉了我好多故事,但就是在这样的生活基础上,我仍然跑遍了凉州,交了许多农民朋友。我到他们那儿去的时候,跟到自己的家里一样,他们没钱的时候会问我要钱,他们的孩子读不上书的时候,我也会帮助他们。我那时候经济条件不好,但很节俭,对自己甚至算得上小气,这样才能省下一些钱,帮助身边的人。这是从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一种家庭传统,但我也确实把这些农民当成朋友。正是因为这一点,他们都能把心掏给我,有的人甚至把一些秘不传人的东西都告诉了我。比如,《大漠祭》、《猎原》里的那些打猎秘诀,好多猎人都不知道,但是一位老猎人却把那秘诀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有些人把一生搜集的资料都无偿地、毫无保留地给了我。就是这样,我才从一个才踏上文坛的文学青年,渐渐在艺术上走向成熟。换句话说,那寂寞的二十年,是我苦苦修炼的过程。只有经过苦修,一只寻常的猴子才可能成为孙悟空。没有苦修,就没有顿悟;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
真正明白这一点、接受这一点的时候,好多人才会明白,一切所谓的客观困难,实际上只是自己给自己找到的一些退缩的理由。如果你自己不愿意退缩,只要勇往直前,不断升华自己,就没有任何困难能挡住你前进的脚步——当然,这种义无反顾的前进仍然不能盲目,要具备一种清醒的眼光。这种清醒的眼光,也是一种直观的智慧,你只要不断修炼灵魂,升华心灵,揭去一层又一层欲望与执著的蒙眼布,你本有的智性就会觉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