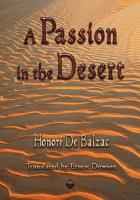叶先生忙道:“这是我家新来的两个远亲,亭儿、榭儿,快来见这两位武林高手。”几人见过,那两个女子仍端坐在一旁。原来这两个女子,正是白云亭和白云榭,她们一直宿在远房舅舅叶潜的家里。
白云亭问:“你可认得有个叫程廷华的武术家?”马维祺道:“原来你们在外地也听说过眼镜程,他是我们的朋友。”
白云榭道:这下可好了,前几日我和姐姐一同到广化寺烧香,遇到一个叫伽蓝的和尚,他上前调戏姐姐,我姐妹与他对打起来,谁知打不过他,于是逃出寺门。
那和尚笑道,北京城里只有一个叫程廷华的还有些功夫,其他都是酒囊饭袋。
马维祺一听,气呼呼地说:“这秃驴如此无礼,看我不用煤球碎了他。”梁振圃道:“这小子也太猖狂,我们不如一齐杀进庙去。”
白云亭连忙劝阻道:“想是二位义士是隐士,那和尚不认得。”
马维祺道:“北京城里谁不知煤马和小辫梁。”
白云榭道:“我们姐妹不劳神二位了,只想请你们转告一下程廷华,请他近日去广化寺鸣不平。”梁振圃道:“既是这样,我去转告程廷华,让他明日晚上到广化寺?”
马维祺对梁振圃小声道:“你不是跟叶先生借宝吗?”
梁振圃道:“叶先生,我想跟您借几副佛香膏药。”
叶潜道:“你怎么知道我有这种膏药?”
梁振圃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原来叶先生有一种专治硬伤的膏药。
梁振圃又道:“此次皇会主擂的神力王肃王爷腿功厉害,若是被他踢中,凶多吉少,所以来借几副膏药,以备不测。”叶潜沉吟一会儿,道:“既是这样,我就送你两副。”马维祺笑道:“我也参加皇会,也要两副罢。”叶潜笑道:“我就知道你也会要的。”
说完,叶潜来到东厢房内,轻轻按了墙上的机关,地上两块方格花砖向两侧移开,现出一个青玉麒麟黄底图案的瓷缸。他打开缸盖,不禁大惊失色:“哎呀,我这瓷缸分明有人动过,有人偷了膏药。”他查了查,少了十副佛香膏药。
这时马维祺、梁振圃、白云亭、白云榭闻声赶来。
叶潜道:“我平时很少出门,家里又有护院,这膏药如何被人偷了?”
白云亭道:“俗话说明贼易躲,家贼难防。兴许还是家里的丫头、护院干的呢!”
叶潜道:“那就搜搜吧。”他们来婢女、护院房中搜了一遍,未见可疑之处。走到白云亭、白云榭的房前,白云亭道:“舅舅,我们房中您也瞧瞧吧。”
来到房内,只闻得花气袭人,大红绣并蒂百花披风、绿纱绣喜相逢百蝶裙儿、四合如意肩、汗巾、抹胸儿、膝裹儿等丢了一床、白云亭、白云榭一看,脸上泛红,原来只顾叫他们来搜,竟忘记收拾了。
叶潜查看一遍,也没看出什么可疑之处,叹口气,退了出来。
晚上,梁振圃来到程廷华家里。程廷华正在烛下磨眼镜,梁振圃把白云亭姐妹请他去广化寺鸣不平一事讲了。程廷华道:“我到过广化寺,怎么没有听说过有个叫伽蓝的和尚。”马维祺道:“或许是新来的和尚。”程廷华道:“既然是二位姑娘请我去,我明日晚上就走一趟。董爷收了瘦尹为徒,学习八卦掌,我也想拜董爷为师,不知他老人家愿不愿意收。”梁振圃道:“我也有此意,只是咱们若拜董爷为师,每日出入四爷府,有许多不便,不如帮董爷开个武馆。”程廷华思忖一会儿,道:“施纪栋家里倒挺宽敞,位置也不错,在他家里办武馆最好不过,咱们一块凑点钱。”
第二日晚上,程廷华换上夜行衣,来到地安门烟袋斜街广化寺,他穿过钟楼,来到大雄宝殿前。有个和尚正在巡更。程廷华上前猛地搂过那和尚的脖子,僧帽脱落,露出一络秀发,原来是个女子。程廷华怔了一下,只觉一个飞套已套在脖子上,双脚离地,被悬空吊起来。房上有个女子正在拽绳子,程廷华自知中计,慌忙用手掌去削绳子,地上那女子手握尖刀,朝他心窝刺来。各自这华一揣脚,踢飞尖刀。房上那女子叫道:“不要便宜了他,先把他折磨个够本儿,再叫他见阎王爷。”程廷华定睛一瞧,地上立立着的女子不曾相识。只听那女子说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我们是十几年前被你杀的白凤冢小白龙的两个师妹,如今找你复仇来了。”房上的白云亭将绳子拴牢,也跳了下来。两个女子对程廷华拳打脚踢,程廷华双手死扒绳套,没有还手之力,身上被她们姐妹踢得青一块紫一块。
这时僧房里已亮烛,从西南角僧房里又跳出两个女子,一位梨颊娇姿,两鬓乌云笼住春色,头上罩一幅元青绉纹包头,身穿佛青衣衫,脚穿宝蓝尖头绣碎花弓鞋。后面那位腮厣桃花,唇含樱颗,玉骨玲珑,柔躯娇嫩,濯濯如春月杨柳,滟滟如出水芙蓉,一双尖生生手,一对小叮叮脚,手持一柄鸳鸯剑,正是吕飞燕和翠珠。原来吕飞燕和翠珠自入九华山师父遇害,冲出得围后,便来河南开封府寻找董海川,可是见到开封府被封,董海川不知去向,又找不到一个熟识的人来问,二人又来到凤凰山。她们看到山上残尸遍地,屋宇倒塌,知有变故,于是只得浪迹天涯,继续寻觅董海川。前几日她们听说北京四爷府里新来一位教头,八卦掌功夫甚好,名叫董海川,吕飞燕不相信那个教头就是自己朝思暮想的董海川,但又有些疑惑,于是与翠珠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先栖身在广化寺内,想探个究竟。没想这日晚上正在睡梦中却被白家姐妹殴打眼镜程惊醒。
吕飞燕一声喝道:“贼人手下留情!”说着一剑劈去,翠珠将手一扬,一支飞镖削断绳索,程廷华摔落地上。白云亭、白云榭见有人来救,一齐拽出宝剑,四个侠女五支剑,一场好杀。吕飞燕毕竟技高一筹,更加上有八卦掌功夫,那白云亭渐渐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有些气喘吁吁。白云亭退后几步,顺手摸出一个掌心雷,向吕飞燕掷去,吕飞燕头一偏,掌心雷飞空。吕飞燕一招“仙女送桃”,一剑挑去白云亭一缕秀发,白云亭一招“旱地拔葱”,上了殿顶,伸手一扬,五枚梅花针扑来。吕飞燕一招“玉女穿梭”,躲过梅花针,也跳上房。白云亭挽一个剑花,朝吕飞燕捅来。吕飞燕用雌剑挑开她的剑尖,用雄剑朝她身下刺来。白云亭往后退了几步,退到殿顶沿上,那宝殿年久失修,殿瓦散松,白云亭一个趔趄栽了下来,她一连翻了几个跟头,正要落地,被地上的程廷华拦腰抱住。吕飞燕一招“燕子钻云”飘落下来,一剑刺中白云亭。白云亭倒了下来,吕飞燕连补几剑,白云亭气绝身亡。那白云榭见姐姐被杀,已经胆怯力弱,猛朝翠珠虚晃几剑,落荒而逃。
这时文殊法师已率领众僧过来,程廷华认出吕飞燕,不禁叫道:“原来是你!”吕飞燕也认出程廷华,惊喜地叫道:“原来是程义士。”
程廷华上下打量吕飞燕,惊得后退几步:“你就是十多年前在天宁寺相识的吕飞燕,十多年没有听到你的音讯,什么风把你给吹到北京来了?”
吕飞燕说:“听说北京四爷府有个教头叫董海川,不知道是不是十多年前被我们救的董文安?”程廷华说:“这个董海川从未对人谈过他的经历,他会一套八卦掌功夫,功夫十分了不得,北京城里许多好汉都想拜他为师。”吕飞燕一听,怔了一怔,忙问:“他长相如何?”
程廷华呷了一口茶:“大大的个头,身材魁梧,方方正正的脸盘,浓眉大眼,没有胡须,是个割阉的太监,是王府护卫群里响当当的人物!”吕飞燕见程廷华所描绘的正是自己朝思暮想的董海川,想到他竟然投奔王府,自甘堕落为清延的走狗,不禁又气又急,“哎呀”大叫一声,晕厥于地。
吕飞燕醒来后,程廷华等人已经离去,只有翠珠在旁边服侍。吕飞燕怔怔地望着翠珠,眼泪象珠子般淌下来。翠珠知她心里难受,连忙给她倒了一杯香茶,又用手绢替她拭泪。吕飞燕恨恨地说:“董海川呀董海川,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小人,师父的教诲你全忘了!师父原指望你能继承道家拳,在武术上大显身手,可是没有想到你却卖身投靠了王爷,当了太监,去端那剩饭碗,你这个没骨气没良心的东西!我悔不该在沧州救你,悔不该将你推荐给师父,悔不该痴情于你。”说着拔出利剪朝双眼戳来。翠珠慌得急忙去夺利箭,利箭夺到手,可是翠珠的右手没小心被利箭扎破,吕飞燕心疼地一把抱住翠珠,呜呜地哭起来。翠珠劝道:“董海川看到凤凰山义军失败,秦淮碧夫妇被害,一定是吓破了胆子,软了骨头,变了心肠,这样的男人还有什么可眷念的,咱们离开北京,远走高飞吧!”吕飞燕凤眼圆睁:“不能就这样一走了之,我要与他理论清楚,让他交出《易卦》再一剑杀了他!不让他空怀绝艺,干为虎作伥的事!”
却说董海川近日来在四爷府苦练武艺,准备赴皇会刺杀咸丰帝,至于他自己退路如何,他却全然没有考虑。这天上午,董海川又来到后园练武,只见鹦鹉笑盈盈从玉带桥上走来。鹦鹉说:“董爷,这几天总见你练武,也不出门逛逛去。”董海川笑道:“北京城我已转得差不多了,那些胡同、庙宇、道观都象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瞧了几个就八九不离十了。”鹦鹉见董海川的衣服破了一个口子,说:“董爷,你这衣服都破了,也不缝缝,今晚你换下来,让何五爷送到我那里,我给你缝几针。”
此时,吕飞燕正藏在附近花丛中,她看得清楚,呼地从花丛中跳出来,指着董海川骂道:“你这忘恩负义的东西,竟忘了师父的教诲,投靠王府为贼。”说着,啪地打了董海川一个耳光。董海川一见是吕飞燕,不禁呆怔了。吕飞燕从怀里摸出一个玉匣,抖出一柄鸳鸯雌剑,折为两鞭,摔到董海川脸上。
董海川忙道:“飞燕,你听我说明白……”吕飞燕愤愤道:“我千里迢迢来寻你,想不到你变成这般模样,为王爷看家护院,还与丫环偷情!”鹦鹉一听羞红了脸,忙躲到董海川身后。董海川又气又急,当着鹦武的面,又不便说出洪秀全委派之情,只是重重地叹了口气。
吕飞燕颤抖着抽出鸳鸯剑,一剑朝董海川刺去,董海川躲过。吕飞燕唰唰几剑刺去,董海川左躲右闪,不曾还手。这时,何五、何六带着护院跑来,一伙人围住吕飞燕。董海川急忙叫道:“不要伤了这个姑娘。”吕飞燕挥动鸳鸯宝剑与众人拚搏,由于气愤过度,又加上昨夜一宿未睡,身体虚乏,渐渐气力不支。董海川见她有危险,一招“脱风换影”,旋到吕飞燕身边,用右掌轻轻托起好的娇躯,轻轻一送,将吕飞燕托于圈外。稆飞燕自知不能取胜,抹了一把泪水,愤愤而去。何六抬头看着董海川眼眶里涌满了泪水,他还是头一次见到董海川伤心落泪,于是走过来问原因。董海川一言未发,闷闷不乐。
却说吕飞燕恍恍惚惚,走在地安门大街门,见旁边有个酒楼,走了进去,上了二楼,唤酒家端一瓶山西汾酒和两个拼盘,一连喝了三杯,很快酩酊大醉,人事不省。这时,走进一个风流倜傥的中年秀士,他嘿嘿冷笑两声,一声呼哨,两个大汉进来,将吕飞燕拖下楼去,塞进一辆华贵的马车,飞驰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