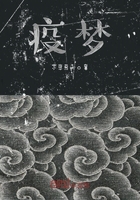席慕蓉是台湾当代著名诗人、散文家和画家,她的诗歌在 20世纪 80年代风靡大陆,打动了无数青年男女的心,在诗坛上形成了“席慕蓉现象”。这一方面和大陆诗歌长期的封闭和“左”的风气有关,在一开放的情况下,人们发现诗歌原来是这么美好的东西,而不只是革命和斗争;另一方面则是与席慕蓉诗歌本身的艺术品位有关,正如席慕蓉自己所说,自己是用诗来追寻一种“绝对的爱情”,正是这一点,使她的诗获得了广泛的读者。
所谓“绝对的爱情”,席慕蓉曾经说:“我一直相信,世间应该有这样一种爱情,绝对的宽容、绝对的真挚、绝对的无怨、绝对的美丽。假如我能享有这样的爱,那么,就让我的诗来做它的证明。 ”(席慕蓉:《七里香》,花城出版社 1987年版)诗人实际就是要用诗去捕捉人性中最纯最美最永恒的那一丝丝情愫,这不是理想,更不是空想,而就是在人们的生活中,只要你有时间有心情停下来审视一下自己,审视一下周围的人,观察一下生活,你就会发现这种“绝对的爱情”。而这种观察,诗人首先就从自己开始。
席慕蓉在谈到自己诗歌写作的动机时,说自己写诗就是晚上没有事的时候,拿一些纸、一支笔,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自由活动的美好时刻。她认为和自己的“职业”——绘画相比,写诗只是自己心灵很惬意地“静静流淌”的活动,自己在写诗上“从来没有刻意地做过什么努力”,而只是等待它来到自己心中。
这让人想到了佛教的修行,一人独居静室,闭目凝心,拂除心尘,直观内心中永恒与最真挚的愿望与企求——这些东西才是绝对,才是永恒。
席慕蓉曾经回忆自己对诗歌的初次感觉。她说:“少年之时,初读《古诗十九首》,真是心灵震动。那时候太年轻,不能明白其中的原因,只觉得有许多首仿佛都早已相识,仿佛等待已久的就是这些感觉,这些诗句。其实那就是在僵硬的国文课本之外,少年的我,第一次接触到人性深处的呼唤。从此,诗,成为我与外在世界抗衡的一种力量。 ”(席慕蓉:《河流之歌》,台湾东华书局 1992年版)她这里说的是自己在体验到了《古诗十九首》中佚名的诗人心中流淌出来的诗意时的感动,觉得自己和这些诗发生了共鸣,而这共鸣又与外部世界形成了“对抗”。
这就说明,虽然席慕蓉写诗是出于心灵的自由活动,但这种静观的自由又不是绝缘人间烟火的、不仅仅是纯粹的内心表白和体验,像未出阁的少女在闺中的笔墨鉴照。这种内心的活动往往就是诗人外部生活的应激反应。从诗歌中往往能找到使全体共鸣的东西,而不仅仅是她个人——正如她能够从别人诗歌中找到共鸣来对抗世俗一样。
但诗歌首先能感动自己,才可能感动别人,引起别人的共鸣。席慕蓉经常通过自己的诗来抒解自己的心情,她说:“这些诗一直是写给我自己看的,也由于它们,才使我看到自己。”也就是说诗人通过诗歌寄托自己的生活,再从诗歌中如照镜般审视自己,这增加了诗人生活的自觉性,这也显然对世俗人生有净化意义,使人们在尘世的生活中不断注入理想的力量。这样写诗对她来说就是一个不断重新“审视”生活的行为——发现生活真谛,寻求理想的生活方式,来指导现实生活。席慕蓉的夜晚静处的写作状态,就是一种白天生活,晚上思考的过程,任何一晚的诗意感受和思考都会指引明日的生活。
人们日常忙碌的生活是琐碎繁杂的,是庸俗乏味的,每个现代人如果每天都有一点自由的时间,像席慕蓉那样一日三省己身,心理就会有更超拔的体验,生活就会有更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当一个实用理性社会中的人们都有那么一点点执拗地追求“绝对”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可能也会有趣得多,亲切得多。
按我们一般的理解,绝对的东西在生活(历史)中是不存在的,但历史或生活的存在决不能离开这“绝对”的理想,理想、形而上的追求可以是永恒绝对的,一旦进入现实生活,“绝对”将以具象的形式显示出其历史相对性,但就纯粹的精神激励来说,这种“绝对”对人生不可或缺。
由此理解席慕蓉的“绝对的爱情”,我们也就豁然可以明白了。她的诗中的爱情就像一粒糖,生活就像一杯水,你有了糖,将它丢入水中,你的生活就有滋有味,而在生活中你不可能天天吃糖生活。就糖而言,这是一种“绝对的爱情”,就你在生活之余写诗读诗而言,这是使生活增色的质素,而席慕蓉的诗就是这样使晦暗的生活豁然光彩的一颗颗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