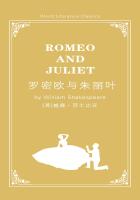按照俄国形式主义的观念,好的文学作品是能够从人们司空见惯的生活经验中写出不一样的艺术感受,给读者新鲜而陌生的感受。我想新鲜和陌生可能是人们进行文学艺术作品欣赏和阅读的一个主要的动力。日常生活如此紧凑和紧张,以至于人们只能用生活经验中的实用理性来应对一切,而艺术作品则会打破这种实用逻辑,带你到一个“陌生”的艺术体验的世界(而实际上它并不陌生,它恰恰是每个人心底被压抑的人性的光辉),让你体验超越于生活的价值,正如这首《鱼市场记》。
人们都有到菜市场买鱼买肉的经历,人们对触目悬挂的肉与瞬间被敲昏的鱼可能会熟视无睹,只想快一点搞定自己的买肉,离开这样一个“污秽”之所,这里的污秽完全是本义,没有任何精神的指涉。人们更无法想象一个诗人会驻足于腥臭的鱼市场,在这里为一条鱼来吟唱。而余光中的这首《鱼市场记》则恰恰是这样一个出乎人意料之外的一首诗——一个本应脱俗的诗人,却在鱼市场中面对这些“秽物”动情吟唱。
这有点类似于坚的《尚义街六号》,将市井之词市井之事放在诗歌中吟咏,只不过余光中从这市井之事、之物中挖掘的是一种古典意绪和情怀。诗人以近乎佛家的悲悯万物,来关怀这样天天被戕害的生灵,从这些日常司空见惯的事件中看到一些已经不为人注意的深层的精神内涵。
诗人对这条鱼的悲悯是以“同心共感”为出发点的,鱼身被剖开,只剩下“一片赤心”在“间歇地跳抖”,诗人马上感觉到自己的心也“猛地一抽”,感应到这鱼的“无头的绝望”。于是诗人马上想到这条鱼再也回不了故乡,而这恰恰是诗人自己的心病。早年被迫离开大陆,在台湾、香港、欧美游历,故乡想回却又不那么自由,诗人无法回乡的境况,不正像这条死在砧板上的鱼吗——凄惨而悲凉。
不仅如此,诗人还由这鱼的悲惨遭遇联想到“自由”和社会的凶险,社会中的个人本应是自由的,但这只是个理想,处于社会关系的制约中和各种社会机构的管制中,人的生存就处处存在着危机。就像在水波中自由嬉戏的鱼儿,在“逍遥”的波浪里,处处都布下了危机。有渔网,有篓筐,有钓钩,还有砧板、讲价的秤盘,这些以一条龙的方式安排了鱼儿悲剧的命运。只不过这悲剧性却被最后的妻子厨房的美食所掩盖,丈夫也会欣然动筷,品评妻子的厨艺。诗人反躬自省,自己的这种不问鱼儿来历和命运,只管享受美味的行为不也是戕害鱼儿的阴谋系列吗?自己不也是谋杀鱼儿的同谋吗?
盘中的石斑鱼,向空中翘起几根鱼刺,悲凄地控诉着人们的恶行。而饭桌上的人们全然不觉,他们高谈阔论,吟诵着: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诗人悲愤地加了两句:子非鱼,安知鱼之苦 /子在濠上,鱼在俎上。构成了对这些表面风雅实际残忍的吃客们的辛辣的讽刺,你们怎么才能体会到这鱼的悲惨?你们站在岸上吟风弄月,鱼儿却在砧板上被解剖砍剁,你们于心何忍?
自此诗人完成了对这鱼儿命运的全部同情和思考。诗人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仅仅是怜惜一条鱼的生命,还能够由鱼及人,将更深广的社会意蕴注入到对这条鱼的命运的思考中。如将人的无法还乡的愁绪赋予这条死去的鱼,将鱼的生存环境的险恶比喻人的社会生存的不易,同时还批判了满口经纶的人类心灵的麻木和他们内心的虚伪。
当大家无视菜市场中一条鱼的死亡,只管在觥筹交错中畅享这美味的鱼宴的时候,这不正在上演一场鲁迅意义上的“近乎无事的悲剧”的悲剧吗?只不过鲁迅批评的人们对自己的同类作为牺牲品的麻木,而余光中在这里则讽刺的是人们对于这些异类生命被涂炭时表现出的麻木。鲁迅的社会批判是黑色、晦暗和沉重的,而余光中这里的讽刺是温和节制却又让人不安、令人警醒的,二者社会批判的精神是一脉贯通的,都体现了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和针指人性之弊的气魄,而文本演绎的风格个性却又各自不同。
要做纯洁与高尚的人,人不仅要面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要面对人与其他物类,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一个当代人,具有这种意识就更为必要。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的立意似乎又高了一层,具有生态意义和寰宇视野,这首诗的当代性特征也在这一刻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