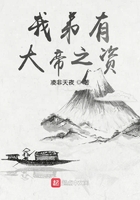梁小斌生于 1954年,山东荣成人。年轻时下乡插队落户, 1972年开始写诗。后来当工人,因爱好写诗不能经常上班, 1984年被工厂除名,之后一直靠阶段性打工维持生活。正如有些评论者所说,梁小斌是他们那一代写诗的人中最没有从诗歌写作的成功中获得实际好处的人。
梁小斌的《雪白的墙》《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发表后,引起巨大的反响,成为朦胧诗的经典之作,也有人把这两首经典诗歌当做是“伤痕文学”的代表作。《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写在 1979年,首次刊载于《诗刊》 1979年 10月号上。 1978年在政治上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而 1979年又是中国思想解放、最为活跃的一年,这首诗的发表,又以诗意感召的形式将人们进一步唤醒。
十年“文革”是“革命”的疯狂,当人们沉浸于虚妄的红色革命时,它让人们的生活迷失了很多东西。生活中本该有的童真、诚实、爱、美和自由,在十年疯狂的追寻中都失落了,而这个自由童真的世界正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精神家园。按照诗人的比喻,十年“文革”就像人们沿着大街疯狂的奔跑,在奔跑中,人们回归家园的钥匙已经丢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就是作了一个这样的比喻,这首诗是在一个时代结束、民众猛然觉醒的大背景下发表的,这引起人们极大的共鸣。一时间标为“中国,我的 XX丢了”的诗满天飞,梁小斌借这首诗表达了自己的企盼和理想,而这样的理想又是整个时代的企盼。不仅仅是一个小孩遗失了回家的钥匙,一个国家的民众都遗失了理想国的钥匙。
那一年中国“觉醒”了,他们发现他们遗失了“钥匙”,这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也是一个准确的描述,诗人用诗歌简洁的方式勾勒出了一个沉重的命题。这也是梁小斌诗歌写作的一个明显特征,总是用一个单纯的形象或故事来说明一个深沉厚重的主题,在这首诗中就是用一个儿童的迷失来比喻人民整体的历史失落。这在《雪白的墙》中也有类似的形象建构。
说的是孩子,指称的是历史,诗人代人民立言,这样的诗人是时代的诗人。而若干年后,梁小斌却为这种大众理想的表达进行了忏悔。 2007年,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梁小斌发表了以下忏悔的言论(梁小斌:《我为〈中国,我的钥匙丢了〉忏悔》,载《南方都市报》2007年 2月 8日):
……(《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这首被称为“新时期文学”代表作的诗,引来了不少读者给我写信,甚至有解放军战士把家乡房门的钥匙寄给我,他也要奔向荒野,尝尝“丢失钥匙”后的心灵滋味。
……一个诗人在写出“钥匙”之前,他在写什么样的诗呢?我曾经说过,我是个逃离上山下乡劳动的冠军,但我的确由衷地抒发过“第一次进村”的情景,来讴歌知识青年到农村的那场运动。我记得,当“公社美景看不够”时,到底是把麦苗采在手,还是把麦穗拥在怀,我颇费心思。因为麦苗在手,是破坏春耕,而采下麦穗,又是掠取人民的劳动果实。诗人对一个举动作如此揣测,说明他的心迹仍然处在左右摇摆之中。
一个诗人必须对他写的诗承担责任,这是我心头的沉重石头,我在讴歌那个暴戾时代的时候,因为早有《理想之歌》在我的头顶,我在那个理想主义的诗坛上,没有哄抢到“暴风雨中的海燕”那顶桂冠。没有抢到并不说明就没有抢夺的愿望,没有抢到活的阶级敌人捡回来斗,我只抢到阶级敌人留在家里的坏思想。
……我忏悔!当代文学里解构思想看上去具有批判精神,实际上如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一样,只是控诉主义骗局的变种,如今的青年诗人们看上去什么事情都未参与,当别人把“腐朽”的大厦盖起来之后,他们猛然成为一个拆建筑的人。我们能提供的所谓“诗歌经典”,就是这样无形地毒化着后人。
……我忏悔!《中国,我的钥匙丢了》违背了我们的前辈巴金先生所倡导的“说真话”的原则,我建议,将这首诗从所谓的诗歌经典系列中永远抹去。
在这篇忏悔文章的最后,作者又重申了“天问诗歌公约”,他认为“每个诗人都应该维护诗歌的尊严”“诗人必定是时代的见证”,而“一个坏蛋不可能写出好诗”。诗人的忏悔是用人们对诗的圣洁解读来对照自己逃避上山下乡的行动,对照自己曾经对上山下乡的不够真诚的讴歌,以及自己曾经向往向体制中认可的经典性作品看齐的渴求。在对照中诗人进行了真诚地反省和忏悔。也就是说他自己在历史中有非常因循的一面,即便在“文革”中,他也从心里认同并紧跟热闹的“革命运动”,只不过在“四人帮”被打倒后,民众反省“文革”,他才开始写诗反思“文革”。
梁小斌觉得生活中的诗人和诗中的形象应该保持一致,这不仅仅是道德问题,更是一个对于诗歌的信仰问题,是“诗行合一”。自己在诗中好像是个先知先觉者,而实际并非如此,这在他看来有违真诚。他主张“单纯性是诗的灵魂”,其实也就是诗行合一的问题,在梁小斌看来,“诗人”是一个高尚的头衔,任何不称这个头衔的行为甚至想法都要忏悔。诗人要有殉难的态度和勇气,才能写出真实的生活。这篇忏悔式的说明恰恰说明了诗人勇于自省和自我批判的精神。
诗人不仅要忠实于自己内心,还要体察历史的真实脉动,这样写在当下的诗歌才会成为历史的永恒记忆。在另外的场合,梁小斌还说:“我希望通过我写的东西,使人觉察其实每个人都过着相同的精神生活,不过是被很多人忽略了,我重新表达那些被忽略的。 ”(梁小斌:《梁小斌作品及诗观》)这可以看做是诗人忏悔之后的新的发现。诗人忠实于自己的生活,才能体察这个时代所有人的生活,这里要说的其实也就是诗人所说的“见证时代”,而这种见证需要极大的诚实。梁小斌的这个忏悔更表明,诗人要始终保持对理想的追求,家国期望只是一个有限的理想,对于永恒的诗歌来说,应有更高的人性与人格的理想要求。
无独有偶,北岛也对自己进行过类似的忏悔,他以自己的诗歌《回答》为例说:“现在如果有人向我提起《回答》,我会觉得惭愧,我对那类的诗基本持否定态度。在某种意义上,它是官方话语的一种回声。那时候我们的写作和革命诗歌关系密切,多是高音调的,用很大的词,带有语言的暴力倾向。我们是从那个时代过来的,没法不受影响,这些年来,我一直在写作中反省,设法摆脱那种话语的影响。对于我们这代人来说,这是一辈子的事。 ”(北岛:《游历,中文是我唯一的行李》,载北岛散文集《失败之书》,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这和梁小斌的忏悔性质是一样的,都是他们那一代诗人力求发现自我——而不是一个自己身上的“非我”——的努力。诗歌是心灵的,诗人要荡涤心灵,才能发出纯净的“诗”的声音,而这种荡涤,需要不断地忏悔和自我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