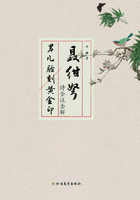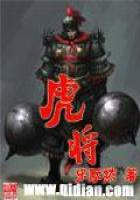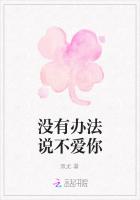《观出有感》从题目看,是要讲抽象道理的,属于理性认识的范畴,写成论文可以,如果写诗就有困难。因原诗比论说还要概括精炼,如把观出的感想概括成四句话,就只剩几条筋了,怎么能感人呢?所以诗人没有直接写成议论,而是借形象比喻来曲说的。首先诗人把书中的思想境界比喻成像半亩池塘的池水一样,其光洁度又比喻为有如明镜一般,而其丰富的内容又以映入池中变幻莫测的“天光云影”比喻,于是抽象的不便简括论明的内容,具体化了,形象化了,而且也真美。明镜般的池水,池水中游动的天光云影,不禁使读者联想到这书的思想内容该是何等的丰富高洁,令人爱恋,恨不能也读到这样美的书,得到这样的艺术美的享受。赞叹之余,诗人又发出启人深思的一问:“哪得清如许”。清者明也,论理透彻之谓也,末句指出:这是由于书作者思想修养、学问积累之高深所形成的,是借鉴前人成果加上自身观察体验现实生活的结果。这一切,诗人只用“源头活水”比喻论出,便道尽了“清如许”的内涵,使人由源头想到溪流,由溪流想到池水。是啊,没有源头之流,哪儿来的半亩方塘?没有活水的不断注入,哪来的水明如鉴?没有水明如鉴又哪来的“天光云影共徘徊?”到此观感抒发详尽。之所以收到如此动人效果,正是由于诗人把理性认识经过形象比喻,使之回到感性认识,然后以感受的形象来启迪打动读者的心灵,引起美感的共鸣,再在读者脑中升华原理性认识。这就是曲说的力量。
什么情况该直说,什么情况曲说,这只是一例。但是,它告诉我们一个起码常识:即便于直说的不应故意曲说,不便直说的用曲说能收到诗的效果,那就曲说。
§§§第5节直说与曲说(之二)——读杜牧二绝句
杜牧以《阿房宫赋》而被人称为“王佐之才”。如果说《阿房宫赋》是以“词华觉盛”而著称,那么他的七绝《过骊山作》则以“无华”而见胜。
“黔首不愚尔益愚,千里函关囚独夫。牧童火入九泉底,烧作灰时犹未枯!”
诗人简直是扠着腰,怒目横眉地在诅咒历史上的暴君:你秦始皇实行愚民政策,妄想让人民万世受你统治,结果与你的愿望相反,你“使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激起了万民的怒火,“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灭亡的却是你自己!谁愚谁智?是你这个暴君才愚蠢到家了。你虽然早死秦亡前的三年,厚葬于骊山,但是如今从函谷关往西旧秦千里国土已都变成了囚禁你的巨牢。而在后人心目中,你是十恶不赦的千古罪人,就连无知的牧童也不曾饶恕你,他们也要放起野火直烧到九泉之底,把你的尸骨烧为灰烬,可是你的罪责“犹未枯”,骂名千载,也难解世人之恨!
这首诗真是直泻胸愤,痛快淋漓,毫不雕饰,完全出自自然。“诗情豪迈,语率惊人”,大概就是指这类诗说的吧!当诗人感情达到怒不可遏的亢奋程度,只好直说。直说出的每字每词都有如利箭、飞刀、炮弹般喷射出去,达到直中敌命而后快。
同是吊古,杜牧的《赤壁》诗则又别具风貌: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
诗人在赤壁拾到一段沉沙的铁戟,经过磨洗,认出是前朝汉末时的遗物,不禁想起汉献帝建安十三年著名的大战役——赤壁鏖兵的历史来。那场大战,尽管史书上一再赞美周郎的功绩,依我看,要不是有刘备一方的配合,并力击曹,孙方恐怕早已灭亡了。这里既肯定了孙方周郎指挥的功绩,又强调了刘方与之联合的力量。既不是抑孙扬刘,当然就用不着激昂陈辞,需要的倒应该是婉转含蓄,令人有回味咀嚼的余地。所以诗人没有像对秦皇那样直接抒愤,而是借“折戟”起兴,引起吊古抒怀;而抒怀又不是直接议论,诗人巧妙地借“东风”喻指刘方,借“铜雀”喻指曹方,借“二乔”喻指孙方,而中心人物却放在“周郎”身上。因为当时是曹操亲率八十万大军征讨孙权,孙权的指挥主帅是周郎周公瑾。但是,此时孙权兵力实不足以抗曹,幸有刘备派军师诸葛亮为周瑜谋划,借东风,用火攻,刘孙大军夹击,才达到破曹的目的。据《三国志》载,诸葛亮确曾借过东风:“孔明于十一月二十日甲子吉展,沐浴斋戒,身披道服,嘘足散发,到坛祈借东风。三更时,瑜出帐看旗脚,竟飘西北,霎时间东南风大起。”当然这可能是诸葛氏故弄玄虚,但是诸葛亮晓天文,知地理,对气象变化能推算以至预知几天内有何风向,却应该是意中事。如果他不算出东南风起之时,那么火烧赤壁将是不可能的。是东风给了周郎火攻之便,否则“东风不与周郎便”,那么这段历史就得颠倒过来:被击溃的不是曹军,而是孙吴的大军。
曹操于建安十五年(210)冬在邺城(今河北临漳县西)建成铜雀台。此次南征,距台成之日还有二年,曹操就在水寨中贪婪得意地发出狂言:“吾今年五十四岁矣,如得江南,窃有所喜,昔日乔公与吾至契,吾知其二女,皆有国色,后不料为孙策、周瑜所娶。吾今搆铜雀台于漳水之上,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以娱暮年,吾愿足矣。”铜雀台尚未建成,曹即作如斯幻梦,正见其得意忘形之极。今杜牧用这一句结尾,不只嘲笑了曹操的幻梦破灭。而且也讽喻一下周瑜,并提醒那些周郎的吹捧者:赤壁之战,破曹取胜,不是周郎个人的功绩,假设东风不与其便的话,曹操不但要吞掉江南,而且还要把周郎的爱妻以及妻姐——孙权的寡嫂掳到铜雀台,供曹娱其暮年。可见这“东风”的力量该有多大!这首诗的诗眼就在第三句,特别在“东风”二字上。
这是诗人锐敏观察、冷静分析的结果,借隐喻折光来寓以警醒之意。这是曲说,含而不露,一经悟出其中道理来,又非常深刻。
但是,这一曲笔却被人们误解过。宋人许彦周竟怪罪杜牧“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其大不识好恶。”他不懂得艺术善于以小喻大,以物明志的道理,竟以为杜牧真的丢了西瓜捡芝麻。而何焕文驳许时,也只是说:“诗人之词微以婉,不同论言直遂也。牧之之意正谓幸而成功,几乎家国不保。”按何说,则“赤壁”一诗是庆幸孙权“幸而成功”的赞歌了,这未免肤浅。此外,还有人说杜牧作诗“好异”,好用“翻案法,跌入一层”,都在驳许氏的“不识好恶”,所以都在末句“二乔”上兜圈子,直至近人也还是强调末句的教训意义。而对“东风”,则都理解为自然界的东风,没有一个人指出“东风”应与诸葛亮有关,更很少见到有人谈到诸葛亮代表刘备一方势力,在赤壁之战中给孙权方面以东风般的援助力量,是孙刘联合的力量才取得抗曹的巨大胜利。而这个力量的发现,正是杜牧写这首诗的深刻独到之处,是诗人的警醒之笔。反跌,不在末句,而在第三句“不与”上。“不与”正翻出“与”的力量。这样写,对周郎既爱护又醒谕,而醒谕又寓于幽默的爱护之中,才显得情趣盎然,引人遐想。
§§§第6节直说与曲说(之三)——读贺知章《回乡偶书》二首
贺知章(659~744),字季真,越州永兴(浙江萧山县)人,三十七岁擢进士,陆象先引他为太常博士,张说荐举他入丽正殿书院修书。开元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累迁至秘书监。知章为人秉性放达,为当时贤达所倾慕。陆象先说他“清淡风韵,一日不见,则鄙吝生矣。”与李白交友,甚至出现“金龟换酒”的佳话。知章是当时“饮中八仙”之一,杜甫作诗写他的醉态:“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他不是一般的狂饮,而是“醉后属词,动成卷轴,文不加点,咸有可观。”他写的东西,人们争以为宝。可惜现在遗留下来的诗仅剩十九首,只有六首是绝句。他的诗:“不尚藻彩,不避俗语,似乎无意求工,而时有新意。”即以《回乡偶书》来看,正好体现了这一特点。
一、“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难)改鬓毛衰(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二、“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距今虽已一千二百多年,但是口语化的程度,到今天看来仍觉流利亲切,没有一个彩藻词汇,没有一点斧凿痕迹,读来琅琅上口,一听就懂,好像夏日畅饮一杯解渴的“凉白开”一样,虽无茶香糖甜的味道,但是顿觉一阵清爽,沁人心脾。
这两首诗不知背景的人读来,也觉得好。因为诗人用平常语道出了常人的回乡之情,引起共鸣,由少小离乡到老大回乡,漫长的岁月,使青丝发已变成鬓毛斑了,一代少儿又长起来,老一代已有半数消磨殆尽,所幸自己乡音仍然未改,镜湖依旧扬波,从今后仍可以与乡亲一起生活在镜湖岸上,度尽余年。
知道背景的,读来则更有味道,好比刚才饮的“凉白开”,当你知道它是白沙水或是热河泉时,你当发生种种联想,在淡淡的白水中,又巴哒出一种新的味道来。
贺知章这次还乡是告老退隐山林而来的,年逾八十不愿再在朝廷空享俸禄。史书记述,说他曾“梦游常居”,醒来立即上表请求还乡当道士,把自己的住宅献出做“千秋观”。当时正处于安史之乱的前夕,唐玄宗正在过着“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的糜烂生活。杨妃得宠,国忠乱朝,安禄山权倾太斗,高力士红得发紫,长安城这个“帝居”已成了一片纸醉金迷的世界。一位有良心的诗人是痛不忍睹的,所以他晚年“尤加纵诞,无复礼度”,借狂饮以消愁,犹不可,又学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来个“归去休”,离开京都,回到生育自己的故乡去,以求从晕眩迷离中解脱出来。
唐玄宗很赏识他的才学,看他年老退隐,不只立即批准,还“诏赐镜湖剡溪一曲”,并亲自赠诗送行。知章又是太子宾客,所以太子又召百官为之饯行,这也是一时的盛况吧!这种境遇不是朝官退居时都能享受到的。他能受此宠遇,作为封建士大夫来说,是值得夸耀的。
他怀着上述两种心情还乡,可是诗中既看不到过度的哀伤之情,也看不出衣锦还乡的荣耀之感,完全摆脱了常人的想法。所谓脱俗,出以新意,也即在此。
第一首比第二首流传得广,据说国外都有为之谱曲传唱的。原因何在呢?我们且来咀嚼品味一番。
“少小离乡老大回”,虽七个字,却概括写出几十年的生活,从少年到老大,由离乡到回乡。这几十年有什么变化呢?第二句作了回答:首先是“乡音无改”。古人不像今人,提倡学普通话,他们是以不改乡音作为热爱家乡的美德的。贺老诗人对家乡是眷恋的。有一首“晓发”五言绝句,可能是写他“少小离乡”情景的:
“故乡沓无际,江皋闻曙钟。始见沙上鸟,犹埋云外峰。”
可以看出他离乡之时是恋恋的,又是兴奋的,但是在恋恋兴奋之余,却担心自己将来像沙上鸟一样,飘落到“云外峰”去。如今他从“云外峰”,又能回到“沙洲”一样的故乡,自然是对青年离乡时的一个安慰,回来了,没有抛身他乡。虽然鬓毛衰白,年逾八旬,毕竟是回来了。这种感情犹如“飞鸟恋旧林,时鱼思故渊”。
当然,我们今天的青年是要“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要为共产主义理想展翅高翔,不能因恋故乡而影响事业前途的。我们今天爱家乡,就要化成力量,把亿万人的家乡都建设得更美好。古人不可能有这样的宏图大志。但是,贺知章能看清唐王朝当时的危机,自己感到年迈无力正乾坤,而要保持晚节,退居故乡,这在士大夫中还是少见的。
回乡路上以至到家乡村口,见到的人或事肯定是不少的,但是,别的都舍弃未写,专选与儿童会见时的一个场面来抒发情怀。这是很别致的。儿童与八旬老人相对照,该是第三代人了,“相见不相识”乃自然之理。一因离乡年久,不用说儿童,即童年故交相见,也不易相识了。一是因为儿童年幼无知,明明我“乡音未改”,却也认不出来,反以为客,竟自“笑问客从何处来”,本乡之主反而为“客”,真使老诗人下泪;可是儿童却笑问。笑,不只活画出儿童的天真烂漫的赤子之情态,逼真动人,而且一问,也画出儿童俨然以主人自居,把诗人当客来接待。自己虽自认为“无改”,但是客观却都在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地在改。自己的鬓毛衰了,可是儿童却已长大能到村头迎客了。鬓衰堪悲,笑问可喜,悲喜交织,这是老诗人回乡的新鲜感受。从老诗人这方面讲,也侧面烘托出其朴实的本色,不只“乡音无改”,其潜台词也在说明老诗人依然布衣,两袖清风而归,既无鞍轿之威,更无朝服之盛,使儿童一见备觉亲切,如待常客一样,敢于上前还不算,还敢于“笑问”,于是主客之悲又立即转化为老少之情了。鱼回故渊,与鱼同乐;鸟归旧林,与鸟同欢。于是老诗人回乡前后的复杂感情,通过这一小小镜头,都折光地反射出来。这是直笔中的曲笔,是淡色中的深情,是无味之味的妙味。
第二首为什么不如第一首那样脍炙人口呢?有人说因为说得太直了,不如第一首那么形象。上边我们分析了,第一首之所以好,不只因为形象,而是看他形象中透出了怎样的情思意趣。第一首不仅写出了人之常情,能引起人们的共鸣,而且又有作者自己晚年独特的复杂的回乡之情思,这首诗的境界超越了一般士大夫“显亲扬名”、“衣锦还乡”的俗气,具有一种人生的深沉的思想意义,含有一种人生哲理,少小难免老大,官高不免辞官,离乡不免归乡,主可以变为客,客又可以转而为主,自身虽已鬓衰,儿童却已成长。这首诗在生动形象中却韵味无穷,情思绵邈。
第二首缺的正是这些东西。头两句基本重复了第一首的开头两句,所不同的是第二句,一写己之变化,一写他人的变化。三四句表面是写家乡的风光依旧,联系前两句好像在叹息“人事已非”。但是,联系回乡的背景一琢磨,就会感到贺老诗人想到的是皇恩浩荡——钦赐的镜湖剡溪,在春风中“不改旧时波”。暗喻皇恩抚育之情在诗人心中感到无限快慰。这种对皇恩感激莫名的情怀,自然就不如前一首高尚了,也就难以找到知音了。虽然在写法上末两句也是直中见曲,但情怀不佳,因此意境不高,当然毫无美学价值之可谈了。
§§§第7节诗贵出新
今年在双塔寺举办了大型的赏牡丹诗书画盛会。会上有众多的诗书画作者在百米白绢上题诗作画,有不少佳作出现,令人赞赏不已。但是,在赞赏之余,又不免感到有些许遗憾:为什么有些作品都好重复这些词语:“国色天香”呀,“荣华富贵”呀,“仙子降凡”呀,“争奇斗艳”呀,长绢上留下这些陈词旧语,不是和塔壁上留下的“到此一游”有点大同小异么?
“双塔高高凌云霄,牡丹盛会掀高潮。百花齐放人人赏,国色天香实在高。”
且不说韵律不合,单就内容看,虽然把这次活动全概括了,可是,这首诗抒发了什么情?除了客观介绍以外,谁能从中感受到有多少诗情?第一句只起点明地点的作用,二三句只介绍了参加会的人的兴致,第四句借用前人用滥了的成语赞美一下。诗句虽然顺口押韵,层次也清楚,内容也全面,可就是不动人,算不上一首好诗,为什么?答曰:不新。写新发生的内容,又是当时即兴写的,还不新么?答曰:还是不新,因为你所谓的新是指时间上的新,而不是诗的新。什么是诗的新呢?请看元好问是怎么说的:
“晕碧裁红点缀匀,一回拈出一回新。鸳鸯绣出从教看,莫把金针度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