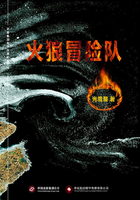狗剩上去把梅琴的碗夺过来扔了,说:“你个地主羔子还忆什么苦?”
张大嘴正想说自己真的不中用,可不知怎的,他感到一股热流在腹内滚动,下身突然坚挺起来。
梅琴感伤地说:“我像沉溺于茫茫大海之中,我自己是难以自救的。只有一个人能救我。”
梅广济没有借到二队的那头高头大马,只好用自己队里的那头小毛驴去接李玉芬。一大早他就抄起扫帚把毛驴扫了又扫。尘土伴着驴毛在院子里飞舞,毛驴舒服地发出一阵长鸣。有根驴毛钻进了梅广济的鼻孔,鼻腔里直发痒,头一摇,一连打了好几个鼻嚏。他把毛驴上上下下地打量了一番,看到四个蹄子还不太干净,就端来温水,用自己洗脸用的毛巾一遍遍地擦,看到毛驴全身一尘不染,才牵起毛驴往外走。刚走到门口,又牵着毛驴回来了,他把毛驴拴到树上,到屋里取出当年国梁娘给国梁做下的结婚用的红被子,铺在了驴背上。
李玉芬下身是一条蓝裤子,上身是一件红夹袄,嘴唇红红的,像是用红纸涂过了。梅广济牵着驴走在前面,逢人便介绍这是我老婆。大家心里话,在一个大队里生活了一二十年了,谁不认得谁啊,还用得着介绍啊!但谁也没有说,只是一个劲地道喜。人家道喜,梅广济就说:“同喜,同喜!”
围着大队走了三圈,梅广济仿佛意犹未尽,便又走一圈。
这时,郭子顺牵着高头大马回来了,马上坐着他的老婆于莲。于莲的胯下也铺着红缎面的被子,下身是一条蓝裤子,上身是一件蓝褂子。色彩上总体不如李玉芬艳,但她胯下的马头上却多了一朵大红花。四人走了对面,于莲那种清水芙蓉、居高临下的气质,让李玉芬感到相形见绌,李玉芬两腿用力一夹毛驴,说:“回去!”
郭子顺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自豪感,摇晃着手中的马缰绳,唱起了梅花调:
当今天子坐金銮,如同舜日如尧天。
人民享尽无疆福,大家同乐太平年。
皇上圣明天下和,平头百姓乐陶然。
吾等生在太平世,财源广进不得闲。
回到家,郭子顺把老婆从马上抱下来,一直抱到炕上,把门一关就和老婆亲热起来。
左邻右舍听说于莲坐着高头大马回来了,都来看热闹。结果,大家发现院里只有一匹驮着被子的枣红马。
狗剩捅开窗户纸一瞅,捂着嘴笑了。
苏秀问:“怎么回事?”
狗剩说:“拉秧子哩。”
梅广慧和卢特派员召集全体党员干部商议割资本主义尾巴的事,屋里一片烟雾,大伙谁也不说话。卢特派员说:“割资本主义尾巴,是一件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它关系到走什么道路的大是大非问题,我刚才讲的一二三工程,就是从根本上限制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我们都是党员干部,立场一定要明确。”
梅广慧见没人发言,就对张二秃子说:“二哥,你谈谈自己的看法。”
张二秃子耍了个滑头:“我这个人没什么见地,还是听听大家的意见再说吧。”
梅广济是个急脾气,把手里的烟扔到地上,说:“我说两句。卢特派员的一二三工程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分界线?一分自留地、两只猪、三只鸡是社会主义,多了就是资本主义。我想问一问,要是生两个孩子,他就是社会主义的后代,要是三个四个就是资本主义孝子贤孙了?那就得把老三老四拉出去枪毙了?”
卢特派员一听,就把脸一沉,把桌子一拍说:“梅广济,你什么态度?你还是共产党员吗?”
梅广济毫无惧色:“人都是吃五谷杂粮长的,如果说社会主义的草人也能吃,好了,卢特派员,明天你就到我家,我给你准备最鲜嫩的草。”
大伙见队长这样说,也都开了腔,有的甚至大笑出这主意的人是龟孙,不是吃粮食长大的。
卢特派员听了,脸立时像刚出锅的蟹子,但又像哑巴吃黄连,无言以对。他好长时间没有说出话来,感到有点渴,拿起缸子就喝,结果里面一滴水也没有,一生气把缸子当的一声暾在桌子上。
梅广慧见局面有些僵,就说:“要不大家先回去,广泛征求一下社员的意见,过后再讨论。散会!”
过了好一会儿,梅广慧见卢特派员的情绪稳定了,就说:“卢特派员,阶级斗争是纲,但抓纲有很多方法。比如说召开忆苦思甜大会,吃忆苦思甜饭,都是很好的形式。通过这些形式,让大家想想过去,看看现在。用切身体会感受还是社会主义好。”
开始,卢特派员背着脸,不理梅广慧。听梅广慧这么一讲,他觉得也很有道理,就说:“我看也行,这事你就具体安排吧!”
全大队的人都集中到大槐树底下,等着吃忆苦思甜饭。忆苦饭有地瓜面窝头,有用野菜和豆饼渣煮成的菜豆腐,还有一锅当镜子照的稀粥。
梅琴也来吃忆苦思甜饭,狗剩上去把梅琴的碗夺过来扔了,说:“你个地主羔子还忆什么苦?”梅琴流着泪走了。
大油袖也来吃忆苦思甜饭,狗剩又上来要夺大油袖的碗。大油袖说:“我是中农,我娘家是贫农,为什么不让我吃?”
狗剩说:“你男人是地主。”
大油袖从怀里掏出一把剪刀,对着狗剩说:“你要是敢夺我的碗,我就把你那东西剪下来喂狗。”狗剩下意识地捂住下身,惹得大伙哈哈大笑起来。
梅广慧向四周看了看,没见张大嘴,就问身边的赵诗文:“张大嘴怎么没来吃忆苦思甜饭?”
赵诗文说:“张大嘴摔断了腿,在炕上躺着呢。”
梅广慧担忧地说:“那还不把他饿死?”
赵诗文说:“我让团员轮流着给他做饭。”
梅花用大黑碗盛了一碗稀粥,又领了三个窝头,准备给张大嘴送去。这时薛蓉走过来,对梅花说:“给我,我去送。”
梅花说:“娘,我去吧!”
薛蓉说:“我去看看他!”
薛蓉觉得自己不该让梅广济迅速作决断,感到张大嘴丢了老婆、摔伤了腿自己有推不开的责任,她带着一种负罪的感觉来到张大嘴家。一进门,薛蓉就听到张大嘴在叫苦连天,赶紧跑进屋,看到张大嘴用手揉肚子,问张大嘴:“大嘴,你怎么啦?”
张大嘴说:“肚子疼。”
见张大嘴肚子疼,薛蓉就说:“我给你揉揉吧!”
左三圈、右三圈,薛蓉一遍一遍地给张大嘴揉。她感到张大嘴的肚子是一块夹生面,又风干了一层坚硬的皮,一块软,一块硬。薛蓉左手揉,右手捏,张大嘴肚子渐渐软和起来,也就渐渐不叫了。
“还疼吗?”
“见轻。”张大嘴脸色好看了许多。
“可能受了凉。用手再捂一捂就没事了。”薛蓉把手放在嘴上哈了一口热气,又用力搓搓手,然后把手捂在张大嘴的肚脐眼上。
仿佛一股电流从薛蓉的手上,通过张大嘴的肚脐眼进入他的五脏六腑,直达神经末梢,他立时像里里外外在清水里淘洗过一番,全身通泰。
望着薛蓉那平和、俊俏的脸庞,默默地感受着薛蓉一个中年妇女的特有的温柔,张大嘴眼里不觉流出泪来,深有感慨地说:“李玉芬那头母老虎,如果有大妹子一半就好了。”
薛蓉说:“大嘴,你给大妹子说,你两个到底为什么过不到一块去?”
张大嘴嘴一咧哭着说:“她骂我是骡子,说我不中用。”
薛蓉说:“你到底中用不中用?”
张大嘴正想说自己真的不中用,可不知怎的,他感到一股热流在腹内滚动,下身突然坚挺起来。一种从没有过的欲望像飓风一样不期而至,他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一下子抓住了薛蓉的手。
赵诗文端着自己的一份忆苦思甜饭,来到梅琴家。梅琴正在院里落泪,见赵诗文来,就进屋拿手巾擦泪痕。赵诗文把饭端到梅尚德的床前,梅尚德赶紧用力起身。梅琴过来扶起父亲,接过稀粥和窝头,说:“爹,您吃点吧!”
梅尚德像一株即将干枯的老梅树,流光了生命的汁液,憔悴的枝干一用力就会断成两截。看到赵诗文,梅尚德感激地说:“赵书记,您的大恩大德,老朽只好来世再报了。”
看到梅尚德这般清瘦,听到梅尚德这么客气,赵诗文心里很不是滋味,说:“论辈分,我得叫您爷爷,我是您的孙子。爷爷,您叫就我诗文好了。”
梅尚德说:“好、好,就叫诗文,就叫诗文。我说,诗文呢,你看我这样子,估计也没多长时间的活头了,我有句话不知当说不当说?”
“您有什么话,就尽管说。”赵诗文用一手扶住梅尚德的脊梁。
梅尚德说:“梅琴这孩子性格孤僻,你还得多开导着她点。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可是咱这个成分很难让她找个合适如意的,你见多识广,给梅琴上上心。”
梅琴有些不好意思说:“爹,您说什么呢?”
梅尚德说:“有些话,也只有给诗文说说,也只有诗文能理解你心里的委屈。”
赵诗文说:“您敬请放心,梅琴姑会找到如意人的。”
梅琴惨白的脸颊上泛出了一丝红润。
赵诗文要走,梅琴跟了出来,赵诗文收住脚,问:“这几天写作情况怎么样?”
梅琴自责地说:“我这个人真是太笨了,就是找不到感觉,总也摆不脱个人情调。”
赵诗文:“拿来我看看。”
梅琴回到自己的房间,拿出一沓诗篇,递给赵诗文。赵诗文看了梅琴昨晚写的小词,说:“其实,这些诗词我很爱读,很能打动人,但又觉得不合时代。我让你写跟时代的诗,主要是让你摆脱目前的心境。”
梅琴感伤地说:“我像沉溺于茫茫大海之中,我自己是难以自救的。也许,也许只有一个人能救我。”说到这里,止住了,梅琴的目光直盯着地面。
“谁?”
“你!”梅琴低声吐出了一个字,脸上的红润化成了两片霞光。
赵诗文的心猛地跳了一下,神经也像被弹了一下:我!他突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一个“救”字,无疑把自己的命运和梅琴紧紧地拴在了一起,在政治斗争的旋涡里,自己也许救不了梅琴,还可能把自己也搭了进去。如果和梅琴彻底脱清干系,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子岂不就此凋零?这也许是自己最不愿看到的。
他伸出手,轻抚一下梅琴的胳膊:“姑,你放心,我会尽力帮你的。”
赵诗文走出很远,回头看了一眼,梅琴还站在门口望着自己。他感到梅琴是暮霭中的一朵彩云,是白雪下的一枝寒梅,更像是秋风中的一只寒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