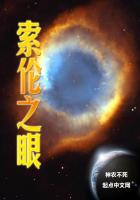已经是深秋了。
这是一小方天井,墙下周遭种满草木翠竹,置身其中倍感绿翠怀荫,不时有微风有头顶被隔成正方形的空中拂过,撩人衣襟,相思坐在一棵参天古木下的长椅上,头稍稍靠着斑驳的树干,似是睡着了。
苏褚透过窗户看着院子里的人,有风从她脚下溜过,轻轻掀起她的裙角,她却一动未动,身侧的古树高大粗魁,更加衬得她身形单薄,他拿了薄毯出来,轻轻盖在她身上,小心翼翼生怕惊扰了她。
不过是疲乏时的浅眠,只一个轻微的动作,相思便醒了过来,看清了眼前的人,淡然轻笑。
随他回香港以后她便大病一场,这病丝毫没有来由,之前毫无征兆,苏褚请家庭医生看过,却也不得结论,只是说人太劳累,外加有些水土不服的症状,既然不是大病,相思也不愿意吃药,就只好这样静静养着。一开始是随他回了苏家的豪宅的,但苏家在香港乃是大族,家中免不了人来人往,他知道她喜静,又念着她的身体,便将她从家里接到这。
这里很好,虽是老宅,却素雅清净,偏院还有这一方小小的天井,相思闲来无事便来这里坐坐,偶尔看书,偶尔和他树下品茶,宅子里只有一个家佣,是从家中跟他们过来的,只是负责平日三餐和日常打扫,话不多,也从不主动打扰他们,有时苏褚出门,这宅子里安静的便就像只剩下她自己,可依旧来这天井闲坐,翻书喝茶,或是什么都不做,独自发呆。
苏褚在她一旁坐下,将她扶进怀里,他极力让自己这个动作看上去自然而然,心里唯恐她的抵触,但意外的是她并没有,甚至比他还要自如平常,自然柔顺的随着他的动作将头靠在他肩上,长发垂下来,仿佛一点也不感到意外。
他身上有淡淡的烟草气息,陌生又熟悉。
过了这么多天她身体渐渐复原,只是经常觉得疲惫,事实上她什么家事都不曾做过,每天有大把大把的时间,只用来休息,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觉得身心疲劳。
苏褚将她身上的薄毯向上拉了拉,略带征询的说:“这周末璨璨要订婚了,跟我说一定要你去参加她的订婚宴,这丫头任性惯了,别说我,有时连我妈都管不了她……”
苏璨是他同母异父的妹妹,这她当然知道,不过还是诧异非常:“订婚?她才十九岁就……”
话一出口才知道是自己又犯了傻,是了,这是香港,不是大陆,只要年满十六岁,别说订婚,哪怕是结婚都丝毫不奇怪。
第一次和那位十九岁的豪门千金,他的妹妹见面,相思便觉得她似骄阳一般活力新鲜。那时她刚到香港不几天,还住在他家里的豪宅,一天傍晚时分,众人正端坐在长长的餐桌前吃晚餐,那个活力四射的小姑娘突然闯进餐厅,笑着叫:“哇哦,嚟得好,不如离跷,我啱啱落飞机,饿死咗!”她说粤语,相思转了转神才能听的明白。
佣人给她添了餐具,盛了汤,她就坐在她妈妈旁边,捧着汤碗刺溜刺溜,几口便喝了一大碗汤,哪有半分名媛淑女的样子。
她母亲皱眉拍拍她的手,提醒说:“别胡闹,没看到有客人吗?”虽是责备,口吻却依旧宠溺。
大概是骤然听到妈妈说国语,她惊奇的“咦”了一声,然后顺着她妈妈的目光看过去,这才看见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