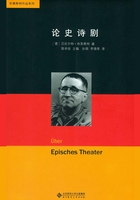他是卫生委员,也算个官儿,他就这样闯进我的生活。
我住的这个居委会,是在县城墙外推开淤积的沙土,新建起的居民新村。城外无庇护,风疾沙大,由于还在搞基建,到处乱七八糟的。
那是我刚搬进新居的第二天。刚起床,“各家各户,打扫卫生喽———”沙哑的声音从远处传来,不大工夫,门外就响起了“刷刷刷”的扫帚的扭动声。
我打开院门,在薄薄缭绕的尘雾里,挥动扫帚打扫我门前的竟是一位两鬓花白的长者。已是深秋,凉风习习,老人灰色的衬衣上只套着一件毛背心。
他看见我,停住手,一手拖着扫把,一手叉着腰。见他眸子一亮,皱巴巴的嘴角翘了翘,清癯的长脸掠过一丝笑意:“噢!刚搬来的?我们这条街又添人口了。我是这里的卫生委员,咱们这条街,你们这一来,就500单8户了。搞卫生,咱们也来责任制,房前屋后,分片包干。刚搞完基建,看这烂砖碎瓦的不少,得辛苦一点。再说,住在头上,麻烦事就多一点。我看……”他耸了耸稀疏的眉峰,用食指叩了几下头发花白的脑袋,“你就给咱们当个卫生小组长吧。”
他走了,临走对我笑了笑,又去招呼前面三三两两持揪抡扫帚的人去了,招呼声中夹杂着一些不大文雅的絮叨。
我望着他的背影,心想这种人拿着退休金不安心颐养天年,为了5元钱的津贴,忙乎个啥劲!
隔了几天,早晨6点半,又是那沙哑的吆喝。
今天安排定的,无论是“门前雪”还是“瓦上霜“都该我的那个对门,一个和我一样刚成家的小刘了。我这样想着,翻了个身又迷糊起来。
“嘭!嘭嘭!”大清早的,何人造访?“咣啷!”院门推开了,是他。
“王同志,打扫卫生了!”本地腔很冲,他停在敞开的屋门外,拄着扫把,目光愠怒,脸显得更长,多少有点质问的滋味。
我有点火了,可是面对一个长者……我冷冷地盯了他一眼:“今天不该我!”
卫生委员的脸煞白了,拄着扫把的手臂微微颤动,嘴唇上下翕动。突然,他一个回转身,踉踉跄跄地走出院门,院门外很快响起“刷刷”的扫动声。
7点半钟,我推着自行车走出院门。划给我和小刘的卫生区都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卫生委员正弯腰用铁簸箕撮垃圾呢!晨光里,那颗头发花白的脑袋升腾着袅袅热气。
他转回身,瞪了我一眼。我等待他发雷霆,他却“哈哈哈”地笑了:“还愣着干啥?赶快上班去!”
一种很复杂的感情驱使我打听这位小县城四居委卫生委员的根底,很快就打听到了:一个离休干部,“三八式”的,月薪的零头比我的工资还多呢,离休前是个什么长,谁知这老爷子有了官瘾,非要大小负个责。不知哪个狭促鬼能想得出,放在我们四居委当了个“卫生委员”!要说官哪,比弼马瘟还不知小几品呢!
又过了两天,早晨7点半,又是那沙哑的吆喝声。
我提起扫帚,赶快走出院门。不远处,卫生委员挺直脖颈在吆喝,活像一只啼鸣报晓的老公鸡。
“咣啷!”对门开了,我的邻居小刘也捏着扫帚。他朝着我歉疚地笑了笑,我对着他歉疚地笑了笑,两人不约而同地抡起了扫把。
他来了,站在不远处。这天早晨他情绪特别好,变得健谈了。他对我们说,当个卫生委员还真得费点难,原来不想干了,可现在他倒是真想干下去。他说:“立冬之前,咱们先在你们房背后建个垃圾集中站,你给咱们当站长。”他指了指小刘,又指了指我,“你给咱们办橱窗,我掏腰包,宣传讲卫生,介绍点科学吆!怎么样?”话虽是征询性的,听起来却像指令一样。我俩相视而笑,他也笑了。打那以后,每逢三、五、七,不等我们的卫生委员吆喝,我和小刘,我们这条长街众多的邻里,就已经都抡开了扫把。
每次评比,我们这条街都是小县城“最清洁”的一条街。
作者简介 尚怀强,男,汉族,1952年生于宁夏盐池县大水坑镇。1968年初中毕业。1970年参军。1973年复员后被推荐到陕西机械学院铸造专业学习,1976年毕业。曾在盐池县农机修造厂、红井子公社工作。1985年调盐池县乡镇企业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