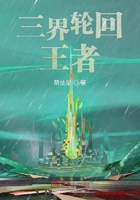漫长的一夜终于过去,东方天际隐隐有了些鱼肚白,远处村落清晰地传来几声鸡鸣。
白无极,不,应该是柳无极才对,他抖了抖身上的露珠,只觉得这春末的黎明竟比腊冬还要寒冷,丝丝的冷风直吹向他内心深处,仿佛连他的血液也在这寒冷的清晨有些凝固。
身后的白疤不知何时已经离开了,无极只记得在茫然间听得白疤让他早些回去,还要他当今晚的事情什么都没有发生,等到时机成熟和他一起报仇雪恨。
可是,这一切真的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么?
那个害死父亲的男人,那个令母亲痛苦一生的男人,为什么对自己这般的好?
再次面对,又该如何相处?
没有回答。
蛇女一双微红的眼睛仍然盯在柳无极身上,这一夜的所有事也都大大的超出蛇女的想象,她忽然觉得这个俊朗的少年是这般的可怜,心里竟隐隐有种说不出的难受感。
原来不受伤真的也会难受。
蛇女虽在毒障渊深水潭下孤身修炼千年,却自幼便没有见过父母,也不懂那亲情的可贵,故而孤身一人却也不感寂寞,无欲无求,只一心求道,可是此刻,她竟吃惊地发现自己能够体会到那种痛失亲人的感受。
谁也没有注意,吊坠内空间的墙壁上的符号在今夜不停地暗淡,到得此时,已隐隐有些模糊了。
柳无极拿捏着胸前的吊坠,呆呆地看着这个母亲临终前戴在自己脖子上的柳家的遗物,只觉得大脑中一片空白。
原来娘说的一直是……
若有若无的一声叹息飘在了柳无极的耳根,柳无极瞬间回过神来,环顾四周,却看不到任何人影,随即自嘲了一下,自己居然出现幻觉了。
他盯着那个翡翠吊坠,只觉得这个世界是如此的陌生,自己是如此的孤独,轻轻的张口,似乎是在向吊坠询问,又像在冥冥中说给谁听:“我该何去何从?”
火红的太阳缓缓从东方升起,天色渐亮。柳家村陆续有村民走出,或去砍柴,或去打猎,每一个经过柳无极的村民都投去好奇的眼光,不懂这看上去只有十来岁的少年为何独自跪在村头,看他面容憔悴,眼圈发黑,不难看出此少年一宿未睡。
不知何时,这少年身后的村民开始三三两两的围了过来,在身后指指点点,似乎在互相询问这少年是谁?又为何大清早的跪在这里?
不住的有人出生询问,“孩子,你是不是迷路了?”“孩子,你是哪儿的人啊?为什么大清早的跪在这里?”那少年却充耳不闻,只是自顾自的发着呆。
只有一些年岁稍大的人,望着这个跪在那个孤坟下的孩子愣愣出神,只觉得这孩子眉清目秀,似乎在哪里见过一般,甚是熟悉。
※※※
赵心兰的死已有一段时日,白马帮本是山贼,素来不信鬼神之事,对于习俗葬礼之类皆是一切从简,故而白猛虽对赵心兰痴心一片,却也只是草草埋葬了事,只是心兰下葬当日自己的儿子无极却不知在哪里,竟没有出现,着实令他气恼,同时也有些疑惑。
无极平日里虽有些调皮,可他与母亲赵心兰感情极深,远远胜过自己这个父亲,却为何在他母亲下葬这天也不露面,甚至找遍了白马山都看不到他的身影。只是白猛虽有些气恼,却也未曾多想,只道是无极他孩子心性,可能看到了什么好玩的事物一时流连忘返吧。他倒是丝毫不曾怀疑无极会偷偷下山,一来无极从未出过山头,二来他并不知无极会武,故而也未曾担心。
只是过了这好些日子,无极还是未曾在眼前出现,白猛这才惊醒,急忙派人满山搜寻,甚至连山下附近的村落都寻了好几遍,却还是不见无极的踪影。
白猛连日里痛失妻子,心中压抑无比,每日里抱着酒坛在后山一人饮酒醉。一帮手下知道近日里白猛脾气暴躁,一点就着,竟也无人敢上前相劝。
唯有白林来过后山两次,劝他节哀,只道无极聪明伶俐一定不会出事,可惜白猛仍是自顾自地饮酒,白林的话却不知是听到还是没有听到。
看着白猛满脸的胡渣,白林摇了摇头,随即犹豫了一会儿,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坐在白猛身旁,叹了口气道:“大哥你又何苦如此?”
天色忽的有些阴沉,初夏的天果然多变,刚才还是晴空万里,现在却布满了乌云,整个白马山也变得阴森森的。
白林深深的吸了口气,道:“大哥,有件事我不知当不当讲,只是或许和无极的失踪有关。”
白猛抱着酒坛的手忽的停顿了一下,却依然没有回应。
白林皱了皱眉头,紧紧盯着白猛的双眼道:“其实、其实大嫂她嫁到我们白马帮的时候,已经、已经有了身孕。”
倘若白猛此刻腾地站起,或是甩掉酒坛问他什么,他都不会惊讶,可白猛除了身子抖了一下之外,一双呆滞的眼睛依然看向前方,没有任何的反应,只是又接着举起酒坛往嘴里猛地灌了好大一口烈酒,也不知道刚才的话他有没有听到。
或许他听到了,又或许他没有听到,或许他听到了却装作没听到,又或许……
白林继续道:“当日我替大嫂把脉之时便已断定她已有两个月的身孕,只是看大哥对她如此用心,又因过去无意中看破大哥命数,注定此生无后,便想着将此事瞒下去,一来大哥高兴,二来孩子终生也未必能知自己身世,只将大哥当做亲生父亲对待岂不也是一桩美事?可现在看来,很有可能赵心兰在死之前将无极的身世告诉了他。“
言未罢,白林似是想到了什么,恨恨地道:“这也都怪那个懦弱的王婆子,倘若她真听了我的话在接生完之后便顺手将那个女人害死,又岂会这么多事?”
“轰隆”一声,滚滚雷声在头顶上方传荡开来,在这之前,一道刺眼的闪电撕开了片刻黑沉沉的乌云。转瞬间,豆大的雨点断断续续的落下,啪啪地砸在白猛和白林的头上,衣上。
白林站起身来拉了拉仍自发呆的白猛,道:“大哥,下雨了,我们回去吧。”
白猛却毫不动弹,任那豆大的雨点肆无忌惮地在头顶砸落。
白林武功平平,自然拉不动这个高它半头的壮汉,此刻任他计谋过人,终究还是束手无策。
又是一道闪电划过,哗啦啦的大雨滂沱而至,暴雨竟来得如此之快,只是片刻,白猛白林二人的衣衫已尽数湿透,紧紧地贴在身上。
只是白猛依然没有离去,仰头望天,任那瓢泼大雨击打着他沧桑的面容,雨水沿着下巴滴落,却不知同样滴落的有没有咸咸的泪水。
白林大声地喊着:“大哥,那不是你的亲生儿子,那个女人也不过是我们抢上山来的,你又何苦如此啊!我们曾经多少次在生死边缘挣扎,可最后不还是闯过去了?没了那个女人和那个野种,你还有我们这帮兄弟啊!”
雷声阵阵,瞬间淹没了白林的嘶喊。
※※※
丹阳城
一个头发凌乱,满身泥垢,胸前挂着一个与这身行头完全不搭配的翡翠吊坠的少年,独自一人垂着头走在繁华的大街上,周围人来人往,他的心却是如此孤独。
柳无极已经记不清有几日不曾吃饭了,全身无力,走起路来都有些不稳,仿佛下一刻就要跌倒。天空忽然阴云密布,眼看着就要下雨了,街上的行人纷纷加快速度赶路,道旁的店铺也陆续地关上了店门。
只是一会儿工夫,伴着刺眼的闪电和震耳的雷鸣,倾盆大雨如约而至。
街道上只剩下了一个朦胧的身影,在大雨中是如此的孤单。
是什么,掏空了顽劣的心脏?
是什么,冷却了沸腾的血液?
柳无极蹲坐在一处阴暗的墙角,任凭大雨洒落在自己的头上、肩上,却没有一丝知觉,他已经实在没有力气继续走下去了。
风雨交夹中,街道的尽头隐隐有马蹄声传来,只是眨眼间,一辆华丽的马拉轿车从无极眼前奔过,然而那马车上的主人似乎也注意到了这个蹲在墙角的少年,在前方不远处缓缓停下。
风雨中柳无极的视线有些模糊,加上饥饿难耐,眼皮不争气的异常沉重,缓缓的闭上了双眼,只听得凌乱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转眼到了跟前。
落在身上的雨滴突然间少了许多,恍惚间,只听得一个清脆悦耳的声音轻轻地道:“好可怜的小乞丐啊。娘,这么大的雨,我们帮帮他吧。”
仿佛春季午后轻轻的暖风,这声音带着几许善良、几许温柔,悠悠地传入了柳无极的耳中。
仿佛那掏空了的心脏也瞬间重新焕发了点点生机。
仿佛那冷却的血液也重新有了丝丝温度。
这个无人相识的城镇,这个大雨滂沱的街道,竟然也有人关心自己么?
柳无极极力地想要睁开双眼,却实在力不从心,不知不觉中竟沉沉睡了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