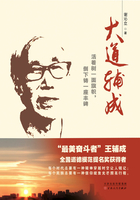任绍礼领了几个任家的族人,到后园里去见了任文锦,对任文锦说祠堂被火烧了,我们也不采取个什么办法,或者说把祠堂再修起来。”
任文锦说:“祠堂的火刚灭了,大家都有很多种说法,让大家说说、议议,现在先都忙着抢种秋粮去。议论上一段时间了,肯定会有定论的,现时说有点太早。”任绍礼听着这话也对,就笑了笑,和几个族人出了后园,任文锦直把他们送出了园门口。
且说,四月八的文殊山上,虽昼夜刮了三天狂风,风过后,下了两天的雨,把山川、树木、庙宇又洗刷得干干净净了。住在山上的游人们还有成群结队的小商贩们、过路商客,也和去年一样,拥挤在东西峡谷口内。四月十三日,文殊山庙会达到了高峰,也是游人最多的一天,突然文殊山进口处开进去了四辆大汽车,前两个车拉着正规部队,后两个车是朱发生的民团兵,他们一下子包围了文殊山的几个重要通道。游人们慌乱起来了,一个军官站在九棵松的那个位置上,朝天打了几枪。九棵松下的那位军官大声讲道我们是来招募兵丁的,自愿者请在山下这一块空地上就座,如有不规者,打死无须偿命。”讲完,又打了几枪,几个通道上也跟着又放了几枪。随即,朱发生的民团兵就开始抓丁了。
这些民团兵,除背有大枪外,还每人手拿一个榆木棍头,就像放了笼的饿狼猛虎一样,见年轻小伙子,乖者还罢了,不乖者当头一棒,打得鲜血淋漓、晕头转向。不大一会儿工夫,就在九棵松下的平地上,抓坐了几十个,随即发了衣服,换穿在身上,又把换下来的衣服丢在火里烧了,抓够一车,就拉着进了城,圈在校场兵营里。这一天,共抓了二百多人。
这佛地抓兵,也是一绝招,本是游山逛庙的人,突然失去了丈夫、儿子,或者是自己的哥哥、弟弟,怎能不痛心呢。悲天惨地哭爹喊竭的、呼儿找女的,部队一撤,游人们哭声震天,像蝼蚁一样涌下山去,当地老百姓把这次抓兵称为“朝佛圈丁”。有个和尚据说是个过路游僧,名叫广纳,他对文殊山发生的“朝佛圈丁”非常不满,故把身上穿的袈裟,撕了二十块,写了二十个字,挂在了九棵松上,这二十个字是:乐不乐,朝佛圈丁上山崖悲不悲,捶胸泣血下泽。
十几天后,朱发生去任家庄找过任文锦,见面就说:“我的任大哥,你这次吃了张家牛娃子的亏了吧,人家抢了你的祠堂,又一把火烧了个干净,不知哪个土匪把你们任家族人杀了一个,移尸祠堂旧址上,代替牛娃子的罪名,可笑、可笑。天下竟有这等事,有朝一日我逮住张牛娃子,非要问个明白。”
任文锦听了,只是笑笑。还和以前一样,大酒大肉地招待了朱发生,称兄道弟地说了许多知心话,又问朱发生你最近没有未余香院里听曲子?”
朱发生神秘兮兮地说:“去了,一有空就去,每次去还要领我那大醋坛子,她现在听上瘾了,我不去时,她还邀着我去,从领头的丘雅鸳、杨春儿,到末尾的黄丹丹、薛玫瑰我们都听过。她们唱的《黄氏女》,还把我老婆唱哭了。”朱发生不像前一次来那样垂头丧气,这回是春风满面。
朱发生走后,任文锦笑着对张明月、张玉亮说:“我的这个朱兄弟,真是小人得势,还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说完,任文锦嘿嘿地笑了几声儿。
苍蝇头儿大的麦穗子,过早的有了白黄色,这是四月八狂风过后补种的庄稼,这麦苗儿为了赶季节,到底人了米儿,多则六七个籽儿,少则一两个籽儿,这样的麦穗儿肯定是打不出粮食的。市场上的麦子、面粉、小米、大米,都以翻一翻的茬儿长价了,大饼、面条的价长得使人眨眼。任文锦立在庄门外的麦地埂上,眼里看着麦穗头儿,心里想着自己的三个甜水面馆子,是长价继续干下去,还是关门停业。更有个难题儿说不出口,那就是文殊山僧道的吃粮问题,清远大师提早付了四年的粮钱,都是按最低的价付的,现时,土地已卖去了三分之二,剩余的三分之一的地庄稼又受7灾,还有整个大面积的歉收,粮价更要上涨。他佩服郎作仁,去年一粒粮未出,全部压进了新仓房,去年的一斗麦三元九角,今年翻一翻也挡不住,他更佩服文殊山的清远大师’他竟能料到今年有灾,提早付了我四年的粮款。想到这里,他先下了一条定律:不管灾难多大,赔多赔少,文殊山清远大师的斋粮一点也不能少,该什么时候送粮,一定要按时送上山去。清远大师他即知前,也该知道后事怎么做。他又摆弄了一会儿麦穗儿,起身进了任家庄。
他去了账房车姨子那儿,对车姨子说:“玉门矿来拉面时,面价按当前市场价销售,把那点库存的面粉售掉后,水磨暂停一段时间,仓房里的粮食也暂停往水磨上运送。东仓房有几十石陈年谷子,碾成米销点算了,其他粮食都紧缩点。”
车姨子说玉门前天来拉了三车面,我巳将面粉按市面价涨上去了、拉面的那位管家也知道面粉要涨价的,来时,就按涨价的面粉款拿上了。”任文锦点了头,车姨子又说:“最近这几天,佃户们多来探口气,受了灾了,能不能减点租子,让我在大老爷面前讨个情儿。”
任文锦笑了一下说今年佃地的户下也不多,你给佃户们说让他们多在地上下下工夫,能多收回一粒粮就多收回点,减租子的事,到年底了再说。”车姨子应了声儿,任文锦起身走出账房。
回到屋里刚坐定,就见冬梅来了,进门就笑着说:“爹、大妈、妈,你们可知道我为什么事急急地来了?”
任文锦笑道是为甜水面馆卖价的事吧。”
郭冬梅笑道:“不是,你们谁也想不到,我是报喜讯儿来的,谁能想到是卡査西回来了,他开着一辆俄罗斯大卡车,说是来还钱卖汽车的。”
任文锦听了忙问:“他的汽车给谁家卖?”
冬梅说:“卡査西说如果任大老爷要汽车,他就卖给任大老爷,如果任大老爷不要,他就往别处卖去。”
任文锦高兴地说:“看看,还发愁买不上汽车呢,这不是送到家来了,你见汽车了没有,是新车还是旧车?”
郭冬梅说今天天刚亮时,他开着汽车来了,首先开到了汽车修理厂。他又去医院找我,说他饿得慌。我先请他在饭馆里吃了一饱,才去了汽修厂。班师傅开车转了一圈,杨超也上去开着转了转,下车后,班师傅对我说车是新的,如果大老爷要买,他和卡查西讲价钱。”
任文锦忙起身说:“那我进城去把这辆汽车买下。”又问郭冬梅:“卡査西没去找普利敦耶夫?”
冬梅笑笑说:“我问了卡査西,去不去认认他的长辈?卡查西说:“我那长辈不受抬举,我出走前问他借一万元去赎汽车,他说什么也不肯,我只好从银行直取了两万元走了。不管怎么说,这两万元我是要还他的,只是他心眼太小,我见他也可以,不见他也行。”任文锦听着笑了。
任文锦穿上了出门的衣服,郭冬梅却又问道:“现在该说说甜水面馆的卖价了。其他家饭馆面食都涨了价,我们的没有涨,三个面馆排着长龙吃饭,有提麦草的、树木丫杈的、牛粪块子的,大多数的顾客是拿这些物件换着吃饭的,收的柴草粪块都没处盛了。”
任文锦等冬梅说完了话,望着郭冬梅说:“再撑三天后涨价。”说完,郭冬梅骑着自行车头里走了,任文锦、张明月、张玉亮随后坐车进了城。
中午时分,任文锦把卡查西请进了南局饭馆,同时在座的还有班子恭、娜塔莎、杨超、冬梅等,任文锦想把普利敦耶夫也请过来,卡查西说:“不用请他了,请他来反而多事,等我把汽车卖了,我自然会去看他的。”任文锦就没再坚持去请普利敦耶夫。这当儿,娜塔莎说了她被劫持的事,卡查西骂普利敦耶夫是个坏头儿,他把钱看得比命还重。
饭前,先谈卖车手续及车的标价,卡查西出口就是六万元。班子恭不慌不忙地说了汽车的几处毛病,又由娜塔莎翻译给了卡查西。卡查西一听,知是遇上了懂车的行家,虽是新车,却有不足之处,自己先杀了两千元的价,双方讨价还价,在五万五千元上成交了。酒饭后,卡查西说了几句感谢的话,方说到那两万元的事。任文锦说:“你突然走了后,普利敦耶夫就胡赖起来,我们担了一万元,他担了一万元,我当时还说,卡查西不是那样一走了之的人,他肯定会回来的,果然,应到了我的话上。”
卡查西说:“谢谢任大老爷相信我,那你就给我付三万五千元,那两万元作为欠账还于你们,麻烦你再把一万元还于普利敦耶夫,我再三想过了,还是不见他的好。”任文锦点了下头。
就在这天下午,郭冬梅在银行给卡査西办了汇款单。临走时,卡查西对任文锦说:“你可算是一个正直的中国人,今日一别,以后还有相会的时候,我的车上还带有一卷俄罗斯呢子,就送于你做几件衣服穿穿。”说着话,和任文锦握了手。最后,他抓住郭冬梅的手亲了几下,说道郭经理给我的印象最好,我如果娶上像你这样的中国女人,我做梦都会心满意足的。”郭冬梅有点不好意思,但抽不出手来,只好由着卡査西多亲了几下,在场的人都笑了。
卡査西走了三四天后,普利敦耶夫才知道了这信儿,责问任文锦为什么不让卡査西去见他。任文锦笑道:“话不能这样讲,我让他去见你他不去,要论起亲疏来,你对他更亲些,卡査西不到你那里去,我不能拉着卡査西去见你吧。好了,两万元还回来了,你一万,我一万,见与不见也无所谓了。”普利敦耶夫只好点点头,说不出什么话来。
一个星期过后,任文锦买下的俄罗斯汽车就由杨超开着在大街上行驶了。杨超的耳朵被蒲珠撕了几次,一再交代:“你的命和汽车都是最值钱的,你要小心,听懂我的话了没有?”
杨超诺连声:“听懂了、听懂了。”自此,肃州城里有了第一家私人汽车。
包康里斯基、劳斯顿托夫两人要和桑塔莎妮娅,叶利琴娃两人结婚了,他们托郭冬梅找房子。郭冬梅也动了下脑子,把包康利斯基和桑塔莎妮娅的房子找到了南街上,把劳斯顿托夫和叶利琴娃的房子找在了北街上,她想着分开点住好,免得闹出是非来,影响医院的工作。为这事,她找人打扫粉刷了房子,包康利斯基和劳斯顿托夫高兴地说了许多感谢的话。他们按照俄罗斯人的风俗布置了房间,结婚那天,汽车派上用场了,新郎、新娘坐在驾驶室里,客人们坐在车上面,汽车披红挂绿的,来回在大街上跑了好几趟。街上人来人往的,议论着这件事,为肃州的青年男女用汽车结婚开了个先例。
郭冬梅专为两对新人在南局大酒店办了俄罗斯传统菜肴,那边,普利敦耶夫夫妇及在肃州的俄罗斯同乡参加了婚礼这边,任文锦、张明月、张玉亮、青山、婕芙娜等都参加了两对新人的婚礼。普利敦耶夫的夫人亚西妮规娜自发生了劫持娜塔莎的那件事后,见了任文锦、张明月、张玉亮等人总觉有点不好意思,不敢用正眼看别人,见了娜塔莎就更不用细说了。
婚后,两对新人说:“我们在异国他乡举办婚礼,不比在我们国内差。”他们专去谢了任文锦、张明月、张玉亮及郭冬梅。
任文锦只是客气地笑了笑,郭冬梅却说了几句结实话:“用我们中国人的一句成语说,让你们乐不思蜀,好施展你们的医术才华,为肃州人民祛病除灾。”也许是有了一个幸福的家庭,包康利斯基和劳斯顿托夫两人,确实精心工作,这是后话,暂不提。
夏收了,农民们望着地里稀疏的小黄麦穗儿,流着眼泪,抹一把泪,长出一口气儿,哀叹几声。任文锦和谭璋也在自家的地埂上转着,碰上流眼泪的乡民就说:“光流泪起不了作用,赶快把麦收了,种点晚秋作物补补歉收。多挖点大白菜,多种点冬萝卜,掏个大菜窖藏起来。虽是菜头萝卜,有了总比没有的强。没粮吃了吃点菜,起码饿不死人。”
任文锦话虽这么说,自己心里也难受,古人讲民以食为天,一没了粮食,人心都慌了。他和谭璋转了一大圈后,一指谭璋面前的一大片地说这几十畦子地全种大白菜,南边那几十畦子地全种冬萝卜。比去年要多种一半以上,保证玉门油矿拉的外,还要足够自家人吃的,为了早种几天,每日吃过晚饭了再加班干一阵。晚上再吃一顿腰食,适当时杀两只羊给大家解解馋。”
谭璋说有大老爷的这句话,我们拼着命干几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