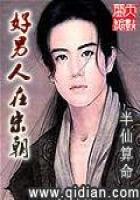巴尔扎克(1799~1850),出生于法国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家庭。1819年毕业于巴黎大学法律专业,随后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同年,巴尔扎克决定放弃法律,改行搞文学。1829年,他写出了自已的第一部成功的小说《最后的朱安党》,从此登上了法国文坛。由于工作过于劳累,他只活了50岁,1850年于巴黎寓所去世,而几个月前,他刚结婚。
巴尔扎克是十九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大师。他一生创作了九十余部长、中、短篇小说。他试图用这些小说真实地表现十九世纪法国的社会风貌,因而他把它们统称为“人间喜剧”。巴尔扎克的代表性作品有《高老头》、《幻灭》、《欧也妮·葛朗台》、《贝姨》等。
异常艰难的起步
巴尔扎克出生在1799年的5月21日。他虽是五十多岁的父亲的头生子,但他的出生没有引起父母亲多大的欢乐。他像一个患麻疯病的人一样,还没有满月,就被母亲交给了一个乳母。父母虽有宽阔的住宅,但是他们却不让他回家。每周只有星期天才让他回来一次。他没有玩具,没有接受过任何礼物,甚至生病的时候他也没有得到过母亲的照顾。母亲对他从来没有用过慈爱的字眼,没有过亲昵(nì)亲昵:十分亲密。的举动,甚至当他偶尔想在母亲的膝头挨近想拥抱母亲、得到母亲一点爱抚的时候,得到的常常是一声声严厉的呵叱(chì)。
巴尔扎克童年的真正悲惨是在学校里的生活。七岁时,他就被送进了王多姆的一所寄宿学校——欧瑞多教会学校。那是一所扼杀儿童身心的监狱。在那里,他生活了整整六年。
从开学的那一天起,他们就接受着严酷的苦修生活的训练。在那里,没有假日。父母只准许在特殊的情况下才能看望孩子。而据巴尔扎克的父母的情况来看,很可能在特殊情况下也不太会来看望他们的大儿子的。于是小巴尔扎克除了忍受学校严酷(kù)的制度外,还要忍受被家人抛弃的痛苦。这对于一个需要关心和爱抚的孩子来说,无异于是一种精神和肉体的扼杀。他没有手套和暖和的内衣,他的手指常常是冻裂的,脚上生着冻疮(chuānɡ)。
他所在的学校每年都要将学生分一次班,按学习成绩分到优、良、中、劣四个班去,巴尔扎克每次都很自然地进入第四等级,原因很简单,他的成绩很差。
巴尔扎克在学校里是坏学生,经常因为不认真学习而被关禁闭。自从入学开始,他蹲(dūn)小黑屋的时间越来越长。后来据学校的校长和校工们回忆,他一星期总要被关上三四天禁闭。久而久之,巴尔扎克习惯了,他在小黑屋里胡思乱想,这培养了他的想像力。
十二三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为他找到了一位补习数学的老师,因为他的数学成绩实在是太需要补习了。这位老师是一位工艺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是巴尔扎克遇到的第一位好老师。他除了帮助巴尔扎克补习数学外,还利用自己的方便条件给巴尔扎克借来了大量的图书,作为小巴尔扎克学好数学的条件。谁知他的许诺(nuò)一出,便给自己找来了无穷的麻烦:这位学生读书的胃口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无论给他带来多少书,都不够他看的,他就不得不经常去更换那些书。这就使小小的巴尔扎克得到了一个最最有力的思想和生活的救星,它们把他引入一个惟一真实的世界。各式各样的书他都读,如神学、历史、哲学、科学……他用它们来充实自己饥饿的精神。用这些书中的知识、故事、常识减轻着、抑(yì)制着学校生活的种种屈辱和痛苦。在那里,他找到了一片广阔无垠(yín)、美妙无比的天地。在那里,他忘掉了父母的冷漠、教师的严厉、同学的讪(shàn)笑讪笑:讥笑。。在那里,他找到了一片“极乐世界”,找到了一个真正惟一的归宿。
他有极强的阅读能力。不说一目十行吧,也可以做到一目七八行。他的思想,能极其敏捷地配合着眼睛的速度。眼睛扫向哪里,思想也跟到了哪里,能迅速而准确地抓住眼睛所能见到的每一个文字的意义。他的阅读方法也是极其聪明的,对于有的书,他并不一字一句地读,而常常是只抓住一两个单词就领悟(wù)了全句的意义。
他的记忆力也是惊人的好。他不仅能够快速地阅读后记住所读的内容,而且能够记住重要的语言和意义。对于书中所写的地域、人物的姓名、相貌、言谈、举止以及书中的情节、细节和这些东西在他头脑中产生的形象、感觉、色彩、姿态,他都能一一记住。他不仅能记住它们,而且还能够用他的内心,把它们一一呈现在眼前。他不仅有极好的记忆力,而且有一种惊人的再现这些记忆的本领。他能够把进入他心灵的第一个思想到进入他心灵的最后一个意念统统抓住。他的脑子,早年就习惯于这种能够把人类力量集中起来的复杂的劳动。
他还有特别发达的想像力。十二岁的时候,他的想像力,由于不断运用的刺激,已发展到一个顶点,使他把那些仅从书本上所得到的事物的概念,拟构得如此之真切,以至于那些事物的影象呈现在他心中,即使他在事实上真看见了它们,也不会更显得清楚。在他读到奥斯特里兹(zī)战役的描写时,他能看见战场上发生的每一件事,能听到连珠的炮声和战士们的呐喊声、马蹄(tí)的疾驰声和士兵们的各种声音,能闻到火药的气味,能看到两国的士兵在原野上酣(hān)战的情景。当他在读书的时候,他好像失去了肉体的知觉,“只凭了他的智慧在活着。”这种感觉逐渐扩大,最后竟至到了遗世忘我的程度。
他的记忆力和想像力,有时也给他带去一些麻烦。因为他记忆力强,有些书他就不去死记硬背,甚至于念也不念,只凭课堂上老师提问时同学的回答就能把功课记住。这样,他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想像他内心的故事。可是,有时老师把提问的秩序颠倒了,让他先回答问题,这样他就傻眼了。结果当然可想而知,不是一顿呵叱(chì)就是一顿处罚。
欧瑞多教会学校的不堪忍受的奴化教育,严重地影响了少年巴尔扎克的身心健康。六年以后,他以一个少年精神病患者的名义离开了这所学校。这时——十四岁的时候,他才算第一次回到了他父母的家中。在这以前,他只可能偶尔被父母去探视一下,或者偶尔回父母家中住上一两天。可以想见,一个长期离开父母的孩子,这时该有多么快乐。可是,六年的僧(sēnɡ)院式、奴隶般的生活,已使一个圆乎乎的胖孩子变成了一个瘦弱不堪的小瘦猴。而且由于长期的精神紧张,他已失去了对欢乐的感觉。当然,这个家庭,其实对他也没有什么欢乐可言。他常常恐怖地睁着一双大眼,行动就像一个犯着梦呓(yì)症的病人,眼里常常露出茫然的凝视的眼光,昏昏懵懵(měnɡ)地坐在那里,甚至人家和他说话,他也听不见。外表虽然这样,但他的内心世界仍然是丰富的。他把这种内心的丰富看作是自己的一笔财富。也许是这内心的自信吧,不久,他就摆脱了精神的抑(yì)郁,成了一个健康的孩子,不仅愉快,而且健谈了起来。这样,父母又把他送进了杜尔的一所中学。开始是走读,不久,当他父母搬家到巴黎后,他就进了黎华德先生的一所学校,又过上了寄宿的生活。仍然是得不到关心和爱护,仍然是被摒(bìnɡ)逐和被弃绝,仍然是得不到父母的爱心。不过,他终于中学毕业了。而且在1816年11月4日,他考入了一所大学,成了这所大学法律系的一个学生。这是一个代表了他奴役(yì)期满的日子,是一个透出了自由曙(shǔ)光的日子。他将可以获得自由,自由地攻读他所热衷(zhōnɡ)的书籍,自由地从事他所热爱的事业。
大学毕业后,他在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
在事务所里,巴尔扎克总是将活计积累成一大堆,然后才伏下身去一下子干完。空余时间干什么呢?侃(kǎn)大山。以致于主管先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sù)”,毕竟他不想为一个巴尔扎克而失去三个雇(ɡù)员,用他的话说:“巴尔扎克一到,就等于我这里少了三个学徒干活。大伙的注意力都被他吸引开了!”
一天早上,巴尔扎克正待出门到律师事务所去,忽然有一个小厮(sī)送来一张主管先生给他的字条。展开一看,巴尔扎克笑了,上面写着:“鉴于今日事情甚多,所以巴尔扎克先生不必光临。”巴尔扎克被炒了鱿(yóu)鱼,只好又换一个地方了。
1819年4月10日,巴尔扎克像一个疯子似地跑回家,对父亲宣称他要做“文坛(tán)国王”。
父母以为儿子疯了。可他的神情那样地庄重严肃,一副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架势,又不像头脑出了问题。老巴尔扎克夫妇只好从震惊中回过神来,鼓动起全家,调动各种力量给小巴尔扎克洗脑。
但是怎样劝说都不行,儿子就是不愿再做有肥厚利润的律师工作了。巴尔扎克夫人还要再劝,她丈夫显得不耐烦了,他对家人咕哝了一句:“为什么就不行呢?”是啊,为什么就不行呢?他老巴尔扎克没进过学堂不也家财万贯家财万贯:家庭的钱财、家产很多,很值钱。了吗?
老巴尔扎克的妥协动摇了巴尔扎克夫人的决心。经过一番思考,她决定改变自己的策略,直接进攻不行就迂(yū)回包抄,让巴尔扎克身处困境,最终自己乖乖地投降。经过夫妻二人的密谋磋(cuō)商,他们终于同意了巴尔扎克的请求。一场耗(hào)时5个月的较量结束了。
但同意是有条件的,条件就是要签一纸合同。这个合同规定:家庭给巴尔扎克提供两年时间去测试、展现他的创作天才,两年之中其生活费由家庭供给;如果两年之中丝毫不见巴尔扎克文学天才的火花,那么两年后他必须老老实实回到律师事务所的凳子上,去为巴尔扎克家族做个好公证人。
这个奇怪的合同可以说是巴尔扎克一生中的第一个合同。
为了表现母亲对儿子的“关心”,巴尔扎克夫人亲自领着儿子到巴黎去挑选住所。她终于找到了,原来是位于五层楼顶的一个黑暗的充满怪味的亭子间。屋顶差一点就要斜压在地板上,穿过瓦缝,可以清楚地看到外边的天空。尽管房东太太只象征性地收取租(zū)金——每月五个法郎,也没有任何人愿意住在这种洞里。
但是,儿子毅然地走进了这座破旧的楼房、爬上了那破旧的楼梯,住进了那间破旧的楼顶小屋。
从此,这个青年人就蛰(zhé)居在了这间简陋的破屋里,成了这里的一名隐士。
他以愉悦的心情欣赏着他的楼顶小屋,这是他的住所,是他的空间。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它也将为他提供出一切所希冀(jì)的东西——创作出成功的作品。顶楼小屋有一个窄小的窗口,这是巴尔扎克与外界相通的孔道。从这里,他能放眼远眺(tiào)。
现在,摆在巴尔扎克面前的一个首要问题是写什么。他还没有完全选择好自己的道路:是当哲(zhé)学家呢,还是当诗人?当小说家,还是当科学家?他还在举棋不定。他的兴趣太广泛了,看的书也太多了。这使得他一时还不知道朝哪一方面去发挥自己的才能。但是,要写,要写出有名的作品,这是他雷打不动的目标。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在他正式的写作生涯(yá)开始的时候,他用了大部分精力去学习,学习别人的技巧,同时也寻找自己的题目。在这一段日子里,他除了研究与发展自己的风格外,什么也没有做。他把研究和发展自己的风格,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为了找到一个理想的题目,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经过了两个月的探索,他终于作出了决定,决定写一部关于古代帝王克伦威尔的诗体历史剧,取名叫《克伦威尔》。他计划用两年的时间去写作,然后进行修改。他的压力是很大的,一方面是对自己才能担心,一方面又为母亲给他限制的两年期限担心。
他的苦行开始了。他以着了魔的劲头去工作。他没日没夜地工作,常常是三四天不离开屋子。要出门也只是买一点生活的必需用品。他以那种不要命的劲头工作。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它并不因这个青年的苦斗而放慢一下脚步,也不因为他的紧张而为他多提供几个钟头。时间的流逝,倒是他最大的苦衷。他必须走在父母给他提供的两年时间之前完成这部作品。时间的紧逼,迫使他疯狂般地工作。他要不惜代价地把《克伦威尔》写完,而且要保证质量。这样,经过了四个月的苦干,在两年的期限刚过去一半的时候,他拿出了他的第一部作品的草稿。那是在1820年4月。
这个“不务正业”的儿子,终于忍饥挨寒地提前一年拿出了他的作品。这不得不使他的父母感动了。一个青年小伙子,踏踏实实地坐在写字台前,一个字一个字地写作,怎么也比那些到咖啡馆里胡混的青年好得多。何况,这么艰苦的环境、这么微薄的供应,他居然没有欠下一文钱的债。这对于把金钱看得极重的父母来说,也太让他们宽慰(wèi)了。父母的看法开始有了些转变。他们开始认识到,也许这孩子坚决要求干写作,是有他的道理的,并不是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懒惰(duò)与游手好闲。再说,如果写出来的剧本真能够上演,那对父母,对父系、母系的家族也不是没有光彩的呀。所以,对《克伦威尔》的完成,父母的态度是极为热忱的。母亲甚至还亲手帮他把草稿抄写了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