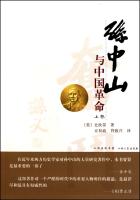这日,亭相颜来锦阁取衣。
二人又约在紫藤架饮茶。
他们兄弟之间的谈话,我无意打扰,便在亭外的杏林里等颜相亭。
风清日丽。
我躺在吊床上,粉白的花瓣随风荡下枝桠,携着怡人的馨香在我面上轻轻着陆。头顶树上花影纷繁,过滤掉阳光的刺眼,只剩下柔柔的暖意照在我脸上,舒服得令人想睡觉。
人生最惬意,不过醉花阴。
鼻尖花香萦绕,耳畔鸟啼婉转,清风徐徐拂面,吊床悠悠荡荡,我舒服地合上眼皮……
不知过了多久,我再次睁开眼。
眼前花影碎光全无,只有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
这是哪里?
又一个梦境吗?
我试着从脑后抽出枕麻的双手,双肘却戳到什么,一阵麻筋。试着曲膝,也碰到了硬物。身下也不再是柔软的吊床,而是一张硬板。
我小心地抽出双手,触摸四周,发现自己被人关进了一个箱子。
这箱子就像是为我量身定做,单单平躺着,并不感到束缚。但活动十分受限,连翻身都不行。
箱内空间封闭而逼仄,空气不流通,已经开始令我感到胸闷。
过不了多久,我便会被闷死在这里。
不行,我得想办法出去!
我敲了敲箱壁,发现是木制的,而且听声音板子不算太厚,兴许可用蛮力踹开。
时间每流逝一秒,我的胸闷便加重一分,呼吸也愈发困难,不能再拖了……
我深吸一口气,手脚同时发力,向上踹去。
“砰!”
头顶的木板应声裂开,一道光照了进来,却是黯哑的。
木板断裂时产生的碎木屑飘进眼里,微微刺痛。
无暇顾及眼内的不适,我三下五除二地扒开木板,急于呼吸新鲜空气。
我从箱子里坐起,闭着眼睛大口地喘气,希望自己再次睁开眼时,眼前还是花影蹁跹。
奈何意愿难遂,睁开眼,我看到自己在一个气氛压抑的院子中央。
院内四角挂满白色灵旗,一幡一幡,飘荡在空中,仿佛未逝的灵魂。
人生将近二十载,我第一次见到这样恐怖的景象,吓得低下头不敢再看。
低头一看,更加骇然,我竟坐在一口棺材里!
我顿时惊起,跳了出去,足下的爆发力将那棺蹬出数米开外。
我立在原地,头皮一阵阵发麻,心跳得厉害,定定地遥望那口破棺,不敢相信自己方才待在那里面。
究竟是谁把我带到这个地方的?
为什么要把我装进棺材里?
“公子。”一个冰冷的声音凭空响起。
我不禁毛骨悚然,下意识地后退一步,却撞上了什么东西。
惊得我猛回头,入眼是一张苍白、面无表情的脸。
“对不起!”我快速地说出这三个字,脚下利落地前移了几步。
“我家主人在前庭等着公子。”身后的人不知何时已来到我身前。
头皮麻到紧绷,我感觉自己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那人走在前,身量纤弱,少年似的背影,轻飘飘的,仿佛一阵风就能将他吹走。
“这是哪儿?”我不由发问。
“骨冢。”他不回头地发出这两个简单冰冷的字。
“你家主人是谁?”我隐隐有些猜到答案,但还是忍不住问出这句话。
“到了,就在你面前。”
我抬起头,眼前已经不见了方才那个少年。
我环顾四周,都没有再看见他,他来得悄无声息,去得也是悄无声息,仿如鬼魅……我被自己吓了一跳,在心里啐了几口,呸呸呸,大白天的哪里会有鬼!
这是另一间院落,却与方才那个别无二致。
白到近乎灰色的灵旗,黯哑的光线……这个院子仅有灰白两色。
院落中有一个人,背对着我,一身白衣,发如墨泽。
他一定就是那个把我弄到这里的人。
不管他是人是鬼,他都已经在我面前。
我不再慌张,盯着他的后背,问:“你是谁?”
那个人缓缓转过身……
我终于看到他的脸,但那张脸上,却是一片空白,他没有五官!
“我是……”
院中突然狂风乍起,满院的灵旗疯舞着脱离幡杆,向我扑来。
我抬手抵挡,风呼啸着灌进我的袖子,旗穗抽打在我身上。疼痛中,我丧失了听觉,但我还是不甘心地嘶声吼问:“你是谁?你是谁?你究竟是谁!”
……
“谁是谁?”
轻柔的声音飘进我的耳朵,我慢慢睁开眼睛,眼前不见纷繁花影,也不见午后的碎光,只有一张放大的人脸,在我头顶遮出一片阴影。
是颜相亭。
我翻身欲起,却一个轱辘滚下了吊床,重重摔在地上,吃了一口杏花拌土,身侧震起的浮尘雪上加霜地迷了我的眼睛。
我放弃挣扎,无力地趴在地上喘气。
“你做了什么好梦,吓成这样?”耳畔响起颜相亭悦耳的调侃。
还好,我尚在人间。
喘匀最后一口气,我从地上站了起来,拍着衣上的土,瞪他一眼,没好气地说:“梦见你了!”
“那一定是个好梦!”颜相亭哈哈大笑。
我没理他,转身就走,手腕传来钻心的疼痛,方才着地时狠戳了一下。
“我新接了一单生意,要去颐水都,你要不要随我一起?”颜相亭在我身后喊。
我站住,疑惑地回头看他,“你不是要歇一阵子?怎么又接生意?”
他看着我,面带笑意,“主要游山玩水,捎带做生意。怎么样,要不要一起去?”
我转过头,继续向前走,“不要!”
“听说颐城的姑娘美如花,你不去,满城春色,正好我一人独赏。”
这个登徒子,癞蛤蟆还挺想吃天鹅肉,不行,不能便宜了他!
我再次回头,笑容比春花还要灿烂,“颜兄,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我们何时启程?”
颜相亭一脸奸计得逞的狡猾,笑着吐出两个字:“明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