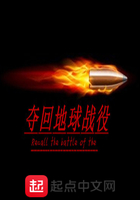公元1970年8月25日,我在北大荒上一个名叫新生的小村出生了,那一年是狗年,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从小,我就喜欢狗。
从我开始记事起,我就是和狗一起玩儿大的。养了很多只狗,但都先后因为种种原因而失去了,也淡忘了有关那些狗的记忆。但有关那只叫阿黄的狗的记忆却似刀雕斧刻般在心头,时时让我疼痛和内疚。
阿黄是在我刚刚读小学三年级时从外村抱来的,因为浑身上下都是黄毛,被叫成了阿黄。它似乎对自己的名字很喜欢,小不点儿的时候,只要有人叫“阿黄”,它就会应声跑过去,摇头摆尾地献媚。慢慢长大了些,再有人叫“阿黄”,它就会有选择了,陌生人怎么叫,它都不肯靠近的,叫得急了,它就吼叫起来;熟悉的人叫它,它也只是试探着走近,面无表情地观望叫它的人有什么动向;而一直把它照顾大的我,无论什么时候喊“阿黄”,它都会应声过来,孩子般地往我身上扑。
那时候,农户人家是只喂猪鹅鸡鸭的,对已经长大了的狗基本上是不闻不问不喂。阿黄也难逃这种命运,常常靠捡食猪鹅鸡鸭的残羹果腹。我便常常把自己的午餐分一半给阿黄,甚至哪怕只是一块糖块,也要分一半给阿黄。每每看着阿黄得到我的一半午餐和零乐是一种能力食后的欢快样子,我心里就很是安慰。可当晚上放学的时候,我的肚子饿得呱呱叫的时候,我就会想到,吃过早饭和半顿午餐的我还这样饿,只吃过那点午餐的阿黄一定会更饿,想着想着,我的心里就会酸涩起来。
我和阿黄最快乐的日子就是在夏日的周末,一起去村外的草地,我挖野菜,它追蝴蝶……野菜挖够了,我就躺在草地上晒太阳,憧憬理想,阿黄就伏在一旁陪着我,一动不动,生怕打扰了我的遐想似的,只是两只眼睛不停地转来转去,间或孩子气地用鼻子嗅嗅我的衣角。
阿黄是一只非常通人性的狗。每天上学,它都会跟着我到村小学校的校门外;而我放学的时候,它总会等在校门外不远处,看到我便会欢快地跑过来,我便常常把书包挂到它的脖子上,它便很吃力,但却很骄傲地“提”着书包陪着我往家走。那样的日子总是美丽的。
小学毕业后,我开始到3公里外的镇中学去读中学,阿黄也开始送我去上学。去镇上要经过一片树林,阿黄每次都将我送过树林,然后在我放学的时候,再等在那里。
一天放学,天空布满了乌云,我意识到就要下大雨,就急匆匆地往家赶。可刚出镇不远,大雨就瓢泼着下了起来,我很快就被淋得透湿。我以为,下这么大的雨,阿黄一定不会再等我的了,可刚刚走近树林,雨帘中就奔过来阿黄的身影,我心里不禁很是激动,向阿黄跑过去,可没有跑两步,脚下一滑,我一下摔滚到路旁的沟里,脚撞到一根树桩上,立刻有血流了出来。我试探着想站起身来,可脚腕处钻心地疼,又一下跌坐在地上。这时,阿黄已经跳到沟底,围着我不停地绕着,吠叫着,声音里竟满是焦灼和不安。我无奈地看着它。阿黄用嘴巴咬住我的衣服往起撕扯着,继而松开嘴巴,往后退了两步,对着我吠叫着,好像是在鼓励我再试试。我看着阿黄,点点头,再一次尝试着站起来,可又失败了……阿黄停止了吠叫,怔怔地看了我一会儿,来咬我的书包,我木然地看着阿黄。突然意识情到,阿黄是想要我的书包啊!我将书包挂到阿黄的脖子上,阿黄冲着我低叫了几声,然后挺起脖子,跃出沟,往村里跑去……
二十几分钟后,阿黄的叫声透过雨声和雷声由远而近传来,紧接着,阿黄出现在我的视线里,很快,我的父母也气喘吁吁地出现了。趴在父亲的背上,看着跟在一旁的阿黄,我的眼泪扑簌簌地滴落着。
此后,阿黄成为了家人眼里的功臣,父母总会不厌其烦,一遍遍地向邻居炫耀介绍阿黄报信救我的事。阿黄的命运也因此改变了许多,它不必再去捡食残羹了,但仍是很难吃饱。在那个连人吃饱都不容易的时代,阿黄应该是村里所有狗中最幸福的了。
我读初中的一天,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阿黄像以往一样在树林旁等着我,和阿黄回到家,院子里挤满了邻居,被村人暗中叫为“泼妇”的张婶看见我和阿黄,冷哼了一声,对着阿黄叫骂道:“就是它吃的,这个偷嘴的畜生!”我诧异地看向父亲和母亲。父亲和母亲的脸色都冷冰冰的。我试探着问母亲发生了什么事情。母亲的眼圈就红了,将我拉到屋里告诉我,邻居张婶家的小鸡雏不见了3只,张婶说是被阿黄给吃了,吵骂了一下午,父亲说阿黄不会吃小鸡雏的,可张婶却咬定就是阿黄吃的。父亲没有办法,答应赔钱或者赔鸡雏给张婶,可张婶不依不饶,说是一定要让阿黄赔鸡雏的命。还说为了证实她没有冤枉阿黄,一定要把阿黄开膛来证实……我的大脑迅速膨胀着,挣脱掉母亲的拉拽,冲到院子里,对张婶叫道:“阿黄绝不会偷吃鸡雏的,你在冤枉阿黄!”
“这左右就它这一个畜生,不是它是谁!就是这个该死的畜生偷吃了我家的鸡雏,把它吊死,开膛破肚……”
张婶的话像火药一样在我的心里爆炸着,点燃着我的愤怒和委屈,泪水不争气地掉了下来,我大叫道:“阿黄不是畜生!阿黄没乐是一种能力有吃小鸡……”可张婶的声音比我的还要大:“今天非把这畜生开膛不可,不然好像我在冤枉嫁祸它似的……你家的狗是宝贝,我家的鸡雏就不是宝贝了啊……”
父亲找来绳子,挽成套,决定要按照张婶的要求,吊死阿黄!我歇斯底里地哭叫着,诅咒着张婶,哀求着父亲。母亲牢牢地抱着我,劝着我:“只有这样才能证明阿黄是清白的,咱们家是清白的。孩子,别叫了……”我听出了母亲声音的抖颤,抬头看向母亲,发现,母亲的脸上正有泪水淌下来,我的心一紧。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母亲流泪,我知道,阿黄躲不掉这场灾难了。我看向院子里的阿黄,喊叫着:“阿黄,快跑!跑得越远越好,快跑啊!”
阿黄似乎早已经从我的哭喊中意识到了危险,当父亲想靠近它的时候,它惊恐地吠叫着、退缩着,眼睛探求地看着我,我挥舞着手臂,赶着它。可它却不肯离开。父亲没有办法,进屋找来半个馒头,递向阿黄。可阿黄仍是不肯靠近,和父亲始终保持着距离,吠叫着。
十几分钟过去了,父亲仍是没有办法靠近阿黄,张婶在一旁催促着。父亲看向了我,满眼的无奈、哀怜和坚定:“把阿黄叫过来!”父亲的话向刺刀般一下刺到我的心上,我的心抖颤着,怔怔地看着父亲,父亲的眼角凝结着晶莹的东西,眼睛里已经满是不容拒绝。我默默地走向阿黄,阿黄哀怜地看着我,先是迟疑着,退后了一步,继而又迈近我,靠到我的腿上。我蹲下身,双手抱住阿黄的头,泪水决堤般流淌下来。阿黄抬起头,伸着舌头舔着我脸上的泪水。我抚摩着阿黄,抽泣起来……阿黄突然扬起头,吠叫了一声,声音里满是凄凉和悲哀,那一刻,我清晰地看到阿黄的眼角有一滴泪水掉了下来。阿黄吠叫过后蹲坐在地上,看着我,眼睛里竟有一种我难以相信和理解的安详和安慰,稍后,把头扎进我的怀里,很安详地闭上了眼睛……这时,父亲突然把绳套套上了阿黄的脖子,阿黄骤然睁开眼睛,挣扎着……我大叫着“不!不!不!”扑向阿黄,可被几个人死死地抱住了……
15分钟后,阿黄被剖开膛,肚子里没有一只鸡雏的影子。父亲在村外埋葬了阿黄。那年,我13岁,却似乎一下长大了。一年后,我搬离了小村,再也没有回去过,此后,再也不肯养狗。
【拾贝】
多年后的今天,我耳边仍然会常常响起阿黄那声凄厉的吠叫,它的那滴泪水仍然常常浸湿我的心,就常常会为自己辜负了阿黄而内疚而疼痛……当我决定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的思绪突然清晰起来,我突然意识到,当年,聪明的阿黄是能够从我伤楚、惊惧的眼睛里读懂危险的,而它依然走了过来,是因为它是一只深懂忠诚的狗,甚至不惜用自己的生命来书写这两个字。它向我走来的时候,一定想了很多,一定满心悲壮和酸楚,但也一定是心甘的泰然的。如果它知道今天的我依然如此耿耿地怀念它,内疚着,疼痛着,它一定会为自己的牺牲而不甘,它是决不忍让它的魂灵成为坠压,负载上我心头的!对阿黄,最好的怀念应该是忘记啊!
阿黄,让我来忘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