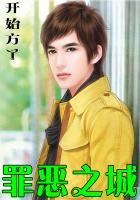“你到底有多少个身份呀?一会儿是少爷公子,一会儿装乞丐。”
“乞丐。嘿嘿,我第一次听人对我说过。从你口里说出来,蛮有味道的,我喜欢。我要申明一点,那不是我刻意去装的。”
“你说这话,谁信?”
“至少,我认为你信。当然,我不排除余艺可能会信,虽然她带人揍过我一次。不过现在想想,回忆真美啊,却不是为我封存的。”
不知不觉的,萧萧被林峰的话引入琐碎的记忆中,眼前闪过一幕幕昔日情境,她想起体弱多病的父母。
林峰趁热打铁,越说越有劲,语速不是很快,有点像催眠曲。
“有一次,在一个阴雨连绵的中午,我跟在你和余艺的后面,余艺撑伞,你们一同走到校门口,我看到伯母给你送伞。”
萧萧记起那次郑芸妈妈送伞的事,却不知道自己曾经被林峰鬼鬼祟祟的跟踪过。
“哦,对了,那次你参加完音乐比赛,好像是余艺替你领的奖吧。”
林峰的监视,神不知鬼不觉,萧萧从不知道。那时的林峰,表面看是个优秀学生,竟然会做出这样的行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而且是中学生,更让人不敢想象。
“那次,我送牛奶给你,你不要也就算了,余艺还把牛奶扔进垃圾桶。”
; ; ; ; ;林峰轻微一笑,目光悄悄盯着萧萧的脸庞,这种笑像是一把水果刀子插在苹果里,而萧萧全然不知。情感动物就这样。就拿蜜蜂来说吧。蜜蜂徜徉在春天的花海中,它忘却了季节,找不到回去的方向。如果说蜜蜂被花香迷惑了,那萧萧便是被温情的话语迷惑。萧萧的感性,是她的缺点,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陷入林峰精心设置的迷局。
接下来一步,不知道林峰会使出哪招,我们为萧萧感到担忧。
“唉,不说了。”
林峰的视线从萧萧的脸庞移开,他拿起酒瓶,把余下的酒全部倒进杯子里面。喝下酒,林峰把空瓶子往地板上放,不知怎地,空瓶子哗啦啦朝萧萧座位滑去。没过多久,停在萧萧椅子下。
现在是晚上九点。
墙壁上的老钟敲了一下,林峰和萧萧都没注意听,余音已经消散。
林峰一共叫了四瓶酒,刚刚喝了一瓶,惬意酒家的酒,度数分为四个等级,林峰喝的属于第一等级。
划分酒的等级,其中一个标准是精酒度数的高低,而实际操作过程是按接酒的先后顺序。
惬意酒家的酒之所以畅销,那是因为它的消费人群广,有社会不同阶层的消费者。决定消费人群的是酒的级别,级别越高,价格越贵。
惬意酒家采用传统工艺制酒,这是它在酒的江湖中久经不衰的一个重要原因,并且使它名扬四海。
制酒是一门技术活,惬意酒家有专门的制酒技师,技师分为高级技师、中级技师和初级技师,技师之下的是学徒。
级别不同,待遇不同,学徒薪水两千块钱左右,主要负责玉米粒的蒸煮。而高级技师负责的是配酒,调制出不同口味的酒,薪水高达几万。中级技师负责酒药和玉米的比例以及火候的控制。初级技师负责接酒,这步非常重要,关系到成酒的等级。
惬意酒家的制酒流程线,层次鲜明,条理清晰。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是落实到每一步就不是那么容易啦。
首先,要把玉米粒蒸熟。在蒸煮过程中,火候的控制尤其重要,因为玉米粒受热不均匀,直接影响成酒的质量。
玉米粒蒸熟之后,下一步调整酒药和玉米粒的比例。恰当合适的比例,酿出来的酒,独具风味。
接下来,便是发酵。这一步在整个制酒过程中,是最为重要的一步,也是最难控制的一步。不仅要控制适宜的温度和湿度,而且还要空气通入量。酵母菌是一种兼性厌氧菌,氧气的含量,影响它的发酵,最终决定酒的产量。
发酵时间一般为十五天到一个月,具体得根据周围条件来限定。
发酵完成后,将玉米粒装进一个很大的容器里面,容器的底部,放有用竹子编成的网状过滤器,但是玉米粒不能漏过。容器的上方放置一口大锅,酒师们把它叫作“天锅”,里面装满水,用于冷却。整个装置也是放在一口大锅里面。然后给整个装置加热。
距容器上口,占容器高度略有五分之一的地方开一个口子,插入一根管子,酒从管子流出来。
在这个过程中,一边控制火候,一边换“天锅”里面的水,还得有人负责接酒。
管子里先流出来的酒,属于上等品,经过高级技师调配,成为第一等级的酒。
以此类推,划分酒的等级。
林峰出国留学,学会喝酒,他认为酒是世界上最懂灵魂的东西。
“出国留学,吃了不少苦吧?”
萧萧的眼神变得温和,她把手放在膝盖上,微微倾斜身子,看着林峰的脸。
“我喜欢享受‘苦’的味道。从我有生命开始,一直都是。”
“为什么这样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乐意当你的倾诉对象。”
“二十一年之前,妈妈生下我没多久,她离家出走了。”
林峰和着泪水喝下酒,心似乎在颤抖,因为话语不是那么清晰。
“爸爸没有去寻找。”
; ;林峰双手捂着额头,皱着眉头,沉默了一会儿。
“后来,爸爸给我找了一个后妈。”
灯光照在林峰脸上,反射进入酒杯,发生弯曲,勉强还可以分得清他的容颜,瞬间衰老好多,看着一点都不像二十一岁的青年,反而更像六十岁的老头。
“后妈和爸爸生了一个妹妹。妹妹很可爱,十分招人喜欢。”
林峰把手中的空杯子转来转去,脸露微笑,像在想象美好的事物。
“他们搬去另一个地方住,妹妹一块去了,留下我和爷爷奶奶。”
萧萧静静的听着,呼吸声都没有分针转动的声音大。
“嘿嘿。再后来,当初离家出走的妈妈回来了,说是要和爸爸复婚。爸爸说她简直是无理取闹、荒唐,妈妈一急之下,把爸爸告上法庭,说爸爸犯了再婚罪。”
林峰停顿。不一会儿,又慢悠悠的吐出每一个词眼。
“过了很长时间,好像有半年时间吧,我记不清楚了。妈妈败诉,狼狈不堪的样子,我傻了眼。她送了一个手机给我,但是我从来没有给她打过电话,即使她打来了,我也不接。读初中的时候,爸爸给我买了一个苹果。在我的记忆中,爸爸很久才回来一次。每次向他要钱,要多少给多少,放到口袋装不了。那个时候,我以为他是我的摇钱树,是我依靠的大树。”
“原来你也是苦命的孩子。”
“你这是幸灾乐祸呢,还是同情?”
“我觉得你的某些心里感受和行川相似。”
“行川是谁?”
“行川是我最爱的人,是我这辈子的宿命。”
“我和他一点都不像,因为从初二起我变坏了,我已经不再是我。”
月光从林峰没有拉拢的窗帘缝里穿出,没有连成一条线,像散点图一样,被限定在二维方向,逃也逃不掉。
每一个小圆点,释放明亮的光芒,宛如漫天星星倒映水里,风一吹来,碎成一片。
其实,房里的大部分空间都是亮的,只有桌子底下和林峰后面是黑的,林峰后面不算是全黑,那块地方躺着斑驳陆离的亮点。
萧萧没打算再问林峰为什么变坏了。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变坏?”林峰突然问。
“变坏没有标准。”
“哈哈。”
“你笑什么?”
“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变坏意味着心灵不再清澈透明。”
“好好的一个孩子,他怎么会变坏?林峰,你不要把一些极端的想法加到别人身上去。”
“然而并没有。”
“你这是强词夺理。”
“说我强词夺理?”
“难道不是吗?”
“听说过‘动物通性’没有?”
“不曾有过了解,偶有听说。”
“动物通性,指的是在某种动物群体中,它们具有的某些习惯或想法大致是相同的。”
“说这个干嘛?”
“证明我并没有把我的想法强加到别人身上,特别是孩子,因为我在孩童阶段遭遇不幸。”
“我不想反驳你。”
“是吗?”
林峰皱眉而问。
“也许你没有过这种经历,才会这样认为。”
“虽然没有过,但是我可以想象。”
萧萧说得很干脆,故意压低声音,像是自然界中狼对狮子的警告,但是萧萧忘了,狮子毕竟是狮子。
“你曲解了我的意思,我没有说你不能想象。想象一下,一个没有父母疼爱的孩子,一步一步的走向堕落,最后不可挽回,你能体会到那种心里挫败而又纠结的感觉吗?”
“我觉得没什么不能挽回的,除了生命和青春。”
“请不要逃避我的问题。”
“好,那你说说。”
“没有人管我,我整天躲在房间,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别说了。”
“你不是要我说吗?现在我就给你讲讲,一个孩子是怎样走错路的。”
萧萧手拿提包,站起来,对林峰说。
“我要求你打电话给服务员拿钥匙来开门。”
“哟哟,你还要求我咯。告诉你,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对我,即使在国外。”
“林峰,你要是再不拿钥匙开门,我就喊了。”
“你喊呀,随你。顺便告诉你,这间房原来是惬意酒家用来藏酒的,密闭性不用我说吧。”
“林峰,你到底想要干嘛?”
“我不想干嘛,既然你不想听我说一个孩子是怎样走错道路的。那现在,我用行动来告诉你,一个成年人是怎样犯罪的。”
“你放开我,你个禽兽。”
; ; ; ; ;萧萧还没反应过来,林峰一把抱住,提包掉落地上。那是一声巨响,撞击着萧萧的心肺,又像是一场噩梦中的雷鸣。
萧萧拼命挣扎,但是她的手被林峰捂住,根本施展不开。像一只小鸡,被老鹰捉住,刁在嘴里,甩来甩去。
小鸡尖锐的叫声,丝毫没有动摇老鹰,反而增加老鹰的愤怒。
这是一只疯狂的老鹰,对它管辖领域内的小鸡下手,以前它没有动手,是为了等小鸡长大。小鸡长大了,老鹰从觅食的远方回来,专门设计一个圈套,逮住小鸡。可怜的小鸡被老鹰的话语迷惑,生出同情心,刚才还倾听它讲故事呢。
一只蝴蝶落在杯子边沿,抖了抖翅膀,飞走了。
“砰”
一声巨响,门被撞开,行川先进来,余艺和旭日紧随其后。
林峰呆了,放开萧萧,回到座位坐下,端杯喝酒。
萧萧摊在地上,缩成一团,像刚落水的狗一样,半天没有反应过来。
行川过去抱着她,帮她把扣子扣好,然后脱下自己的衣服,给萧萧披上。
“萧萧,没事了,有我在。”
余艺一进去就骂开了,双手指着林峰脑袋,越骂越近。
“林峰,你这个王八蛋。”
旭日也说开了。
“你竟然对老同学下手,厚颜无耻。”
林峰一股劲的喝酒,表情平淡。像是在对余艺说,“你们骂吧,继续呀。”
现在是晚上十点钟。
旭日走到窗台,拉开窗帘,看到街道上有几个行人,边说边笑,每个人手里拿着一瓶酒。但不知瓶子是否空了。
余艺对旭日说。
“旭日,你在哪儿愣着干嘛?快打电话报警呀。”
旭日突然想起,拿出手机,拨通警局电话。
月亮圆圆的,透亮的光芒洒在地上。
“他们说,一会儿就到。”
没多大会儿,警车上走下四五个民警,惬意酒家的十多个员工围观,也许他们还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只有柜台的那个服务员知道,刚才有三个青年,两男一女,问了情况后,匆匆上楼。
警察到房间,问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旭日在电话中只是说在惬意酒家有事发生,但是没有具体说明。
余艺刚要开口,被萧萧阻止了。
“我们一起在这儿喝酒,发生了一点争执,已经协调解决。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
萧萧的声音近乎悲凄,像是自己做错事一样,乞求别人的原谅。
行川接过话。
“谢谢,我们自个解决了。”
“嗯,那好,你们要是没事,我们走了。记得,一定要和谐相处。”前面的那个警察说。
“萧萧,我们走吧。”
现在十一点半,墙上的老钟没有敲响,行川他们已经走出惬意酒家。
林峰独自坐着,满脸写着忧郁的神情,四瓶酒只剩下一杯。
“萧萧,你看今夜的月亮多圆呀。”
行川扭头对背上的萧萧说,掂了一下。
“要不是行川打电话来,我还以为萧萧是和行川一起去惬意酒家的。”余艺说道。
今晚,行川和萧萧本来有约定的,萧萧在厢房才想到,但是没有打开门,随后发现电话也不在,所以,没能给行川通电话。
行川打电话给余艺,才知道萧萧有事,去惬意酒家了。行川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想到萧萧从来不会一个人出去。于是,再次拨通余艺的电话,说明了他的担忧,余艺也感觉奇怪,他们叫上旭日一块去惬意酒家,幸亏及时赶到。
余艺转头看楼上的厢房,灯仍然亮着,拉开的窗帘上仿佛有一个影子,风从窗口吹进去,窗帘上的影子随窗帘的摇动变得十分难堪,最终消失了。
萧萧没有从刚才的噩梦中醒过来,伏在行川背上,像蜗牛背上的落叶,枯黄颜色显示出秋天的苍白,没有一点儿生气,仿佛抽干灵气的尸体一般,看着十分害怕,连萧萧自己,皮肤上间段性的冒出鸡皮疙瘩,心里不由得生出一股凉意。
回想着刚才经过的事情,萧萧被动联想到林峰的人生经历,看似没有半点关系,正是这种像梦境一样的轮换,使得她心力狡猝。
与其说是幻想的破碎,不如说是幻想纯粹是幻想。萧萧的善良,牵引着她,力求把一切优秀的品质往林峰身上放,因为她相信每个心灵都是纯洁无瑕的。
如樱花般纯洁,不会参杂一丝恶劣天气留下的迹象,它为人类精神的储存提供空间,没错,在那花纹下面。
每一条花纹,是那么清晰,红色透明,或是白色透明,红色的红似玫瑰,盛开在满是爱的季节,白色的白似雪花,下坠在满是温暖的季节。
爱与温暖,相互关联,正如白色与红色的精细搭配,产生粉红色的春天。漫步春天,虫鸣鸟叫,满目的彩色,梦想与柔情涌入心房。
美丽的心房,是每个人心火的源泉,当寒冷袭击的时候,它缓缓燃烧。释放的温暖,荡漾心海,浪花在风中飞舞,影子漫上蓝天,嵌入海水。蓝天碧水,云淡风轻,像一杯奶茶的,散发了的清香,贯穿十二月的宪书,和六七层的宝塔。
宝塔其实是一座心房,每个人都有,它的旁边,是一片薰衣草,淡紫色和着浪漫的气息飘扬。气息里面,有各种各样的爱,夜风吹不垮,黑幕吓不倒,它就这样存在着。你可以用皮肤感知它,轻油般的流体,温柔滑过,带走满目苍夷,留下阵阵羽感。
薰衣草之间,间种的郁金香,淡淡的黄色,仿似一层薄膜,上面堆满阳光和月光。阳光和月光,分别给人不同的感受,或暖或阴,但似乎都象征一种惨淡的美,无法言说的美。
惨淡的出生,惨淡的经历,惨淡的交际。相比之林峰,萧萧的同情越发加强,却不能改变什么,让人有点悲伤,这种悲伤体现在萧萧的脸上,便是今夜苍白无力的月色。
月光的触动,萧萧在心里默默祝福林峰,希望他能看清心路,放下过往的一切,重新启航。在路的前方,有一个如春的季节期许他靠近,靠近之后,不再纠结,活得轻松自在、简单平凡。
萧萧忘掉刚才发生的一切,像是做了一件好事,拯救了林峰,而她正好忘了受害者是自己。
萧萧的手一下用力起来,紧紧的贴在行川背上,行川感觉到。
“行川,你看,今晚的月色多美呀。”
“嗯嗯,但是没有你美。”
“咦,你怎么学会贫嘴了?”
萧萧向前靠了靠,右手点了行川上嘴唇一下,然后迅速收回。
“你再伸我嘴里,我咬了啊?”
明明没有伸到嘴里,行川偏偏说伸到嘴里,让人想不通。
“萧萧,有时间我们去湖心草原,那儿有一个亭子,叫作赏星亭。据说,那儿的夜空有最明亮最美丽的星星,幸运的话,能够看到星系移动。”
“什么叫作星系移动呀?”
萧萧嘟嘴,眼里充满好奇,她微微仰头看着夜空。一抬头便是月亮,周围有稀疏的星星,数量不是很多。萧萧相信一定没有湖心草原上空的多,这引起她无限的向往。
“星系移动,具体来讲,我也不太清楚。我的理解,某一颗或者多颗星星的运动,引发连锁效应,带动周围的群星,一起移动。既像浪花波动,又像音符跳动。”
“我好想去看呀,川。”
“找个空闲的时间,我们就去。”
“嗯嗯。”
萧萧的脸贴着行川的背,面露温润的淡红色,眼角的眉毛,向上翘起。不知它是在看星星本体,还是在看星星的影子,或是和星星对话。
余艺和旭日跟在后面。
“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噩梦。”
下课后同学都走了,余艺和旭日也先走了,只有行川和萧萧留在后面,萧萧对昨晚做的梦感到害怕,她不想憋着,于是对行川说起她昨晚做的梦。
“傻瓜,你一定是还没从昨晚的事情中走出来,没事的,有我在呢。给我说说,你昨晚做了什么梦。”
“那是一个长长的梦,一想到我就害怕,我不知道该不该说。如果我说了,我会更害怕的,我一刻不想离开你,川,我真的很害怕。”萧萧的声音颤抖,话语断断续续的,教室里弥漫着恐惧的气氛。
行川紧紧握着萧萧的双手,“别怕,有我在。来,靠着我的肩膀。”
萧萧缩成一团,全身无力,紧紧靠着行川的肩膀。都不知道萧萧是怎样度过一早上的课,怪不得刚才上化学课的时候,上了半节,行川才发现萧萧拿得竟然是材料导论。
“萧萧,别怕啊,有我在呢。”行川重复说着,并且右手搂着萧萧的右肩。
行川看过心理书,说是心里有事情而感到恐惧的时候,最好找一个朋友或是同学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些。
“萧萧,给我讲讲你昨晚做的梦,讲出来心里会好受些,别怕,我一直在。”
“昨天晚上我梦到上了一辆公交车,阳光和雾水一同笼罩着公交车前行的方向,公交车始终行驶在一条直道上,没有叉道。车上的人表情稀奇古怪,没有人讲话,车里静得让人窒息。”
萧萧的手用力抓住行川的衣服,眼中闪耀着泪花,脸露狰狞。
“公交车开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路边的牌子上写着‘死亡通道’路的右边有一个宽阔的湖,湖面烟雾缭绕,看不清尽头。再过了一会儿,我看到路的前面有一座桥,桥跨过公交车行驶的道路,也是烟云缭绕的,甚至连路线都看不清,全是模糊的。我看见公交车司机从来没有改变一个动作来控制车的方向,到转弯的地方,车子自动转弯,当我抬头看的时候,我看到桥上挂着一团黑乎乎的东西,我揉揉眼睛,仔细看发现那是一具尸体,流着的血滴落在路上,在这条路上我没有看到其他的车子。转过一个弯道后,我突然发现前面全是车子,都亮着刹车灯,这时我发现公交车已经在湖面上了,而且速度越来越快,像飞一样,车上的一个女乘客突然大叫一声‘啊’。然而车子并没有停下,反而速度变得更快,湖面上有一个修车的店家,但是没有人,只有废弃的轮胎之类的东西仍在外面。前面那些亮着灯的车子像发了疯一样向湖面冲去,突然间车道变得特别狭窄,眼看着公交车就要撞上了,公交司机没有减速,而是一脚踩在油门上,这次司机的动作十分明显,所有乘客都看得清清楚楚,仿佛他们在怒斥司机,但是我没有听到一丁点儿声音。”
萧萧脸上没有一丝表情,眼睛过了一分钟没有眨动,手变得冰冷,行川感到事情不妙。“喂,萧萧。”
“让我说完。突然,那条道晃动起来抖落了一些车子掉进湖里而没有一丝声音。没有掉落的车子,从车窗伸出一个头,全是动物的头颅,而且只能看清大体形象,不能看清,也是黑乎乎的,像之前悬挂在桥上的尸体一样。然后,所有车子一同涌进一个隧道,我听到车子在鸣笛,像炸药爆炸的声音。当我的眼光穿过公交车后面回头看的时候,我看见很大的圆石头朝我们追来,只有几厘米的距离,我看见石头上写着红色的字‘诅咒’。我一看到那两个字,头就特别疼,差点晕倒过去。幸亏这个场景只持续了几秒钟,然后消失了。穿出隧道,我看见一个头发凌乱的妇女站在隧道口挥动着左手像是让车停下,她的右手拖着一只箱子,那只箱子破烂不堪。她穿的衣服像是从垃圾堆里面捡来的,她用无奈的眼神看在正在向她驶去的公交车,当车子向她撞上去的前几秒钟她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我,看得出来她要把我吃掉,我没反应过来,她已经倒在车下。”
萧萧大哭,“呜呜……呜……她为什么要看着我?又不是我开车撞的她。”行川迅速抱紧萧萧,用嘴亲吻萧萧的额头。“不是你的错,萧萧,不是你。那个妇女,是她自己的错。况且整个车上不止你一个人。”
“然后,公交车飞起来了,我看见路旁有一家殡仪馆,墙上刷着白色的漆和红色的不知道名字的什么东西。殡仪馆的后山是一片看不到尽头的墓地,有一座新坟墓尤其显眼,燃着刚刚烧过的冥币,我看的清清楚楚,还有黄色的草纸,没有祭酒,因此我推测那个墓的主人一定是个女的,难道是刚才的妇女?怎么可能?我一直在追问,直到从噩梦中醒来,被子已经湿透了。醒来以后,我不敢往窗外看,用被子捂着头直到天亮也没有睡觉,但是我很奇怪今天早上上课没有半缕睡意。”
“你看,教室外面阳光多么鲜艳啊,没事啦。”行川用手揉萧萧的脸蛋,然后指着窗外,突然笑了。
萧萧依着行川肩膀睡着了。
一只蝴蝶从窗口飞进教室,落在放在窗台里面的盆景上,翅膀上下轻轻扇动。它有着树叶颜色一样的触角,不时微微抖动,像晨露闪耀着晶光。
没过多大会儿,又有一只蝴蝶飞进教室,先是落在和之前那只蝴蝶的同一片叶子上,后来跳到另外一片叶子上了。
第二天下午,第二节课刚下,萧萧的电话响了。
“喂,你是萧萧吗?”
“嗯,我是萧萧呀。请问您有事吗?”
“萧萧,我是你大伯,家里有事,你务必请假回来。”
“有什么事啊?”
“你回来就知道了。”
“哦…………”
挂了大伯的电话后,萧萧急忙拨通爸爸的电话,拨通了但是没有人接,她按下重拨。“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萧萧感到不安与焦虑,脑子一片空白,如同找不到方向的大雁。
“行川,你帮我向老师请假,我有事需要回去一趟。”
“好的,你去吧。”行川答应她向老师请假。
行川回到寝舍立马把两套衣服塞进书包,便向车站冲去。
今天人流量大,萧萧没能很快买到回去的票,排对用了一个小时左右。
她坐上车子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五点半了,什么东西也没吃,但她没有感觉到饿。
坐上车后,萧萧心情时而低落,时而狂躁,她心里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十二点四十左右,车到站了,旅客纷纷走下,四散而去。
萧萧五点半上这趟列车的时候,在武汉的那个季节里,下午五点半天还没黑,车子到达终点站,天空一片漆黑。伸出五指,也看不见了。
坐了十二个小时的车,萧萧的感觉却是从武汉一步跨到她家所在的这个飘洒着她儿时与郑芸妈妈的一切记忆的城市。
下车后,萧萧加快脚步向她家的方向走去。她家离车站不算太远,按萧萧的这种步速,不出十分钟就能走到了。
晚上的十二点,街道上几乎没有人了,就连出租车也不见了,只有红绿灯还在按时轮换。
行走在苍凉的街道上,萧萧感觉被千万双眼睛盯着。她时不时用余光扫街道的两侧,但没有看到什么。心里一阵发麻,暴露在空气中的手上蹿出一个个鸡皮疙瘩。
当她经过学校的时候,停顿了一会儿,她看到学校门口的阿姨正在收摊,出来约会的情侣也从亮着灯光的大门走进去,保安喊着“快点,快点,我们要关门了。”
萧萧的高中就是在眼前的这所学校上的,这里记录了萧萧三年的经历,包括忧伤的事、开心的事。
现在,萧萧回想到那时开心的事也笑不出来,反而心里增加了一种莫名的沉重感。
看着眼前的寂静的夜景,萧萧想到那次郑芸妈妈为救她而被车子碾压最终不得而已换假肢的事情。
在学校门口停留片刻后,萧萧穿过一条狭窄的巷道,经过几个拐角,她远远的便看到自己熟悉的家亮着灯,周围一片通明,而且有好多人聚集在那儿。
门上的挽联映入萧萧眼帘,白纸黑字像在嘲笑着她。
萧萧涨红着脸,眼睛直直地盯着黑白色的挽联,她双肩在打颤,脸色瞬间变成了铁青,眼泪簌簌地滚落下来。
她双手捂着脑袋蹲下去,小手臂难为情的把脸藏起来,失声痛哭。
她就那么躲在拐角处,并没有要进屋的意思。
灰色的天空中,下起纷纷扬扬的毛毛细雨。不知为什么,寂静得使人难以置信。萧萧眼光呆滞,一脸茫然的望着虚空。
萧萧想起前不久回来,爸爸不是说妈妈的病已经好了吗?而且妈妈也说病好了。
怎么现在成这个样子了?
萧萧简直不敢相信,她接受不了这个现实。
她还记得上次回来的时候,妈妈陪她聊了很久,她还给妈妈倒水呢。
怎么现在成这个样子了?
萧萧站起来,拖着像是灌了铅的双腿,走进家门。
“萧萧,你回来了。你妈妈……走了……”大伯声音哽咽,话没说完便已经用手去抹眼角的泪水。
萧萧趴到在地,从门口一直跪到妈妈的灵柩旁,拿起妈妈的遗照哗啦一声痛哭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