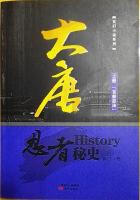一个卖红绘的年轻男子正从那儿走过去,背上的画纸在晨风中飘舞——这是江户街上一道柔和的风景线。
奇侠泰轩一口气推开了突然朝自己胸口刺过来的短矛。
“哈哈哈,我半夜潜进这儿来好几十次了,从来没被人发现过,可是今晚却被逮了个正着呀。啊哈哈。”
同时,忠相的声音也甩进了目瞪口呆的大作的耳朵里。
“休得无礼,大作!此人是我的挚友,名字不能说,不过他是身兼要职的大奥[1]密探,不可怠慢!你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就拿出利器刺他呢?快收起来!”
过去在伊势的山田时,忠相也在手下面前敷衍着假称泰轩是千代田的密探,但现在又说他是大奥密探。对于忠相的这些随机应变,敌视德川家的武田余党——蒲生泰轩在烛台的灯影中,显得有些尴尬地摸着脸,而毫不知情的大作为自己的鲁莽惭愧起来,一下子丢掉短矛叩拜在榻榻米上。
“啊,小的也不知道这位大人是什么时候进来的,而且这身装扮实为与众不同,所以不由得错把他当成危险之徒,多有冒犯……”
“嗯……你睡眼惺忪,也没仔细看吧?”忠相忍住笑说道。
“是的。”
“虽说装扮比较奇特,但这也是他职务的性质所致,正因为是密探才要打扮成这样的。这位大人可因时因地为搜索的方便而变换各种不同的打扮,有时还很离谱呢。”
“是,小的明白了,真是抱歉。”
“你也应该先问一声,怎能对正与我交谈的客人矛刃相向呢?这就是你的疏忽大意了。”
“还请大人饶恕小的……小的也替大人给客人赔个不是,望贵客原谅。”
“越州大人,他也知错了,你就别再追究了。不过我希望你记住我的样子,以后见我来时就准许我进门。”泰轩也抑制住内心的好笑,随声附和道。
“今后注意点儿就行了。”忠相嘟哝了一句,又问道,“你有什么事?说吧。”
大作这才想起阿艳的申诉,跪着向前凑了凑,说道:“大人,那个伊兵卫被拦路抢劫的强盗砍死了。”
“什么?你说伊兵卫,就是那个木匠伊兵卫吗?可是你怎么听到这个消息的?有人来申诉了吗?”
“正如您所言。”
“是个女子吧?”
“对,申诉者确实是个女子,但大人您怎会知道……”
“越州大人的神眼能洞察千里的,你天天跟在大人身边,连这个都不知道吗?”泰轩插嘴说道,大作畏畏缩缩地低着头。
“恕小的愚笨无知。”
忠相故作神秘地微微笑了笑,说:“传进来。”
“哈?”
“把那女子传进这儿来吧。”
“遵命!”
大作刚要站起来,忠相又叫住了他:“关于那个来申诉的女子,我姑且猜猜看吧。首先她是个貌美绝伦的年轻女子,而且应该是打扮成世间所说的深川短褂艺妓的样子吧。”
“其实小的也还没见过她,不过据通报的侍卫说,那女子大概就如大人所猜的那样。”
“一定没错,快去把她带进来。”
惶恐的大作终于急急忙忙退出去传唤阿艳了,忠相与泰轩对视着扑哧一声笑了出来。
泰轩结束血笔账之旅回到江户后不久,今夜又照例从庭院进到忠相的寝屋里,向他谈起自己在途中斩杀月轮援军的情形,而忠相则告诉泰轩,他把阿艳托付给与自己时有来往的木匠伊兵卫照顾,伊兵卫又自愿做阿艳的监护人,以一纸保证不卖身的字据把她卖到深川一家名为松川的置屋当艺妓。
还没来得及把阿艳当了艺妓之事禀告给大冈大人,伊兵卫就遭遇不测被人砍死,那么忠相又是如何对阿艳住进伊兵卫家中之后的情况了如指掌的呢?荣三郎的妻子阿艳是泰轩托给自己照顾的重要之人,虽说要留心一个女子的举动对奉行来说是不值一顾的小事,但忠相把阿艳交给伊兵卫后并没有掉以轻心。
大冈大人将万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
他派仆从有意无意地到伊兵卫家里打探消息,得知伊兵卫的想法——让阿艳闲着只会令她心灰意懒,因而打算让她去做艺妓,日子充实愉快了也好打发时间。忠相便想,若阿艳只是在宴席上侍奉一下客人,应该也没什么大碍,而且伊兵卫这个人靠得住,他办事一定不会有差错。所以,一开始就知晓此事的忠相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他正把这件事告诉泰轩时,阿艳就来申诉了。
一沉默下来,淅沥的雨声便隐隐约约飘进了屋内。
“晓雨……”忠相刚要吟出某诗中的一节,门槛上便好似忽地盛开出一朵明艳的鲜花——阿艳在门槛前伏了下来。
“是阿艳姑娘吧?”
“啊!泰轩师傅也在这儿呀!”
阿艳很是惊讶,忠相轻轻转过脸看着她,而嘴里只淡淡地说了句无关正题的话:“好像下雨了啊。”
“大事不好了,伊兵卫师傅被一个劫路贼杀害了!”
“嗯,我刚刚听说了。”泰轩镇静地靠在凭肘几上,问道,“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在方才……”
“地点呢?”
“是深川的相川町,若从这里走去,过了永代桥即船手组的宅邸,案发地点就在那宅邸后面一条幽僻的小巷里。”
“嗯,那是什么东西被偷了?”
“啊,这个……”阿艳似乎有些难为情,“我卖身得来的钱,还有从出羽大人那儿收来的三十两金币……”
“呵呵!”闭着眼睛在一旁听着的越前守忠相好像突然猜想到了什么,哈哈大笑起来。
“出羽大人的金币?那上面应该有印记,是个被圆圈起的‘羽’字,很好辨认。若顺藤摸瓜彻查,应该轻而易举便能抓住凶犯。让江户城内外各个钱铺预先做好准备,一发现那些金币就记到账本里去。好了!接下来就是那个凶犯了,没有人看到他的相貌吧?”
“啊,也并非如此……”
由于当前禀告案情要紧,阿艳都忘了自己是在幕府高官奉行大人面前,不由得对答如流起来,连她自己也吃了一惊。
“噢,既然并非如此,那即是说有目击者了?”
“是的,伊兵卫的随从阿新——”
“把话说清楚,这个阿新是何人?”
“他叫新助,是个小木匠,也是伊兵卫师傅的徒弟。据新助说,那个凶犯好像是个官差……”
“你说什么?!”忠相突然严肃起来,略带叱责地厉声说道,“是衙门里的官差?”
“是的。”
“住口!”
“……”
“我越前虽然不肖,但就任奉行期间,我所统领的属下中不可能有此种居心不良的鲁莽之人,拦路抢劫还杀人害命!那个人确实亲口说出自己是官差了吗?”
“不是,凶犯也绝非一开始就这么说的。从阿新的话来看,那人的装束打扮极像个官差,而且他后来也自称是官差了。”
“是假冒的官差吧?”
泰轩从旁插话道,忠相用犀利的眼神看着他说:
“你会作出这种推测还真让人意外。凶犯若真是故意要冒充官差,那他应当一出现时就说自己是衙门的官差了。可是你刚才也听到了,他一开始并没有这么说,这该如何解释呢?依我看来,也许此人不过是形似官差罢了,平日里大概也常被人误认为是官差吧。嗯,即使他蒙着面,而蒙面布不慎脱落下来,或者不小心被光亮照到脸让人看到了,他也知道自己平时就像个官差,这是原因之一;其次,他看到伊兵卫和新助认定自己是官差了,所以也就将错就错,突然摆起官差的架子来,一定是这样没错。”
“啊!”阿艳反而被大冈大人这番推断提醒了似的恍然大悟,又补充说道,“正如您所言。民女忘了说了,那个凶犯起先是蒙着面的,那蒙面布滑落下来,新助看到他的脸后才以为他是官差的……”
“我猜也是如此吧,要是蒙面布没掉下来,这个老狐狸也不会露出自己那张官差脸。估计他就是被人看到脸而当成官差后,才利用自己形似官差这一点。嗬,这么一来就能确定此案为平日里举止打扮颇似官差之人所犯!目的为抢盗钱财!哈哈,乍一看会让人怀疑是官差为钱所困而谋财害命。这个凶犯是谁呢?蒲生你有什么头绪吗?”
忠相回头看了看泰轩,细小的皱纹乐悠悠地爬上了他的眼角。
“说到官差……是与力吗?”
“对,不用说,一定是八丁堀或加役[2]之类的吧。”
“形似官差的武士劫财杀人……噢,且慢……”泰轩头一歪,立即想起去年秋天在藏前正觉寺门前发生的那件光天化日抢钱之事。
“哦!是他!”
泰轩刚要开口,忠相急忙举起手制止了他:“别说出名字!对方也是个有身份的武士,在掌握确凿证据之前还是,暂且把他的姓名保密吧。你和我对这一切都心知肚明,对吧?你知我知,我们都明白!”
莫名其妙的阿艳听得一头雾水,而忠相与泰轩突然异口同声地大笑了起来。
虽说现在已是春天,但清晨依然凉意袭人。
阵雨过后,庭院里树木的叶子上都积了露珠,在朝阳的照射下晶莹剔透。小草抽出嫩芽,一片生机勃勃,爽朗的空气里弥漫着草木的清香。
池子里响起扑通一声,红鲤鱼摆着尾巴一闪而过;防雨木窗还没打开,宅子周围的回廊上还飘浮着夜的余韵,迟迟不肯散去;对面的石灯笼之间浮现出一个身影——忠相将两手背在身后,穿着木屐踱来踱去。那身影深深隐没在清爽如烟的浅紫色晨雾中,显得有些渺小。
忠相每天早晨都会在庭院里散步。
远处的街巷开始苏醒,渐渐传来嘈杂声。耀眼的阳光很快便将屋脊镀上一层红色,麻雀也成群出动了,嘁嘁喳喳的叫声随处可闻。
然而,忠相无法与朝阳和麻雀一起愉快地迎接这崭新的一天,他心中布满了暗沉沉的阴云。木匠伊兵卫死于非命——此事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一个平民遭遇飞来横祸,被贪欲之剑杀害了……虽然此案另有隐情,但伊兵卫之死却总是萦绕在奉行忠相的心上。
晚了一步。
疏忽大意了。
忠相暗暗痛心地想着:
“我本料到那些恶徒迟早会干出这种恶行来,也早就在暗中监视他们了,可是却没有先一步派人将他们绳之以法,这是我的一大过失。我实在是愧对伊兵卫!”
“那家伙的各种不端之事我早有耳闻,他家中的丑事也是不胜枚举,单凭这些明明很容易就能把他制伏,而实际上,只有赌博这一项罪状也足以将那无赖之徒押走。”
“我明明对此了然于心,却仍然纵容了他们,认为等他们亲自犯法之后再行动也不迟……而就这么袖手旁观按兵不动之时,那伙无赖的暴行到底还是殃及了无辜的路人,可惜了伊兵卫这个耿直的好人,竟化为那恶徒的刀下魂!我对不住你啊,伊兵卫!”
“说起来,也许我忠相才是幕后主谋,是我借别人之手把伊兵卫杀害了啊。唉,我犯下了无法弥补的过错……”
忠相狠狠地自责着,严格审视自己的内心,彻彻底底地斥责自己心中的疙瘩和阴影,在王法面前深深地低头忏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