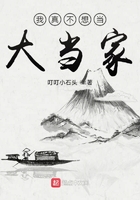“你们这是干什么!”张铁嘴见状直接从座位上站了猛地起来,双眼对驱开人群的士卒怒目而视,厉声质问道,明显,张铁嘴这个外号也不是白叫的,李文在一边看的分明,这个张铁嘴除了身体气的直颤外,脸上没有丝毫惧色,相反,却满面怒气的对着几个守城士卒嘶喊道。
“不干什么!从今天开始你去别处说书吧,近日城门戒严,闲杂人等不准逗留!”一个身穿黑色皮甲的军官从士卒后面走了出来,面色冷峻的对张铁嘴不冷不热的说道,手里做出了一个索钱的动作,同时,一脚蛮横踢翻了原本码放整齐的长凳和张铁嘴身前的桌椅,桌上的茶水顿时溅到了张铁嘴的脸上。
身穿皮甲的军官自然不是普通的军官,虽然军官身上的皮甲已经老旧的不像样子,但从他的穿着上看,至少也是一名百户,寻常的伍长和小旗是穿不起皮甲的,皮甲除了是一副甲胄,更是威严和权柄的象征,在战场上是军官们的第二条性命。
但!这是索贿,赤裸裸的索贿!无关乎战场,只关乎银子,这副甲胄如今变成了索命符,只需轻轻用力,对方便会在刀兵下无可奈何,屡试不爽。
“你······”
张铁嘴张着嘴想要接着说些什么,但最后只是咬着牙十分气愤的甩了下袖子,身子气得哆嗦,脸上一阵青一阵白。
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张铁嘴想斥说一二,但看着来人脸上的赤果又收回了话语,军官身上的铠甲和佩刀就像绳子一样死死勒住了张铁嘴的喉咙。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因为要索贿,所以才有了戒严,所以要砸他的场子,所以要把听书的人都赶到一旁,所以要强硬霸道。即使,戒严和说书风马牛不相及,甚至两不相干,但大明就是如此,没有任何权利,同时连反辨的理由都没有,只是简简单单的一句借口而已,但你却不得不服从。
索幸,守城的士卒和城管还是有些区别的,并没有伸手打人,当然,这也是多亏了张铁嘴身上穿的那件文士长衫,读书人不是谁都可以打的,至少他们这些卫所里的官兵不行。
“三贯铜钱。”为首的军官不痛不痒的掏了掏自己的左耳,随后缓缓拔出腰刀拄在地上,冷笑着将脸贴到了张铁嘴的身边,带着跋扈道:“交三贯铜钱,我们今后便不再来了!”
军官的脸上没有任何顾忌,反而带着些许的玩味,就像猫捉老鼠一样,十分自然而余又享受这种过程,全然不注意周围人群里异样的目光,相反,仿佛周围的人对他来说更像是蝼蚁,即使再多也不能伤他分毫。
“我没有钱!”张铁嘴拂了一下衣袖,气愤的回道:“你们要是索要黄白之物就来错了地方,我这里只说书,不派钱!”
说着,张铁嘴当着军官的面,将身前装着铜钱的瓷碗公然倒入了自己身上的褡裢,脸上的怒意又盛了几分,书讲的多了,自然不免多了几分傲气。
军官坑坑洼洼的脸上一愣,随后一阵失笑,继而抬起手中的腰刀试了试锋利程度,一阵冷笑,挥了挥手,看着周围围观的百姓趾高气昂道:“城里戒严,你竟然敢阻碍官兵,定是女真人的细作,来人啊!给我绑了押回去,仔细拷问,看一看这张铁嘴的嘴到底是不是铁的!”
军官身后的士卒立即将手中的长枪逼向了张铁嘴和周围围观的人,冷漠的枪头上泛着寒芒,若是被刺中一下定然会流血不止,围观的人群不禁纷纷后退了几步,眼神里也不再是鄙夷,相反却多了一抹浓浓的畏惧,就连刚刚几个听书的质朴农户都将头深深埋了下去,装作不认识张铁嘴,更有几个人甚至看着张铁嘴一阵指点,对张铁嘴强硬的态度一阵讥笑。
世事炎凉,莫过如此。
李文不是贤人,只是个闲人,一个看热闹的闲人,张铁嘴的遭遇固然让李文同情,但周遭围观者的行径更让李文隐隐有些畏惧,大明和现代社会终究不同。
李文对这种行为很反感,甚至从心里感到抵触,莫名从心里想到了哀其不幸几个字。
这是大明的常态,也是庆阳的日常,被欺压者连反抗的理由都没有,只能服从或者不服从,绝无反抗的余地,周边的听书人甚至没有一人敢站出来说一句公道话,只是惋惜的看着张铁嘴,随后继续看热闹,仿佛张铁嘴自身也成了一个故事。
这就是大明,每个人在一出生就被划分为官绅、农户、匠户、军户、灶户、窑户、和贱民奴仆,生生世世难以改变,就向一个金字塔囚笼,等级分明而又森严不可侵犯。在这一瞬间,李文突然觉得自己很幸运,同时也很不幸。
围观的人群纷纷向外退了几步,脸上带着深深的畏惧,只有李文十分突兀的站在原地,军官冰冷的看了一眼李文,仿佛李文一直站在原地也成了一个错误。
李文并非有意站出来,而是周围的人退的太快了,脸上也畏惧的太快了。
李文看了一眼周围,有些尴尬,因为此时李文已经成了所有人的焦点,在外人看来,李文是主动站了出来。
李文神情如故,并没有什么变化,仿佛站在原地并没有什么过错,只是微微拧了一下眉毛。
“原来戒严竟是这番模样,我也算是长了见识,呵呵……”李文在原地开口十分平静的冷笑一声,声音不大,但却十分清晰,语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刁钻,不留退路,是非曲直,李文一向分的很清楚,虽然他今年只有十七岁。
这与正义无关,只是因为李文觉得张铁嘴书说的确实很好,这样的普通人不应该成为被勒索的对象。
军官转头看着李文,眼神如同刀锋一般锐利,但却没有任何动作,只是阴晴不定的直直盯着李文,眼睛从李文的看上看到了脚下,不断地打量着,随后高声冷喝道:“你是哪家的少年,还不滚快回家去!”
“原来除了我家之外全城都要戒严,想不到竟是这样?”李文淡然回道,自然没有离开,相反却是真的吓走了不少看热闹的围观者,李文的脸上还算沉稳,眼眸黑白分明,只不过没有想到的是,对面的军官竟把自己当成了有背景的子弟,开口便问自己是哪家的。
“你又可知道勒索百姓是什么罪?”既然对方这么问了,李文自然不介意对方这么想,开口便是不咸不淡的问道,方才军官伸手要钱的场面许多人都亲眼看到了,李文指的也正是这件事。
军官显然没有把李文的质问放在心上,脸上却是更加阴晴不定,对着身边的几个守城士卒使了个眼色,随后,几个士卒持着锋利的长矛强行驱散了所有看热闹的人,只留下了李文和张铁嘴。
“在下百户王涛,还请教小兄弟是哪位大人家的公子?”军官对着李文拱了拱手,像条毒蛇一样紧紧盯着李文的眼睛,声音虽然称不上恭敬,但语气却缓和了很多。
面对手持兵刃的士兵能说出勒索百姓这样的罪名显然不是寻常人家的孩子,虽然百户在卫所里算是中级军官,但对于盘根错节的官场来说,却连小卒都算不上。
李文哪里还听不出王涛的意思,这分明就是在问自己的家世,如果自己的家世不能压服于他,那等待李文的就是或明或暗的报复了。
“刘良栋是我叔叔。”李文皱了下眉头,随后直视着王涛傲然道,“不日就要升千总了。”
叔叔,不是堂叔,也不是敬称,是父亲的弟弟,未出五服,血浓于水,亲情不浅。
王涛脸色一变,随后马上哈哈大笑,三步并作两步走了过来,抱着李文的肩膀笑道:“大水冲了龙王庙啊,贤侄,我和你刘叔叔是多年好友啊,都是误会,误会啊!”
刘良栋不是别人,正是上次来探望李文的百户,李文只见过一面,但李文通过那一面却知道,赵良栋就是下任千户的人选,有些事一次就足够了。所以,李文把刘良栋提了出来,因为他不认为对面的王涛会相信自己是真的‘李文’,而刘良栋是内定千总这件事又是一个卫所里几乎透明的秘密,所以李文将这个秘密摆到了明面,让王涛看了个仔细;这是个秘密,所以知道的人很少,所以刘良栋转眼间就成了李文的叔叔。
所以,自然而然,一炷香后,王涛带着士卒十分满意的离开了,李文地下深缓缓拾起未曾摔坏的茶壶和杯子,从嘴里吐出了一口凉气,擦了擦头上的冷汗,倒出依旧温热的茶水,仰头便是一杯,一旁的张铁嘴直直的看着李文,想了半天也没想出应该说些什么。
恰在这时,天香楼的大门被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打了开,牌匾上的红布也被二楼的伙计从窗口兴高采烈的摘了下来,同时挂上了数不清的彩色灯笼,不一刻,天香楼里便传来了一阵莺莺燕燕的笑声。
李文看了张铁嘴一眼,同样没说什么,只是把倒下的桌子摆正,将茶壶和杯子放在了上面,随后向天香楼走去。
“你叫什么名字?”张铁嘴忽的急促向李文问道,但一开口张铁嘴就后悔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因为这么问太不礼貌了。
“李文。”李文转过身看了张铁嘴一眼,想到同是读书人,于是报出了本命。
“李文···李文······”张铁嘴默念了几遍,总觉得这个名字有些耳熟,但又记不清楚到底在哪里听说过,刚刚他不是说他是刘良栋的侄子么,怎么不姓刘?
一阵秋风吹过,张铁嘴顿时感到身上冷的刺骨,连忙抱着身子打了哆嗦,看着城墙上缓缓落下太阳,这才反应过来原来天色都已经渐渐黑了,这一抬头,恰好看到了城楼上挂着的鞑子人头,心里登时窒息了片刻。
“李文,不就是杀鞑子的那个么。”张铁嘴不禁打了个冷战喃喃道:“原来真的是个凡人,比我还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