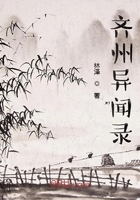转眼向晚竟在太子府呆了两个月,一场雪过,眼瞅着便要过年了。官离离找人修缮了漪方苑向晚和环玦住的地方,添了火盆木炭和其他东西,又给两人做了几身冬衣,眼瞅着也有了年节的气氛。
整整两个月了,向晚愤然停笔,狼毫的笔尖滴落一滴墨汁,在纸上晕开小小墨花。冻僵的手指冰冷,悬着的手腕酸痛难忍,纸上横七竖八地划了许多道。太子没过问过她的任何事情,算是默许了她住在这里,不必再回清心殿。整整两个月没见到那阴险狡诈的李承赫了。
漪方苑在太子府西北角上,离清心殿极远,离官离离住着的西苑还算近,向晚除却在漪方苑练字,剩余时间全在西苑,西苑桃花林中天然便是练武的绝佳之处。日子虽简单却极为充实忙碌,只是再没机会见到太子。
本就是不相干的人,何必相见,徒添烦恼。
向晚心中莫名火气,一甩手将手中毛笔丢进桌旁的青瓷大缸里,发出“咚”的一声闷响。环玦去了账房先生那里,还没回来,向晚心里烦闷,在屋里走了两圈,一脚把柜子门跺了下来。
两月前她一去南疆“千里寻夫”,外面皆盛传太子夫妻伉俪情深之事,老皇帝也颇为赞许,对太子态度极好,大事皆交由太子处理,对端王也渐渐冷了下来。朝中之人拜高踩低向来是拿手好戏,家眷们纷纷抱着礼物削尖了头往钟毓琉的憩梧阁钻。憩梧阁里的东西堆成了山,偏偏那钟毓琉生性淡静,不喜这些东西,隔三差五地便叫了向晚过去,向晚倒也不客气,吃人家的喝人家的,临走了还大包小包地往漪方苑里搬。只是向晚不知何时,竟与钟毓琉之间生了嫌隙,每每看着她端坐憩梧阁,心里没来由地酸楚。
“你这是闲疯了么?心情不好何必拿屋里东西撒气。”官离离声音泠泠如冰玉溅地,挑开挂着的暖帘进了屋子,一脚将地上的柜子门踢了出去。
“有什么要紧的,反正殿下有的是银子。”向晚背着手,没好气地从鼻孔里哼哼出声。“是么,殿下有的是银子,这谁呀还不舍得烧点炭火,屋子里冷冷清清的,是给殿下省钱呢吧。”官离离弯着眼睛笑着打趣向晚。
“走吧,陪我逛逛。”官离离皮肤本就白皙,今日又穿了妃色披风,上面用金线绣着桃花,妖冶绮丽,愈发衬得整个人娇俏好看。手里提着的镂空雕花琉璃宫灯,那琉璃灯光明亮,照的镂空花影映在地上,移步换影,走马灯般新奇。
“都什么时辰了,外面可不是刚下过雪……”向晚跺跺冻麻了的脚,嘴上虽那样说着,却还是挽着官离离的手要出去。“给你做的披风呢?外面冷着呢。”官离离摸了摸向晚身上的衣服,冬衣是新做的,里面夹着今年的新棉花,暖和极了,却还是不挡风,整个脖子全露在了外面。
“不要那个麻烦东西,我不冷,不穿那个。”向晚拢了拢散在脑后的头发,揽到前面想用头发来遮住脖子,可惜头发如锦缎般冰凉,官离离本就站在门边,一抬手掀开暖帘,一阵冷风吹进来,向晚忍不住直打寒颤。
“还不冷么,快去穿上。”官离离笑着,催促向晚从柜中拿出那藕荷色的披风,绣着和官离离一样的桃花,“桃花我亲手绣的,怎么样,漂亮吧。”
穿好披风,大大的风帽挡着向晚目光,只能看清面前一片地儿,雪还在细细密密地下着,脚下的积雪踩着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向晚听着好听,特意捡了雪厚的地方走,靴子不一会儿便湿透了。“别闹了,等下冻着了又要说殿下给你下药了。”官离离一手提着琉璃灯,一手扯着向晚拉回了廊下。
快过年了,廊下挂着有大红流苏的灯笼,满满地喜庆,向晚抬头,雪花在灯光下闪着灼灼银光,天地间一片皓然。
“去哪儿?”
“积梅馆。”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还没到那积梅馆,老远便闻到了逼人幽香。积梅馆里红梅多,衬着枝上晶莹白雪,树下琉璃灯花影,夜游果然别有风味。
“师傅喜欢梅花啊?梅花好,清极不知寒,还有如此扑鼻清香。”
“比起梅花,我倒是更喜欢桃花。”官离离笑笑扯着自己的披风,指给向晚看上面金线绣着的桃花,“桃之夭夭灼灼其华。春好,便盛开,风来,便凋零。顺时顺命,依赖着东君,若能如此一生,倒也不算辜负了吧。”
“和水上浮萍一样,飘到哪便到哪扎根。”
“恩,挺好。”
官离离走到一枝梅花下,随手揪了几朵开得正好的红梅,把手里琉璃灯交给向晚。“替我照着。”莲步轻移,官离离腰肢如水蛇,轻软却端庄,指尖夹着梅花,时而出现时而隐没,风雪反而都成了助力,托着她折腰扬袖,披风在身后不碍事,上面金线梅花在灯光照耀下影影绰绰,反而更添几分风姿。
早听说称水楼官离离一舞动天下,果然名不虚传,没乐曲相和,却生生用这舞姿让人听见人间仙乐。
“可还喜欢。”向晚正搓着手,冷不防手中灯被接走,一双温热大手将向晚的手牢牢包裹住,整个人被人向后一扯,跌进一个温热怀抱,那人温暖气息喷在向晚颈间,向晚眯着眼笑了。
“轻雪经年,这么兴师动众,只为你一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