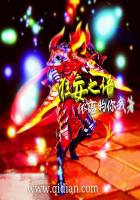?29 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
“我记得那个女的!”一跨进帐门,杨冲便嚷嚷着道。
花中寒怒火正炽,可听到这一句,不免也微微凝滞。
“我记得当初去血族找到你的时候,你好像正是和那女的在一起。”生性粗率的杨冲没有意识到什么不妥,大步上去转到他的面前,“我没有记错吧?花贤弟?”说到这里,他迟疑了一下,又道,“只是八年前的她好似比现在丰润一些。”
何止丰润一些,八年前的月?根本胖得多,哪里像现时这么憔悴瘦弱,一阵风都吹得走似的。他与朱月?的过往,在杨冲的面前是怎么也无法隐瞒的。花中寒阴沉着脸点了点头,没有否认。
“那你真的不管她?任她在外面冰天雪地里自生自灭?”杨冲身为大男人的天性无法坐视他眼睁睁看着一个弱女子忍受肉体折磨。
“不是我不想管她!”花中寒的舌头在挨打的那半边脸的方位抵了一抵,适才月?的这一耳光下手一点也不留情,直到现在脸上还是火辣辣的。而在场的所有兵士与将领此时围聚在外,都不知如何地在猜测揣度着他与那女奸细之间的关系呢,想想都火大,“你也看到了,是她自己不让我理她。”狠狠地一捶砸向身边的桌案,他咬牙切齿道,“那丫头,素来就是这么可恶的,再过一万年都不会变。”
“可是,”杨冲皱起了眉头,“她昨天被你刺了一枪,身负着伤,在这塞北风寒入骨的夜露中如何熬得过去?你不怕闹出人命?”
“不怕!”花中寒强忍着因想到这个可能而牵出的揪心刺痛,嘴硬地道,“是她自己找死,可怨不得本元帅狠心。”
“花贤弟……”
“好了住口!”终于决定不再因为顾忌情面而保持涵养,花中寒打断对方越来越扰乱他心境的唠叨,“本元帅军令已下,不可更改!谁再多言,便是藐视军令,以下犯上!”
“你……”想不到向来在他面前谦逊礼让的花贤弟这次为了个女子当真翻脸动怒,杨冲脸面上一时也很挂不住,但对方职位比他高,自小身在军营知晓尊卑军纪的杨冲虽心中不服也只能知趣地闭上了嘴,伸出食指对他指了两指,想回驳几句,却最终只是咽了口唾沫,甩手便往外走。
杨冲走到帐门前的时候忍不住又停了一停,丢下一句道:“随便你!反正人是你的人,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本大爷也懒得锳这浑水。”当身子已经在帐帘外的时候,又远远传来一句:“该死的,两个人都他妈一路货色,不识好歹!”
花中寒听到这最后一句,额头上青筋爆了一爆,最终还是按捺下来。
漆黑的帐中只剩下他独自一人,坐到自己的床铺上,怔怔出了一会儿神,他猛然站起来,走到帐门口想掀帘出去,可是,当手触到棉帘布的时候又停顿下来,缓缓地缩回,隔了几秒钟,再伸出手去,再停滞,如此反复几次之后,他突然有点赌气般地转身又回到床铺边,解开了袍襟,翻身睡入了被窝。
臭丫头,如此的不识好歹,活该自讨苦吃!说不理她,就不理她!
无法安然入眠。花中寒睁着眼睛睡到半夜,听到外面西北风呼啸得越来越狂野的声音,终于下决心地翻身坐起,穿上了外衣外袍,系上了狐皮披风。
走到营帐外,寒风迎面扑来,禁不住打了一个喷嚏。
遥遥地看到旗杆之下,月?果然被人依令捆绑在那里。头无力地低垂,长发披面。
向她走近的时候,想起多年以前同样的一个深夜,她受了委屈跑到骑奴宿舍来找他,穿得单薄,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的柔弱模样。那一刻,他是那样满心怜惜,特意拿了一件羊毛大氅为她披裹……
“谁?”值夜兵士看到有人靠近,紧张地喝问一声。
“是我。”
兵士迎着风灯看清他的脸,这才退后半步,恭敬地行军礼,“元帅!”为了邀功,又添上一句,“小的奉令看守女犯,没发现任何异动。”
花中寒此时的注意力只在那受缚的女犯身上,挥挥手,命他退下。
然后他缓缓地弯下身子,轻轻叹息:“朱月?,你还好吗?”
似乎看到对方的头颅轻轻转了一转,但最终还是没有抬起来看他。
“时移事异,现如今调转乾坤,你终于也落到我的手里,尝尝被人折磨的痛苦。”本该配上冷笑的话语,可花中寒此刻脸上挤出来的笑容却是一团苦涩,“想当年,我落在你的手里,的确曾经记恨过,想着有一天终要报仇雪耻……可是,后来经过了一些事情,早已不存这种念头。如今在战场上与你重逢,也非我所愿,无奈军令在身、父命难违……”
说完这几句,沉默良久,对方还是倔强地不给予半点回应。倔丫头,宁可冻死也不愿讨个饶吗?
花中寒叹了口气,解下身上的狐皮披风,如当年一样,轻轻地披裹上她单薄的娇躯。对方似乎打定主意不理睬他,仍没有抬头,可也没有把披在身上的衣服掀除。
似乎有所转机,他进一步道:“今日我本无意刁难于你,可你明知我的脾气,却还一再撩拨,故意掀起我的怒火……”他伸手,怜悯地拨开她披在面前的乱发,语气也越发柔和,“你永远都是这样,把身份地位和面子放在第一,真的宁死也不服软吗?”
突然,他的手指停顿,因为触到她的额上有异乎寻常的灼热温度。
“朱月??”他迟疑地用双手捧起她滚烫的脸,轻轻呼唤一声。
她的双目紧闭,小小的脸在他的手心里毫无生气,看起来竟是早已陷入昏迷。
“朱月??!”他有点焦急起来,把自己的脸贴上她的额,那灼烫的触感似乎能烧焦他的肌肤。
“月?!你醒醒!怎么了?”他惊慌起来,把她的头靠在自己肩上,而双手绕过她的身体解开了她背后绑在棋杆上的绳结,绳结一松,她整个人便直挺挺地倒入他的怀中,吃惊地发现她的身体与四肢居然早已冻得僵硬如冰。
“月?!”意识到自己玩得太过火了,他惊恐地紧紧将她拥在怀中,在她的耳边声声呼唤,“月?,你撑住,千万一定要给我撑住!”
“来人!”他扬声高唤,“快传医官到我的营帐来!十万火急!快!”
他抱起她,拔腿往帐中飞奔。就在这时候,却听到靠在肩头的月?轻轻一声呓语:“姓花的……混蛋!”
他一怔,连脚步也慢了下来。
“有种……你让我……死个痛快。”说完这一句,她的头一沉,再也没有了声息。
月?……你真的……恨我恨到这个地步吗?宁死也不愿被我所救吗?
他的脚步犹豫了一下,但也只是犹豫了一下,马上又重新飞奔起来。
来人!救救她!一定要替我救救她!只要能救回她,无论什么样的代价我都愿意付出!
对不起,月?……
只求求你不要就此死去……
为了让她快速温暖起来,他吩咐人在床边架起一圈火炉,再用棉布帘子围了起来,床上也加了两床被子,灌了几个汤婆子。
“怎么样?”
迎上从帘账后面出来的医官,花中寒神色间充满了担忧与焦切。
“受枪伤的部位伤口恶化,幸好天气冷,流的血都结成了冻,要不然失血过多后果不堪设想。但结的血冻与衣服紧紧粘连在一起,万不得已,下官只好将衣服剪开来处理了伤口……加上风寒入侵,深入骨髓……”医官轻轻叹了口气,“唉,下官先开几副药试试,如果见效的话,应该没什么大碍,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以后说不定会落下一些风湿的后遗症,阴天下雨的时候可能会闹个腰酸腿疼的,而且伤口的地方也免不了隐隐作痛。”
“哦。”花中寒心中内疚不已,“那就先开药方把药煎下去吧。”
“是。”
药方开出来,中寒吩咐手下小校前去煎炖。自己便掀开围在床榻前的帘帐,坐到了床边。
朱月?此刻仍是昏迷,睡在他的行军榻上,脸色苍白如纸。
他把手掌探上她的前额,依然是烫得炙手,再摸摸她的手,却是冷硬如冰。
月?,真的对不起。一直以来我都指责你任性倔强缺乏改进,事实上杨冲大哥那句话说得真对,我们两个是一路货色,经过这么多年,我也是死性不改的那个,心高气傲,倔强、不服输、要面子,一遇上你便针锋相对……
月?,快点好起来,只要你好起来,无论你是潜入营地的奸细也好、伤我义父的凶手也罢,我都既往不究,放你回去。就当把欠你的都还给你。
很快,汤药煎了上来,花中寒接过来,小心地舀起一勺,吹凉了,喂到她的唇边……
深黄色的汤汁顺着唇角流下,淌到了雪白的枕巾上。
花中寒一怔,忙取了一方绢帕替她擦净,再舀起一勺,这一次,动作更为轻柔,可依然不行,汤汁还是一滴不剩地全喂了枕巾。
“怎么会这样?!”他的心中升起无限的恐惧,“医官!你快来看一看!怎么汤药都无法喂进去呢?”
医官闻言进来,接过了他手中的药碗,同样是小心翼翼地喂食,却还是悉数顺着唇角全淌到了外面。
“怎么会这样?”花中寒抑制不住地感到慌乱,“是不是病情又有什么恶化?”
“先别急,元帅,让下官再看看……”医官把药碗递回给他,重新为月?把了把脉,然后又翻了翻她的眼皮,再掰开她嘴唇看了一看。
“怎么样?”花中寒追问着。
“从脉象上看来……这位姑娘除了身体的硬伤之外,似乎还有很深的郁结于心。”医官叹了口气,“以她的伤势和病势来说,应该还不至于严重到连汤水都不进。但是元帅你看,”他拉过他,再掰开月?的嘴唇,“她的牙关咬得很紧,以下官所见——似乎是潜意识里刻意拒绝服下汤药。”
“你的意思是她……自己求死?”
医官点了点头,“似乎是受了什么精神上的刺激,这位姑娘死志甚坚呐。”
怎么会呢?不就是跟他赌了赌气吗?何至于严重到如此?花中寒颓然而不解地坐下在床沿,“那么,如果她总是这样拒服汤药的话,就真的会……死吗?”
“唉!”医官重重叹了一声,“如果是她自己一心求死的话,就算是华佗再世,也一样死路一条。”
“砰!”
药碗失手打碎在地上。
“元帅?!”医官吓了一跳,“您……没什么吧?”
“没、没什么。”神情失魂落魄,花中寒抬眼看了看他,“你……先回去吧,如果有什么事,我会再差小校相请。”
“哦,”医官迟疑地道,“那……下官暂且告退。”
待他离开以后,花中寒猛然回头望向榻上女子双眸紧闭的脸庞,未几,眼角竟已一片湿润。
为什么你要一心求死?月?,到底有什么事情如此严重?只是与我赌气而已吗?
用你自己宝贵的生命来惩罚我无心的过错——朱月?,值得吗?
关于主帅与血族女奸细的神秘关联,第二天以各种各样的流言版本在木族的军营中迅速传扬扩散。
昨天晚上花中寒在营中大呼小叫疾速飞跑早已惊动了所有的人,只是大家识趣,都不敢立时跑出来鸡婆。
等到第二天一大早,便有很多人围堵着值夜的兵丁和小校们窃窃私语,连医官营也被人围了个水泄不通。
只是花中寒的大帐没人敢去窥视,但是大家也有目共睹,那个血族女奸细昨夜是休息在元帅帐中的,而花元帅本人直到日上三竿还未曾走出大帐半步。
最奇了怪了的是,血族那边也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免战牌依然还高高挂着。似乎这一场战役,两军主帅都有点心不在焉。
所有的副将都暗暗着急,营中流言四起,但流言毕竟只是流言,大家都不知道确切的真相到底是怎么回事,也很想弄清元帅此刻心中到底是怎么个想法。
他们之中大多数都是长年跟随花定洲的老将,论起辈分来都是花中寒的长辈,只有杨冲是与他兄弟相称的。碰上这种不知就理沾染了绯色的异端事件,长辈们都不好意思出面,唯众推杨冲去看看。
好在杨冲这个人生性粗爽,也顾全大局,倒并不因为昨夜花中寒的冲撞而怀恨在心。加上众望所归,便再一次挺身而出,来到花中寒的帐中。
进门,看到床帐中隐隐约约躺着一个人,又坐了一个人。两个人皆一动不动,似成化石。
杨冲虽是性格豪迈,但并不失聪敏,当他认出朱月?便是八年前与花中寒在一起的那个女子之时,就已经将他二人之间的因果猜得七七八八了。
适才也在医官处打听到,那女子似乎心存郁结,药食不进,而花元帅也因此失了魂魄一般。
此时进来看到这种情况,不由叹息一声,唉,问世间,情为何物?
听到动静,花中寒掀起帘帐,看到进来的人是他,想起昨夜自己好胜赌气,不识好心人的顶撞,而连累月?落得如此惨境,不免惭愧。他起身,迎出来,“杨大哥……”
杨冲察看他的脸色,才一夜的光景,已胡碴满面,眼睛充血。此时,纵然心中还有些许的余怒也都一笔勾销了。
“怎么样了?”他问。
看了看床内,中寒愁容又现,“还是那样,我不断地吩咐人煎药过来,可是,一口都喂不进去……”
“搞不懂这小妮子到底有什么难解的愁,为何小小年纪便如此想不开呢?”
“只希望……不要是因为我。”花中寒的声音渐渐放低,如果真的是因为他而搞出个三长两短,叫他下半辈子如何心安?
杨冲还想说些安慰的话,却听到帐外有人报禀:“元帅,我军探子回营,有要事禀报。”
“那快传进来啊!”杨冲一性急,逾权发令。话说出来之后才发觉有些不妥,有点迟疑地看向花中寒。
花中寒摇了摇头,“没关系,我本也是这个意思。”
无论内心再怎么焦虑不安心存挂念,也不能耽误正事,他不敢忘怀自己此刻所背负的身份与责任。
探子被召了进来,先跪地行了叩见礼。
“发现敌营有何异动?”花中寒问。
“卑职打探到,敌军主帅冯醉原本定于今日阵前完婚,迎娶狮部的公主千金,可不知其中发生了什么变故,婚事告吹,新娘失踪。如今,狮王与冯醉似乎都无心于战事,着急着寻人呢,所以这免战牌一时半刻未必能撤得下。如果我军趁机强攻或者偷袭,赢面很大。”
原来是这样……花中寒不由自主又看向围紧了帘幕的床榻方向,这么说来,月?昨夜会出现在这里真的只是误入,他错怪了她。
婚事告吹——原来她真的打算嫁给冯醉。可是,发生了什么变故导致婚事告吹?更导致她如今万念俱灰,一心求死呢?八九不离十是跟冯醉有关吧?
原本不希望她的痛苦是因为自己,可如今知道是因为冯醉,他又觉得心酸而失落起来。如果一切都是因为冯醉的话,那是不是证明在她的心目中最重要的人还是冯醉?
“怎么办?”杨冲也望向花中寒,看到他的失神,他对他此刻的心理活动十分了然,不由出声提醒,“我们要不要布置一下行动?”
花中寒回过神来,只是向那探子道:“你先退下吧。”
探子退下后,他又向杨冲道:“据我所了解的冯醉,不是这么公私不分的人,纵然身遭重大的变故,他也不会弃战事于不顾,不然也无法担纲一军主帅的重任。如果我们贸然进攻,只怕反中诱敌之计。”
“我看你是心存道义,不想乘人之危吧?”杨冲说得已经算是客气,“毕竟你与冯醉之间,也有一段旧日的渊源。”
他没说他此刻为情所困同样无心战事真的已经非常客气,但花中寒也听得出他言下之意,面色微沉,“杨大哥,我也绝不是那种公私不分的人,如若花某真的夹缠私情,便也不会让自己陷入这场战事,面对此种两难的境地。”
只怕你是身不由己,也心不由己。杨冲这么想着,却没有说出来,只叹了口气,“既然这样,我也不多说了,反正你是元帅,你作决定。”
他本是长平王反战派的人,一向不太热衷于这场战事的胜利,如今看到两军主帅皆为了一个女子而消及殆战,恐怕再耗下去,真如母亲所盼望的,这仗快打不成了。哈哈!人算不如天算,看来老天爷也是和平的爱好者呀。回去后得马上写封家信给母亲,把前因后果加油添醋地说上一说,让她也乐一乐。
这么想着,杨冲便又对花中寒道:“那个——其实我觉得,当务之急,你要先把那丫头给救过来,毫发无损地送回去,让冯醉欠你一个人情。”
“我当然是要把她送回去的。”花中寒接得很快,“只要她能醒过来,只要她可以好好地活着,我……我会把她送回冯醉的身边的。”
杨冲点点头,“那先这样吧,你也注意点自己的身体。”
花中寒也点了点头,迟疑了一下,突然又叫住他:“杨大哥!”
“唔?”杨冲此时已经走到门边。
“昨天的事……小弟要向你道歉。”
“嗨!”杨冲忙摇了摇手,“自家兄弟,偶尔闹点口角也是正常的,哥哥我早不放在心上了。”又抱拳一拱手,“告辞告辞!”
送走了杨冲,花中寒吩咐小校再热一副汤药上来,又回到了床边坐下。
床上的女子依然昏迷不醒,无知无觉。眼角下的月牙形冰蓝色花饰此时仿佛一滴刻入骨髓的泪痕。
“月?,”他轻轻叹息一声,“为什么呢?本该今日成为冯元帅夫人的你,为什么会以如此落魄的形状出现在我的营帐?”
他轻轻地抚摸她苍白而冰冷的脸,那原本如满月般丰润的脸蛋,如今瘦得脱了形。
“月?,这么多年,听说你与冯醉一直都在一起,所有人都把你们看成是一对了,所缺的只是一个仪式。我也猜到你们早晚都会完婚——不意外,真的一点也不意外。可是……他有什么地方让你那么伤心?连婚也不结,还要离家出走呢?月?,你何苦为了他而如此折磨自己?有什么不甘心不明白的事情,你醒过来直接与他理论好了,这样软弱地逃避着的你不像是我所认识的朱月?!知道吗?我现在很看不起你!”
小校把热好的药送了进来,中寒舀起一勺,送到她的嘴边,“月?,来,把药吃下去。不要让我看不起你,你一向是最坚强、最好胜的女孩,你要证明给我看,你要证明你是打不败的朱月?!”
没有用,药汁仍然还是自她的嘴角往外溢出来,一点也喝不进去。再喂几勺,还是同样的结果。
“喝啊!”忽然失却了耐性,中寒充血的眼睛里射出凶恶的光芒,他把她抱起来,让她的后背靠在自己的胸前,伸手捏住她的鼻子,把整个的药碗放到她的嘴边强灌,“喝!你给我喝!要死的话你也不要死在我的面前!你最在乎的人是谁?如果你很在乎冯醉的话,你就到他的面前去死!你要死也死到他的身边去!”
药汁洒了她满身满床,可怀中的人却依然半丝反应也没有,牙关紧闭。
他颓然地停了下来,把药碗往旁边一放,抱紧她无能为力地失声痛哭,“月?,求求你不要在我的面前死去!你让我怎么眼睁睁看着你在我的面前死去?”
依然是没有任何反应,他甚至以为她已经停止了呼吸,把她放下来平躺着,他胆战心惊地试探她的鼻息,在感觉到指间有微弱气流的运动之后些微松了口气。可是,这一缕微弱的呼吸还能够维持多久?如果她继续这样滴水不进,时间真的已经不多了。
看了看刚才的药碗,里面还只剩下大约两口的药汁。花中寒突然伸手取过,喝了一小口含在嘴里——好苦,真的好苦。
是甜是苦都一起尝,是生是死都一起承受……
他双手捧起她的脸,俯身向她靠近,在彼此的鼻尖只剩一线相隔的地方停了一停——没有办法了,现如今只能这样试上一试,月?,原谅我的冒犯——他将自己的嘴紧紧地贴在了她的嘴上。
一点一点地把药汁往她的口中渡送,不论多么的艰难,他都一定要把这一口汤药渡进她的口中。
一点、一点、一点……
终于成功了,她终于喝进去了这么一小口。
花中寒缓缓地吐出一口气,嘴唇顺着她的脸颊上滑,直滑到了她的耳边。他相信,此刻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她都一定能听得见。
“月?,是甜是苦我们都一起尝,是生是死我们也一起承受!这么多年,我从来也不曾忘记在血族的那些日子,也从来都不曾忘记与你在一起的每一个点滴。当年我并不是诚心要欺骗你,发生过的伤害我也再没有办法去弥补。但此刻我对你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发自真心——月?,不论你遭遇了什么样的挫折与伤心,不论你此刻是多么的孤独与困苦,纵然所有人都背弃了你,我也绝不会把你丢下。”他流着泪抱紧了她的身体,“月?,求求你,只要你能够活下去,我可以放下一切,就算对不起义父、对不起家国也在所不惜。告诉你一个秘密,华阿明一直都很喜欢朱月?,而花中寒也永远都不会放弃朱月?,就算真的要死亡,我也答应与你一起承受!这一次,我绝不骗你!”
说完,他起身又喝了一口汤药,向她口中渡去。
而同时,双目紧闭着的朱月?眼角也淌下了一行泪水,终于开始有了知觉。
*本文版权所有,未经“花季文化”授权,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