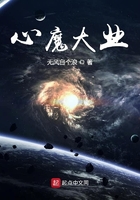榻上赫然坐了一名玉冠白襕的男子。
显是听到响动,他抬起头看向长流,修长的眉目带着一种异样的沉静与认命。长流窥见他的容貌,惊讶过后亦静静回视他。
“这就是殿下所谓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长流从他力持平静的声线里听出了一种压抑到极点的愤怒与嘲讽,一愣之下恍悟,他一定是对自己先前的劝诫误解了什么。长流已经从这几天京城过来的奏报中获悉韩毓科场舞弊案事发,却没有料到他本人会出现在这里,而且这桩案子竟然了结得这么快!
思索片刻后,长流轻声道:“他们是不是对韩大人也下了手?”一般只有犯官家属才会被罚没,女子为娼,男子入贱籍发卖。韩毓虽然已经考取功名,但还未正式入职,是以算不得“犯官”。如果罪名下达到他本人,最多跟前世一样被革去功名,永不录用,当不至于被发卖。因而除了韩大人亦遭到牵连之外,长流想不出还有第二种可能致使韩毓出现在这里。
“殿下何必明知故问。”韩毓的声音里带着一种彻骨清寒。
长流遂似笑非笑地道:“探花郎这是打算卖身救父?”如果真是这样,此人的性格倒是值得捉摸一番。
韩毓几乎将嘴唇咬出血迹,却仍是极力平静地道:“家父被流放三千里。还望殿下手下留情。”
长流方才就猜测他应该是自愿来的,因为没有被捆绑或是下药的迹象。她闻言即刻向他趋近几步,暗花如意纹素纱中单与他白襕的下摆紧贴。然后,她缓缓抬起手抚向他的唇,轻如梦吟:“不要咬。”
细白的牙齿却越发深陷入唇,沁出血珠。
感觉到身边男子的身躯在轻轻颤抖,长流忽然轻叹一声,将莹白如玉的拇指撤回,表情嫌恶地在他纤尘不染的白襕上抹了一把,明艳血珠即刻成了暗红色的污迹。随即她退开一大步,心不在焉地道:“探花郎还真以为自己倾国倾城。”心中却道:忍到这一步还未推开我,已是不易。此人动心忍性,是块值得雕琢的美玉。
长流在一旁太师椅上坐了,轻声道:“还不从本王床上滚下来?”
韩毓显然对她一连串的言语动作猝不及防,好半晌才僵硬着身躯站起,忽然跪在她面前,道:“肃卿任凭殿下处置,还请殿下放过家父。”方才那一刻他才恍悟,眼前这名眉目沉静的少女其实并未对自己有丝毫的动情,那么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报复?因为太女殿下抢了本该属于她的皇位,所以齐王便设计夺去太女的驸马,好叫她颜面扫地?
以字自称,这是服软了么?这书呆子怎么就一根筋到底,认定了此事是本王所为呢。长流忽觉一阵气闷,站起来推开窗。
夏日悠扬晚风扑进室内,将烛火吹得飘摇。
韩毓见她一身素衣在栀子香风中摇曳,不由想起初见那晚。他不禁自问,如果不是当初见过她一面,他还会做出今晚这样屈辱的选择吗。
“起来吧。韩大人的事本王会想办法。不过你就……”韩毓已经没入贱籍,即便日后能将此次舞弊案推翻,韩毓本人的声誉已然大大受损,想让他重新站上文坛恐怕很难。
韩毓却仍是错解了她的意思,轻声道:“肃卿谢过殿下。肃卿甘为殿下驱策。”
这本是长流想要的结果。是以她明知在韩毓身上会发生什么,却仍然选择袖手旁观。一则,她想要他从此站到自己敌人的对立面去。二则,让他受些挫折,打磨一下心性未尝不好。但是此刻,长流不免有些啼笑皆非。显然目前为止,韩毓对“驱策”这个词的理解并不是她原先所希望的那样。
“这件事并非本王所为。本王对太女殿下的驸马没有丝毫觊觎。不过太女殿下就未必了。”长流的语调很平淡。
韩毓猛然抬头道:“殿下是说太女殿下因为不想嫁我,所以……”今晚来此之前,他虽然做好了抛弃一个男人所有尊严的准备,但潜意识里还是那个骄傲的跨马游街的少年。当从下朝的父亲口中听到消息的那一刻,韩毓并未欣喜若狂,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仕途只怕是到头了。但下意识里他亦是自豪的,毕竟他要娶的是大禹最高贵美丽的女子。他不是没有听闻过太女与齐王未婚夫之间的流言,但他以为那不过是些无聊人的捕风捉影,而皇上金口玉言当堂宣布他为驸马就是这件事子虚乌有的最好证明。不过,韩毓并不认为长流有必要骗他,她是那样骄傲的一个人,承认自己的未婚夫与亲妹妹有染,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长流这才转身,看清韩毓面上浓重的失落和自嘲,轻声道:“你起来,说说整件事的经过吧。”奏报毕竟不够详细,还是从当事人口中了解比较妥当。
“是。”
韩毓依言缓缓起身,在一旁坐了,轻声道:“整件案子的起源是监察御史上疏说家父与本次会试的主考官文华阁大学士郭毅过从甚密。其实不过是郭大人嫁女儿,家父前去喝过一杯喜酒。当时朝中官员前去恭贺送礼的人极多,本不足为凭,却偏偏只有我位列三甲之一。而且时机不巧,喜事恰恰是在郭大人被任命为本次春闱的主考官之后。陛下回复此事牵涉驸马在内,需得细细查访,还驸马一个清白。哪知道大理寺草草将郭大人过堂之后便坚称郭毅或有出于同僚之谊向家父泄露考题。陛下震怒之下将奏折留中不发,命大理寺开堂重审,维护之意十分明显。熟料此时恰好暴出参与殿试的二百零八名生员中竟然有一名同进士在醉酒之后吐露事前买到过考题。此人当即被刑部羁押,在早朝时被押解上殿,由皇上亲自出题,此人张口结舌答非所问,确系不学无术之徒。陛下龙颜震怒,之后家父与郭大人都被判了流放,而我本人以莫须有的罪名被革去功名,以‘犯官’家属身份没入贱籍。”他的声音虽听似平缓,但捏紧红木椅子扶手的右手骨节突出泛白,血管暴起青中带蓝,显然是在极力克制情绪。
长流点点头,这些与她得到的奏报大致上并无出入。郭毅算是****棠的学生,当年****棠做主考官时,郭毅得了一甲第六名,其后仕途一帆风顺,直至官拜大学士。如果长流猜得不错,这件事本来就是柳青纶这个老狐狸为了扳倒****棠设的局。但凡御史参劾都是先咬住一人不放,然后等着他背后的支持者主动站出来维护。****棠如果维护郭毅,则正中老狐狸下怀,如果不维护,他在朝中的声望亦不免会受到影响。本来这件事可能不会牵涉到韩毓,不过谁让他是皇帝老爹安排给随波的乘龙快婿呢,芝兰玉树又怎样,谁让你那么没有眼色,正巧长在人家大门口,正好一并除去。皇帝老爹多半本想保住韩毓,毕竟是他钦定的驸马,倒了的话有失颜面,但事涉****棠,权衡再三,才最终决定丢卒保车。而且好就好在虽然朝议已定,但明旨未下,天下百姓还未及闻讯。而老狐狸果然见好就收。双方为免夜长梦多,案子从审理到结案堪称神速。所谓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好好一个探花郎一夕之间沦落为奴。至于他前世还不至于这么倒霉,恐怕因为如今随波已被立为太女,情势已有天壤之别。
只是个中曲折阴暗,韩毓还未入仕,凭他这颗塞满四书五经的脑袋,只怕暂时体悟不了,不然这呆头书生也不会以为是自己因为觊觎他的美色而使的手段了,是以长流并不打算将这番结论同这头牛说,只问:“后来呢?”
韩毓明白她这是在问自己后来的遭遇,遂答道:“后来我就被发卖。一路日夜兼程坐船南下。直到今晚才知道要……的人是殿下。”他终究说不出“服侍”这两个字来,只含糊带过。事实上被发卖的过程根本不若他口中如此轻描淡写。他快要弱冠,以小倌来说未免年纪太大。是以虽然韩毓的相貌无可挑剔,但南风馆的人根本看不上他。有权势的人家本也有喜他才名的,但碍于事涉朝堂争斗,无人敢接手。极尽屈辱之后,韩毓才落到屠宪的手中。一路上他想了各种办法自裁,却因为看守防得紧,都没有成功。
长流因路上遭到漕帮追杀,耽搁了行程。又因为随行人员众多,一路上补给物资,停靠码头又延误了不少时日。而且长流的大船走的是大运河,韩毓的小舟却是从支流绕的近道,反比她早到片刻。
“肃卿身上可有伤?”他本来官话说得极好,今晚却有几个字发音不甚准确。
韩毓沉默不答。
那便是有。长流轻叹一声,正待叫人另行安排他食宿,却听到院中起了争执,其中一个声音是江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