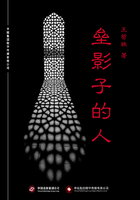这是一个性病患者对妻子的忏悔书:
芸芝:
我走了。
我走向你曾气愤地诅咒过我要去的地方。
但是,在上路之前,我觉得两条腿像灌了铅,好沉重啊!整个身子像背负着什么。不,像压着一座山。不不,是十字架,是罪孽深重的十字架。
我知道,你如今恨我,恨得简直七窍生烟,恨不得一刀宰了我!
可是,我不怪你。
我不认为你性情不豁达,也不以为你不珍惜你我夫妻一场的情份。
你是一个严肃的女人,一个白璧无瑕而自尊心极强的女人,又是一个漂亮得曾令我发狂的女人。
你恨我,完全证明你对我爱得认真,爱得专一。
不是有人说爱情是自私的吗?
我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三年前,当我在越秀亭下与你见面时,我的两只眼睛都直了,好像眼珠都不会转动。
当时我以为,大概是我的眼睛发花了。心里也暗暗自语:这个美女是朋友给我介绍的对象吗?不会是骤然下凡的天仙吧?
只见你修长的身材穿一件雪白的连衣裙,在夕阳的余辉下闪金亮银,放射出迷人的风采,令我眩晕,令我陶醉。我瞪大眼睛望着你,一时竟不知如何开口。倒是你当时那种落落大方,不卑不亢,那种摄人心魄地微微一笑以及一句:“你好!”把我的魂儿才拉了回来。
当时我的心是十分矛盾的,我既为能有你这么一位漂亮的姑娘而兴奋,又为自己条件差而自惭形秽。我不但长相平平,工作也很一般,论职务只不过是一个不足百人的街道工厂的副厂长。那时,我觉得你是个高傲的公主,而我只是个貌不惊人的仆人,两个人的距离相差十万八千里!
可是,我成功了。
我骄傲地得到了你,就像获得了一件价值连城的瑰宝。
我多么自豪啊,觉得俨然变成了王子。
我是凭什么征服你的?
不否认,凭我的穷追不舍,凭我的大献殷勤,也凭我的一些小小的手腕。但是,我也明白,更重要的还是你不重相貌,不重门第,不重地位的高尚与单纯,还有你对爱情的美好期冀。
还记得那个令人心醉而又令人心颤的新婚之夜吧。那天晚上,你静静地坐在窗幔旁,轻声曼语地问道:“你真的爱我吗?”
“爱,当然爱。”我连声回答,脑袋像个啄米鸡。
你听了淡淡一笑:“我是说,你会不会永远爱我?”
我发誓赌咒地表白:“我一辈子爱你,海枯石烂不变心。”我觉得这还不够,为了证实我对你爱的程度,“咕咚”一声跪在你面前,拍着胸脯说:“我要是除你之外再与第二个女人好,就天打雷轰!”
谁知,我的誓言还没过三年,就变成了空话,假话。
往往一个人完全得到了的东西,也便不再十分珍惜了。慢慢的随着我的官运亨通,我开始喜新厌旧,寻花问柳。
我也明白,这种荒唐的行径不仅被世人所不齿,而且也是对你的爱情的亵渎与背叛。
可是,欲海难填哪!
不久,我因乱搞两性关系蹲了几个月的班房。
不久,我发现染上了性病。经医生诊断,梅毒已达二期。
你知道后,气愤难耐。
你骂我,诅咒我,并且说永远不再见我。我都理解。
因为我是个十足的负心人,是个现代陈世美。
我知道,大凡梅毒患者是难以治愈的。即使治好,留下的丑恶疤痕也无法去掉,一半在身上,一半在心灵。人到悔时才知晚哪。既然如此,何必当初呢?!
我也知道,我无论再怎样做都难以补回我欠下的你的债,也难以得到你的饶恕。
我已选择了自己的路。
我应该朝着这条路走去。
我已托朋友搞了几包TNT炸药,准备天打雷轰般将自己炸个血肉橫飞,以此来实现誓言,同时也彻底清算自己的罪责。
芸芝,我走了,我是带着深深的自悔而走的。
我走得很匆忙,因为我毕竟还不到四十岁。
本来我是没资格向你说“再见”的。但我还是想说一句:“再见啦——芸芝。”
断想录:一份忏悔书,一串辛酸泪,一张死刑宣判公告,随之是自毙的“爆炸声”。那情景,可想而知,是惊天动地,是血染天宇,是碎骨如尘,是令人不寒而栗。然,“爆炸声”响过,“硝烟”会立刻荡然无存吗?在被唤作“芸芝”的内心深处,在自毙者父母及亲朋好友的脑海,还有在得知此事的人们的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