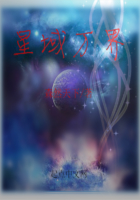10
阿笙留下处理现场,范丞曜与葛薇兰上了另一部车,沈小雨亦上了车,她吓得说不出话来,脸色苍白,她想恐怕这一生也忘不了今晚,让她如此心惊胆战。车子开到公馆,斯密思冯已在公馆等候,今次他带了一个小护士。
麻药已经上好,范丞曜被挡在门外,斯密思冯说:“我要为她取子弹。”
“斯密思冯你总要信得过,放心,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众来人劝他。
范丞曜坐在沙发里,他现在只觉得一团乱麻,头埋在双手中,心里说:“我情愿是我挨了那一枪。”
后来斯密思冯出来,范丞曜迎上面。
他面带微笑,说:“子弹已经取出来,没有什么危险,只是她失血过多,可能会引起昏迷。不要吵到她,让她多休息。”
范丞曜这才放下心中大石,沈小雨地看了他一眼。范丞曜觉得内疚,是他让她牵到这场事件之中。
斯密思冯又嘱咐几句,范丞曜让人送沈小雨离开。
她安慰他说:“她一定会没事。我一定会让家父尽快回来处理这件事情。”
范丞曜点了点头。
沈小雨说:“我终于明白你为什么不接受家父的安排。”她伸出手来说,“祝你幸福。”
他说“谢谢。”
她幽幽地说:“我多么羡慕她,希望也能遇到位像你这样的男子。”
范丞曜轻轻地推开房门,坐在葛薇兰的床边,看她双目紧闭,他用手摩挲她的脸,低声说:“你吓死我了。”他笑,却不知不觉掉下一滴泪来,他又笑了,把头埋在她颈边的被子上,像小孩子似的擦眼泪。他说:“等你醒来,我再与你算账。”
他在她床边蹲下来,为她打理头发,问她:“你明日想吃什么,我让黄婶做给你吃。”他明知她听不到,依然一句一句问下去。她似她真的会回答他一样。他舍不得离开,便躺在她身侧,小心地不碰到她的伤口,“我发誓,再也不会让你遇到这样的危险,永远不。”他一遍一遍地看她容颜,似永不厌。最后他亦在她身边睡去。
阳光透过窗台照在范丞曜的眼睛上,他睁开眼,已是第二日清晨。他拉上窗帘,俯身用手摩挲她的脸,他对她笑,她还没有醒来,他为她拉高了被子,转身出去,让她安静休息。
那****没有出去,耐心等她醒来,他有许多话对她说,只能对她说。
他每隔一个时辰进来看她一次,伸手摸她的脸,这个习惯养成了可不太好,他暗自笑自己。每次她都在睡,他笑她,“你到底还要睡多久?”直到下午两点左右,他再次进来的时候,发现她的脸异常的烫人,他变了脸色!轻轻摇她,“兰,兰!”她竟毫无反应。
范丞曜打电话给斯密思冯,他发现自己的手在发抖。子弹不是已经取出来了吗?他叫自己镇定下来,竟有一种无助的感觉袭上心头。他害怕!他怕她永远都这样,像睡美人一样永远不醒来。
斯密思冯为葛薇兰检查了一次,没有什么异常,说:“没什么异常现象。”
“她还会昏迷多久?”他问。
斯密思冯不敢断言,只说:“她可能出现了重昏迷。”
“什么意思?”
“这是一种并发症,我之前也有病人出现重昏迷。昏迷的时间长短不一,不过如果病人一直处于这种状态,必须输水才行,以维持身体所需。”
她自那日起睡了六日,傍晚的时候,范丞曜坐在庭院的藤椅上,他近日越来越喜欢坐在这里,因为她喜欢在这里吃早餐。月升而日落,他坐了良久,想着,若是葛薇兰现在在他身边,或许她会端来水果,说一些小时候的趣事。他微笑。若是他那日没有受伤,他们会不会见面?会,他们会遇到。他相信。他微笑。他握着那半块的吉祥,是他们专有的定情之物。他想起她那时说:“坦白说,我还蛮内疚的,因为那结也许并不值什么钱……你知道结草报恩这个成语吧,所以我才会那么努力地想要爱上你……”
无论如何他是那么感谢上苍,带她来到他生命中,她因吉祥结思念过的人是他哦。她要他一生一世不娶别的人。
他笑起来,觉得眼角一热。他在心里祈祷,我只要她醒来,其他什么事都不重要。这些日子他深思熟虑,想起已去世的父亲。也许他说得对。他在树下祷告,像个虔诚的信徒:“我愿放弃最珍贵的东西,只愿你醒过来。我放你四海去遨游,纵然不在我身边亦无所谓,我要你好好活着!”他这生最珍贵的东西——唯有与她的感情。
这时风吹过藤蔓植物,一切哑然无声色,他站在那里,似座火山,表面积雪千里,内心却汹涌澎湃。范丞曜走向葛薇兰的房间,他想明日也许可以给桑桑发个电报,兰说不定喜欢见到她。
他推开房门,她依然在熟睡,他低声说:“你醒过来吧,我拿我最珍贵的东西与你交换。”他在她脸颊上一吻,“我答应你,永不娶别的人。”他抬头看她,似要烙下烙印,觉得喉咙发酸,他说:“我要你好好活着。”
桑桑自北平来,她见到葛薇兰掉下泪来,她依然住在霞飞路霍家别院中,今次,葛薇兰自青玉巷搬到霍家。范丞曜没有阻止,他一开始就应当有自觉,像他这样的人,不该爱上任何人。他每日去看她,独坐并不说话。
她终于在半个月后醒来,那日范丞曜刚要踏进房间,就听到桑桑叫她名字。他在门外屏住呼吸,再迈不开脚。他再也没有理由每日去看她。他再不去看她。
他每日上码头办事,日日不休。阿笙问他:“你当真不去瞧她了吗?”好像他多无情啊!她因他而伤。
那日,阿笙与他一起回公馆,喜凤说:“葛小姐来过了!”
范丞曜莫名地揪心,阿笙问:她“说些什么?”
喜凤摇头,“少爷不在,她就走了。”
他与阿笙开怀畅饮,酒入愁肠化作相思泪。阿笙问:“你当真不去瞧她了?”
他比谁都想去瞧瞧她,他想见她,他含笑说:“阿笙,我很小的时候家母就已离开上海。”
“这个我知道。”他听人说起过。
“她与家父离婚,其实家父并不是不爱她,”他陷入回忆,“家母离开之后,家父曾对我说过一句话。”
他想起他那时年幼,除夕夜的时候,拉嬷嬷去看烟火,他玩得尽兴,直到子夜才被嬷嬷劝回。他路过父亲房中,他正在拉二胡,伊伊呀呀地拉着。
“爹,你怎么哭了?”他抬起眼问他。
“今是除夕,爹高兴啊!”可是他明明那么不快乐,他为他擦泪。
“少华,将来若你遇到自己真心喜欢的女子,远远看着便足矣,动不得真情。永远也不要妄想娶她入门。”
“为什么啊?”
“你长大了就明白了。”
阿笙说:“他大概是伤心过了头。”
“我以前也是这样想。”范丞曜趔趄地站起来倒酒,“阿笙,我爹说得没有错。”多么无情的话啊,永远也不要妄想娶她入门!他如今总算体会到那种感觉,情到浓时情转薄!他要做那个无情的人,藏起对她的浓情眷恋。他从今往后,要做个无情的人!
“我要她好好活着,找个值得依靠的人做丈夫,一生幸福。”
“跟着你难道就不幸福吗?”阿笙不懂这其中的道理。
他笑,“我们有什么幸福可言。”整日刀光剑影,连他都累了。
“曜哥,你醉了。”阿笙去扶他。
“阿笙,我与你讲,我真的爱着她,若是她不在身边,我会觉得干什么也没有意思。”
阿笙猛地清醒过来,“曜少,你醉了。”
“我想让她待在我身边。”
阿笙平淡地说:“把她接回来?”
范丞曜摇了摇头,笑得凄凉,“她就像云,在半空之中,我们就像湖水中的鱼,她在我们的世界生存不了。我要她好好地活着。”他又倒了一杯。
阿笙抢下他的酒杯,“华少,你真的醉了。”他扶他上楼休息。
范丞曜第二日在头痛中醒来,他揉揉头,下楼让喜凤泡解酒的茶。他看到阿笙,“怎么这么早?”
“我昨日睡客房。”
他忆起他昨日与他对饮。范丞曜笑道:“好久没有这样与人喝到痛快。”
“你昨日醉了。”
“是吗,记不太清,对你发酒疯了?”他笑,阿笙觉得那笑更让他难过。
“你当真什么也不记得了?”
“记得什么?”他反问他,“对了,昨日姚叔的货运过来了,今日记得去点清楚。”
“华少。”
“嗯?”
“昨晚,葛小姐来过。”
他怔了一怔,极力保持原有的表情,装作不在意地问:“什么时候?”
“我扶你上楼之后。她说……”
“什么?”
“她要与霍太太去南洋。”
噢,那云终于飘走了!他的心向下一沉,“什么时候走?”
“明日中午。”
阿笙与范丞曜开车到火车站时,葛薇兰与沈月红正要进月台。他终于还是说服了自己,他想要与她见面。他远远地便瞧见了她,她比之前更加清瘦了些,生了那么大一场病。阿笙上前去打招呼。
葛薇兰对他微笑,范丞曜觉得自己撑不了多久,他有种想拥她入怀的冲动。他对她说:“我很抱歉。”
“如果你是说受伤的事,大可不必放在心上。”
两个人说些不相干的事情,似有默契,绝口不提感情。
“怎么想到要去南洋?”
“霍先生去了那边,他催桑桑过去已催了好多次。”葛薇兰笑,打趣地说,“他们感情较好,一日不见如三秋兮。”这句话陡添尴尬,好似他们感情不好似的。
他淡淡地笑,心中千疮百孔,揪得人发痛,“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她抬头看他,“也许,永远也不再回来。”
他真的没有开口留她,葛薇兰心想,若是他开口,她一定会留下来,可是他没有。
范丞曜看着她与桑桑走入月台。
“若是她不在身边,我会觉得干什么也没有意思!”
范丞曜与阿笙坐在车里,听到火车离去时轰隆隆的声响。南洋,隔了何止千里!
他们终究像两条平行线,偶尔意外地交叉了,可是那线还要无限地沿长下去,交错的结果不过是越行越远,比以前更加遥远的距离!
葛薇兰望着窗外,桑桑说:“这个人真是无情,一场变故,所有的事情都淡了一样。到底是虚情假意。”
葛薇兰流下了泪。他们到底还是没能在一起,经过了那么多风波,以为早已心心相许,以为可以这样一直到老……
到底还是没有在一起。
手指深深掐进肉里去,手里是那半块吉祥结。
PARTI
“薇兰,你整日在家不发霉吗?要不要找点事做,或是找个学校念念书什么的。”
“好哇,我去念书,有些什么学校?”
“南洋女子学堂?南洋联合大学?”
“南洋女子学堂,这个不错。”
PARTII
“薇兰,那边那个频频瞧过来的是不是你同学?”
“哪个?月红,你眼花啦?我读的是女子学堂。”
“那他是谁?”
“哦,是瞧着眼熟,是徐穆学长!”
“你怎么知道他名字?”
“当然是我认识他才知道他名字。”
PARTIII
“薇兰,你今日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哦,学长约我吃饭。”
“哇,他当真追你。”
“你这是什么表情,你不是巴不得我早点嫁出去?”
“她今日去了南洋女子学堂。”
“她今日与霍太太去公园遇到了李肖生,他似乎对葛小姐有些倾慕。”
“今日徐穆约她吃饭。”
电话那边总是公式化地说着她的行踪,“她去了吗?”他问。
“嗯,去了。”电话那边回答。倘若她身边有一个爱着她的平凡的男子,她与他一起生活,相夫教子。他以为他会开心,今日听到竟如晴天霹雳般让人震惊。
范丞曜从书房走到庭院,他坐在旧藤椅上,为何他今日竟有一种被人遗弃的感觉。她要开始她另一个全新的生活,是否她也会踮起脚来,在那人的脸边印一个甜吻?是否也要那人终其一生,只爱她一人?她是否已忘掉了他?月光如水温柔地照在庭院里,他记得她的每一个浅笑,每一次转身。他思念起她的发,思念她衣角暗暗传来的属于她的香味。这满心的惆怅如那深邃的星空,漆黑一片,无边无界。
银色月光倾泻在上海的庭院,亦照在南洋她的窗台。
“怎么还不睡?”桑桑推开葛薇兰的房门,她正站在窗边,“想什么?”她似抓到了她的小辫子,问道:“你今日与徐穆谈得如何?”
“哎,他在联合大学新闻系里任职,业余爱好是画画。他身高为一米七八,体重六十公斤。未婚,家里父母健在,有一个哥哥,一个妹妹,除了上课,他……”
桑桑做了个打断的手势,“够了。”
葛薇兰格格地笑,“这些不是你想知道的吗?”
她与她并肩站在窗边,葛薇兰正色说:“桑桑,你知道我在哪里认识徐穆的吗?”
“哪里?”
“上海。”她凄凉地说,“桑桑,我想回上海。”
“为何,这里不开心吗?”
她摇头,“我忘不掉他。”
“我以为你已忘掉。他负心于你,你何必还念念不忘?”
“不是的,他深爱着我,我知道。那日去青玉巷,我听到他与阿笙的对话,他是为我好,他要我离开他身边,是不希望我再受到伤害,他总是那么独断专行,他为什么不问问我的意思,又凭什么来安排我的人生,他凭什么要赶我走?”
“我还以为你早已想开,离开了也好,过去的事,薇兰,你忘掉吧。”
“我也以为我能够忘得掉,”她抬起手来,月光下,仰头看那半块的吉祥结在风中打着秋千。他手中有我的一半,另一半在我手中,她喃喃:“我又如何忘得掉。”
徐穆终于向她开了口:“可还记得我那时说过的话,若是再相见,我单身,你也单身,我们试一试吧。”他轻轻地握住她的手,“薇兰,可愿意嫁给我?”
她怔住,问道:“你可有一点喜欢我?”
“薇兰,我喜欢你。”
“你应当早些告诉我。”
“薇兰,我怕你拒绝我。”
“比我好的女孩子太多,你将来总会后悔。”
“我绝不后悔。”
“那你要答应我,你不许爱上别的人,要一心一意待我。”
“我答应你。”
不对,不对,他的对白错了,他应当说:“一心一意待你,这辈子只娶你一人,不娶别的人。”葛薇兰突然掉下泪来。
“今日徐穆向她求婚。”
求婚?“她答应了吗?”
“似乎是答应了。”那电话无声无息地从他指尖里滑落,他这不是如愿以偿了吗?怎么会不开心?这次他该要永远死心了。
他把书房的陈年旧物通通翻出来,红色的流苏,白色的玉兰花,那是什么时候的事啊,她带着吉祥结,在他面前盈盈浅笑。
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
1928年的冬天,大雨淅淅沥沥地落了下来,晚上起了雾。范丞曜坐在大都会三楼的义厅。中华慈善会的人正拍买着前清的古玩,玉如意,金琉璃。再也没有吉祥结了,此只一对,在他生命的某个时刻出现,如昙花一现。范丞曜慵懒地坐在角落里。
管事探进头来,向阿笙招了招手。他在阿笙耳边咕哝了一句。
阿笙惊叫:“怎么可能!
”范丞曜回过头来。阿笙走过去也与他低声说了一句,他从椅子上跳了起来,“什么?”
大都会今日收了新的舞女。领班带着那个新来的舞女站在范丞曜面前,她低着头,他抬起她的头来,她的泪珠滴落在他的手背,像从前一样。他紧皱着眉:“葛薇兰,你怎么会在这里?”要他怎么相信,她应该在南洋,她不是已经要与徐穆成婚了吗?
她不答,只是默默地掉着泪,他失去了耐心,“你怎么会在这里?”
她哭得惨烈,说:“他说他一心一意待我,还不是把我抛弃。我在南阳待不下去,才回了上海。”
他气极,他疼在手心中的宝贝,哪里容得下别人来糟蹋。
“怎么办啊?”
他拥她入怀,以安她心,那温柔发丝犹若昨日,他竟有些恍惚,“那你搬到公馆来住吧?”他说。
“可以吗?”
“可以。”
一个月后。
“薇兰,你怎么会在这里?”
“徐穆,你怎么回上海了?”
“哦,家妹新婚,回来道喜。”
“今日结婚的是你妹妹,真是恭喜哦。”她突然打住,心里大叫糟糕。
“兰。”他在叫她。
葛薇兰突然拉着徐穆转了一百八十度,“改日再聊!”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徐穆?”
“范先生,没想到回来还能见到你们,恭喜你与薇兰有情人终成眷属。薇兰不答应我的求婚,今日见到,若是输给你,倒也算心服口服。”
葛薇兰不断向徐穆使眼色,可是他完全未见。
以范丞曜的脾气,他应该再不理自己转身就走吧?不对哦,他竟礼貌地与徐穆说谢谢。她没听错吧。原来他亦学聪明了,学会与她秋后算账。例如现在——
“我哪有骗你?”她犟嘴。
“你说他对你始乱终弃。”
“对啊,我又没说徐穆。”她不满,用脚指头想也明白,那个人是他范丞曜。
“那你还说你在南阳待不下去,才回了上海。”
“对啊,你又不在南阳,我去哪里找你。”她小声嘀咕。
她知道他生气了,可是那又怎样,她正好用一生一世的时间与他好好周旋。
她当他真的生气,她当自己一时聪明,终于骗过了他?哪知她回到上海他便知一切,只是心甘情愿与她对戏。因为他亦有私心,想要自私一次。就算知道前路不可预料,但是还是想拥她入怀。
“薇兰。”
“嗯?”
“我不能向你保证再没有什么风险,我只能说我会努力保你平安。就算丢掉生命也在所不惜。我会让你幸福。”
……
就算破碎,不那么完整,吉祥结总要一对才够圆满。
—本书完—
*本文版权所有,未经“花季文化”授权,谢绝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