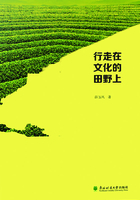很多个日夜之前,我就打算为我的父亲写点什么东西。譬如,平淡至极地写写他曾如何带着我去奔越一座又一座崴嵬的高山,写写他在随时光消逝之后我尚能记起的一些旧事,写写那些曾如江水一般汹涌奔流又回眸不见的泪水。
我曾是那么迫切地想要为此落笔,想要把满腔的愁思,怨恣,都一并宣泄在惨白的稿纸和寂寥的月上。可挣扎了上千个日夜后,我始终还是没能把胸膛中的那些情愫整理清楚,逐一理顺。
它们像缠绕了千年的青丝,细切杂密,疙瘩交错,纵横百里。
我的父亲是个酒鬼。从始至终我都是这么写道。很多人会忿忿地以为,此言是在靠矫情博取读者同情,实质不然。他的的确确是个酒鬼。以至于很多时候让我怀疑,他爱我们多一点儿,还是爱酒多一点儿?
他生于红尘之时,我是不爱他的。印象中,他没有尽过一位父亲的责任。即便有,那也是很让我伤怀和模糊的记忆了。在他的字典里,没有“理教”这两个字。他从不与我说任何道理,哪怕只是简单的碎语都不曾有过。惟爱于我犯错之时,手捏两指宽的竹条,从幽深的巷子里趔趄着狂奔出来,劈头盖脸地朝我身上一阵雨落。
他不曾念过什么书。但每次打我之时,嘴里都恨恨地挤道:“养不教,父之过!养不教,父之过……”
初二那年,他因饮酒过量,再度导致胃出血。对于这样的事件我与母亲都习以为常,未曾太放心上。后来,有年长的街邻前来探望,才悲切地说,怕是就此别过了。
此话一出,我的心里除了刹那的讶异之外,并无其他。母亲站在昏黄的木楼中,失声痛哭起来。大抵是受了感染,我也跟着默默流起泪来。
从此,家里的饭桌上没了父母的争吵,更没了那个黄铜酒杯。瞬时,灰绿交加的八仙桌清冷了许多。坐在他逝前临睡的沙发上,常常觉得手心发凉。我知道,并不是出于惧怕,而是总觉得有一种无由的失落,翻滚咆哮着从四面八方急急涌来,欲将这个脆弱狭小的屋子冲垮。
看着那两只铜黄的酒杯,禁不住想起很多年前的夜下,他烂醉如泥地趴在我的身上,哽咽地抓着我的臂膀说:“兴海,爸爸只剩下你和小涛(我的弟弟)了,要是你们也离我而去,我真将一无所有了……”
他喃喃地把这样的话叨念了整整一夜,直到我疲倦得沉沉睡去,醒来胸前一片湿润。我拨开他裂痕交错的手掌,轻缓地放正他的额头,像他儿时搂抱我一般,将他脱鞋,掖被,细细端详。猛然,泪水簌簌地掉落在他已是尾纹深陷的眼角上。
我捂住嘴巴,以生平最快的速度消失在了幽深的小巷里,生怕他会陡然醒来,怒目呵斥地对着我,将昨夜镂刻于我心间的温柔冻结。
那个他不曾知晓的夜,其实已全然将我生命中的仇怨瓦解。更或者,根本就不存有任何仇怨。要不,我怎会在提笔追忆之前就泪眼潸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