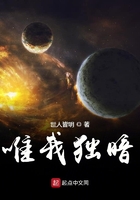大伙七手八脚踢啦蹚啷的把小四儿整到炕上放好,周大掌柜看了看,伤的不轻,又吩咐周二,“叫周虎带上炮手,码踪找找,看是谁干的?”周二走后,周大掌柜从周氏手里接过水碗,抱着小四儿的头,想饮些水,一瞅这嘴肿的没法饮,就叫伙头到灶房拿来漏斗,插进嘴里,饮了些水,一会儿小四儿右眼欠欠开个缝儿,死鱼的眼神,巡了一圈大伙儿。瞅见吉增后,眼神定定的盯住了,嘴撬不开,从鼻孔里窜出像“你”的哼声。
吉增上前,对小四儿说:“小四儿,不要急,就几张破狼皮,算不了啥,能活着回来,就算捡条命啊!这胡子也忒黑了,咋打成这样儿?小四儿,好好养着吧,别瞎琢磨了。”吉增说完,又死死的努努眼珠子,心说,俺不看老丈人面子上留你条小命,早摘下你小子脑袋当尿壶了!
小四儿哼哼地心说:你小子真阴,还猫哭耗子装慈悲……小四儿抹耷下眼皮,不吭声了。
大伙儿以为小四儿叫吉增几句安慰话安心了,也就没再多想。周大掌柜对吉增几句话也很满意,拍拍吉增的后背,“嗨,几张狼皮算啥呀,要是小四儿有个好歹,我这心咋安哪?唉,姑爷,你这几句话暖人心哪!”
周八爷颤颤巍巍拄着拐棍儿来了。周大拎过箱子放在炕沿上。周八爷叫人散散,别栖栖着,叫人脱掉小四儿的棉袄,扒开内衣,用手摁巴摁巴,除有几块青紫淤血外,没啥大碍,“女眷们别栖在门口了,来人把棉裤褪下来,看看伤着没伤着腿哪噶达。”伙头上了炕,往下褪棉裤。这一褪了不得了,小四儿杀猪似的嗷嗷叫声不绝。伙头一头大汗,不敢再褪了,棉裤没褪下来。
周八爷对周大掌柜说:“毛病出在下身,快拿剪子把棉裤豁开!”周大找来剪子递给伙头,伙头从一条裤腿往上劐,一直劐到裤腰,用手扒开一面,再扒那裆部,扒不了了,裤里和那宝贝玩意儿沾在了一起。小四儿疼得浑身哆嗦,拿手搪着,不叫动。伙头瞅着周八爷不敢动了。
周八爷先吩咐人用开水化些盐水来,瞅空对周大掌柜说:“我行医这有年头了吧,别说祖辈,咱白胡子都一大把了,还没经过伤这噶达的呢?这是叫人阉了还是骟了咋的?是要当宦官,还是太监呀,这可要断后啊?”周大掌柜“嗯哼”说:“八叔,瞅完了再说。”
盐水拿来后,周八爷戴上老花镜,拿镊子夹上棉花团,慢慢洇开,把棉裤扒下来。又叫人掰开小四儿两条腿,在场人都惊愕得呆若木鸡。周八爷手有些发抖了,骂骂咧咧地说:“这是造孽呀!咋下这狠手,这是往死里整啊?还好,没给剁下来。这两玩意儿,肿得像个小红灯笼,都透亮。这‘打种’家巴什更肿的没边了,像个老皮儿大紫茄子。”周八爷说着,拿碘酒擦着,“周老大呀,这小子这是叫人竟任儿打的。争风吃醋,看来是这玩意儿惹出来的祸。还好啊,虽肿的挺吓人,这倒没啥大事儿,小命是能保住了。等消肿,摆摆样子还可以。怕是伤着了弦子了,连带损伤了腰子,十有八九成人是废了。挑不起了,跟猪劁了一样,别指望了。唉,这小子淘气了。把人惹上了,还算不善,要是手再黑点儿,把东西捏化了,小命就不保了。我把脸伤和这噶达敷上些药,两三天能不能消肿,我可不好说。周老大,中药汤来的慢,你请个东洋大夫给他打两针盘尼西林。那玩意儿来的快。我怕这小子那个东西肿得厉害,憋住了尿,那就坏菜了!我再开个方子,两下一扎咕,就没事儿了。唉!唉!挺好个大小伙子,废啦!”周八爷晃着头,从药箱里拿出个小葫芦,倒出几粒小药粒儿,用老褶子的手捅进小四儿嘴里,“一会儿就不疼了。”就到桌前开方子。
这边,周大掌柜听周八爷这么一说,悬着的心总算搁在肚子里了。然后,对周大耳语几句,周大拉着周二走出去了。
周八爷开完方子,周大掌柜把周八爷让到上房,吉增也跟了进去。火锅也没撤,周大掌柜陪着周八爷喝两盅。半夜三更,周虎回来了。周虎说:“我们几个炮手牵着狗,顺着爬犁印儿到了出事儿那噶达,从雪迹上看厮打得不厉害,只有一匹马的脚印,从树棵子里撺出来的。又有一溜马蹄印儿往咱这噶达跑了一段,就钻进树棵子里去了。天太黑了,不好跟踪,我们就回来了。大掌柜,这是留在现场唯一的物件。”周虎把一个冻得缸缸的羊奶头递给周大掌柜,周大掌柜接到手翻来复去看会儿,“这玩意儿,咋血糊拉还像沾一层薄皮呢,啥意思呀?”周八爷拿过来看了看,“从这羊奶头看,是从冻奶山羊身上砍下的。这还有斧子砍的印儿。可这血是新鲜的。这皮儿吗,小四儿的上下嘴唇上可有没皮的一大块,这像似小四儿嘴唇上沾下的皮。怪了啊,嘴上插羊奶头,下边整那么一下子,这意思就明白了。羊****当娘们的咂头,下边那玩意儿是干那事儿的。这不跟娘们有关吗,啥胡子劫道呀,去******?”周大掌柜愣愣眼珠子,“这是一个枉死鬼啊,上哪找债主去呀?”吉增充好人地说:“爹,能不能是小四儿跟哪个胡子为了娘们有私仇,叫人暗算了?这一准是胡子干的。”周大掌柜横愣下吉增,“胡子?一个人下山,太少见了。不大可能?”吉增继续说:“能不能是 ‘插签’的胡子捎个脚啥的。小四儿正赶巧,祸害了小四儿?”周虎说:“这倒有可能。”周大掌柜脑袋晃得拨浪鼓似的,“谁没事儿怀里揣个羊****干啥,没事儿咂着玩儿呀?”周八爷说:“这可没准的事儿。胡子在山上一天也见不着个娘们,憋得狼哇的,没准就拿羊奶头当娘们咂头过瘾呗?”周虎说:“要那样的话,周八爷你没看看小四儿那噶达叫胡子****了没?”周八爷呵呵地说:“那倒没看。看了你还能看出像女儿身的见没见喜呀?”吉增说:“这倒合乎小四儿受的罪了,劫财又劫色!”
周大走进来,冲周大掌柜耳语几句,周大掌柜说:“这东洋人,给点儿脸,就抓挠?大小子,你对井下三郎说,我有事儿,等治好小四儿的病,我登门致谢!”周大回话去了。
周大掌柜对周虎说:“你抽个人,正儿八经守着小四儿,等嘴消肿了,看小四儿他咋说。我就不信,吃这冤屈?等我逮着谁干的,我非砸出它杂碎来不可?我这口气不出,誓不为人!”
这事儿,谁干的?
吉增听周大掌柜一说,心里一格登,你小四儿又没见着人面,敢胡诌巴咧吗?他小四儿要是敢胡诌,俺也就怀揣豹子胆,狮子大张口了,叫小四儿他个个儿去找周年吧!
嘿!小四儿竟大难不死,到阎罗王殿蹓了一圈,奇迹般的缓阳了。这是不遭死人罪,还得遭人间活人的罪。半拉来月,小四儿能下炕遛达了。皮肉伤,结疤掉了后,留下红润润的疤痕。周八爷说,疤过个伏天就没啥痕迹了。又精心配制了调理肾功能的汤药,服了一个来月,也没啥太明显的效果,就改用六味地黄丸继续调理。
小四儿能说话后,周大掌柜咋问也没说出个子鼠丑牛啥来,竟是些囫囵语,没有啥证据,这事儿暂时算消停了。吉增心也安了下来。
吉增那天听粉莲说完,气得没背过气去。一想小四儿忒不是东西,蔫嘎古董坏。往人家屎盆子拉完屎,还往人家脸上抹,卖谝的埋汰人!让你清楚的窝囊你,恶心你。他气不忿的。俺和你没啥冤仇,就你相中了美娃,也记恨不到俺头上啊,你得找你师傅去呀?美娃又不是俺从你手里抢来的,你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个个儿找罪遭吗?你向俺老丈人告密俺也没咋的你,你倒猪八戒倒打一耙,欺负上俺了?你睡粉莲就睡了,干啥还来告诉俺,这不明摆着埋汰俺,往俺心上捅刀子吗?俺要不以恶制恶,以古董制古董,以牙还牙,俺还叫七尺男儿吗?他想,对小四儿这种小人,得让他知道俺不是好惹的。要不叫他欺负住了,就不是往脸上抹屎了,还不踩头顶拉屎啊?在这种小人面前不能充善人,狗戴帽子最可恨,必须叫小四儿为此事儿付出代价。俺不整死你,叫你活着比死还难受。人不人,鬼不鬼,终身瞅着娘们不能睡,那才叫解恨呢?吉增想出了比小四儿更损、更阴毒的招术,更叫你小四儿打牙咽下去还说不出来,尤如鱼刺在喉。
从回春院一路走来,吉增就筹划好了复仇的计划。正好路过羊杂碎汤小吃铺,要了一碗喝了,走时看见旮旯有个剁下的羊奶头扔在那儿,吉增一想正好,捡起来,揣在兜里。哼,叫小四儿咂馊咂馊。又路过一个狗肉馆子,看见一个刚楦下的毛哄哄的东西扔在地上,就拿脚踢了一下,一瞅是个狗哨子,这正好给小四儿用上。也不顾埋汰不埋汰了,哈腰捡起来揣在兜里了。
吉增心里嘿嘿地有这羊****和狗哨子两样东西,不用说话,小四儿再呆头呆脑的也明白咋回事儿了。吉增到估衣店买了件黑大褂子,又到鞋帽铺子买了个一把撸黑毡帽,就回到自家铺子,……
老西北风刮起地上雪粒打在浸过桐油由蓖麻拉秕作成瑟瑟发抖的窗户纸上,演奏着“刷”“嗄啦”“唼唼”协奏曲,吉增裹在温暖被窝里正回忆所发生的事儿,美娃披着绸缎花棉袄哄睡了小胖,冷嗖嗖地钻进吉增被窝里,搂着壮实的吉增暖和身子,“哎老二,小四儿这事儿是谁干的,整出点儿眉目没有啊?瞅这事儿,把一个好好的小子给毁了。知根知底的姑娘谁能嫁给他呀,那不是守活寡吗?哎哟,这小四儿还不得打一辈子光棍儿?”吉增嘻嘻说:“谁干的,俺干的你信吗?你可怜他,你嫁他呀?小四儿可心里一直装着你呢?”美娃碓下皮拉嘎唧的吉增,“去你的。我剃过头啊,那也是小四儿剃头挑子一头热!来,小胖睡了,快欻空。”吉增装上大蒜瓣地无动于衷,“你,活鬼呀?嘎巴人的狐狸精!”美娃扳着吉增往个个儿身上扯,“我就嘎巴你!”吉增爬上美娃身子,动着,“俺看你整天捧个《西厢记》,你是叫大西厢里的小白脸魔住了。俺说吧,你就是个馋嘴猫,小骚包!”美娃煽情地说:“你呢,就是个猫嘴馋,小脓包!”小俩口,鲤鱼咬嘴嘎达腮,颠鷥倒凤欢愉一回。
小四儿自打这以后,一瞅见吉增的影子就躲得远远的。就跟耗子见了猫,两腿打哆嗦。小四对谁都缄口不提那档子事儿,直至吉增葬礼上,咧咧嘴,掉两滴冤苦泪,也没说出口。也是没发说,个个儿惹的祸,太丢人了。
周大掌柜后来托媒婆子,花了一笔不少的冤枉钱,总算给小四儿说上一门亲。一来二去,老婆三度豆花开,竟给小四儿生了三个儿子。小四儿心里明镜似的,自个儿不行,哪来的儿子?只得人前一套,人后一套。一人千面,人前是人,人后是鬼,人前笑,人后哭,阴不阴,阳不阳。他已看破红尘,一生只有和粉莲那一次,做过一回真正男人,却造成终身的悔恨。眼瞅着自个儿头上戴绿帽子,当活王八,还得跟那甩鲤鱼籽子的称兄道弟论哥们,猜拳行令,陪吃陪喝。当儿子喊爹时,那心酸的比刚拉核的杏还酸,苦得比黄连还苦,可脸上还得乐呵呵满口答应。
老婆虽找种下籽儿,也是个知冷知热的人,对小四儿体贴备至,才暖和了小四儿那颗冰冷拔凉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