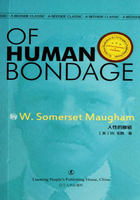而她不知道的是,真正是天助于她。第二天晚上,摄政王府中传来一个大好消息——王妃曹氏怀孕,阖府遍赏,就连这些看守苦役司的侍卫们,都得了美酒佳肴佐餐。
因此,柔嘉更是坚定了自己心中的决心。她知道,适逢这等喜事,萧锦彦必然要陪在王妃的身旁,无瑕过问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便是真有一两个逃奴逃走,苦役司也不会立时就能上报-----——只要拖延得一些时刻,想来,便是自己的重生之机。
彼时就在王府的南书房中,一身玄色便服的萧锦彦却正在灯下凝思。澄亮的金砖地上有匆匆拭去的水渍和零星细碎的瓷片,李德全重新奉了新茶进来时,见着他那脸色,不免有些迟疑地唤了一声:“王爷……”
萧锦彦回过神来,竭力平静着自己才方盛怒之后的嗓音,问道:“何事?”
“回王爷的话,王妃才刚又遣了人过来,问王爷几时过去她那边用膳,又说酒菜早就备好了,还请王爷……”
“本王知道了,你就回她的人,说本王一会就过去。”
李德全这才暗暗大松了一口气,正要将手里的茶盏放下转身退出,却听萧锦彦似乎冷笑了一声,继而是伸手拿起奉来的热茶,嘴角露出轻慢而狡黠的笑意,一字一顿地说道:“以为只要怀上了本王的孩子,就能困得住本王了吗?!”
李德全心里头明白,王妃曹氏出身孝献太皇太后的家族,本来就是太皇太后用来牵制主子的一枚棋子。
此时的主子对于王妃曹氏忽然怀孕之事,显然是十分不满的。而他也有些暗暗纳闷,照说王爷与王妃同房之前,一直有服用避子汤药,为的便是防着将来理不清的种种纠葛。而这三四年之间,王府的确有两个姬妾曾经怀过王爷的孩子,只是曹氏暗中使坏,加上王爷也并未用心想要保全那两个姬妾,因此,便是一个也未曾生下来。
转眼间这几年过去了,如今外头都开始有谣言,说摄政王虽然权倾天下,可杀孽过多,因此这才落了个无所出的下场。萧锦彦本人对此也不甚在意,似乎外人怎么说,都伤不了他一丝一毫。
可怎么一直毫无动静的曹氏,在这当口就忽然传出了有喜的消息?莫非,是……
李德全不敢往下再想,他打心里头替主子感到愤愤不平,却也知道曹氏在王府里的势力无人敢招惹,因此退出内室之后便去吩咐底下的人去准备王爷今晚在王妃处过夜的一应细节。
待到萧锦彦从内室中踱步出来的时候,外头的天色已经渐渐黑了。李德全跟在萧锦彦身后两步远,见其不言不语,也跟着默然。
萧锦彦行走时习惯负手于身后,他身量修长,容貌俊美,只是气质刚硬,站在那一处,便有一股子不怒自威的气势。此时跟在身后的皆是亲信内侍,七八个人手里捧着一应日常盥洗用具衣衫等物,随后更有二十来个心腹侍卫,一行人踏着夜色行来,却是安静的连脚步声都听着整齐划一。
夜色中的摄政王府,在萧锦彦的沉默中显出有种别样的落寞。眼看着前方就是曹氏所住的锦瑟轩时,李德全刚要示意前面的内侍进去通传,却猛然听得萧锦彦开口问道:“那傅柔嘉这些日子,在苦役司可还算老实?”
李德全十分意外此时听到这样的问话,但当下就立时回道:“回王爷,据那边的人回禀,说是已经按着王爷的意思,安排了一个难缠的小丫头和一个老嬷嬷,着力调教了几次,还算有些成效。只是奴才不明白,王爷费这般的力气,难道真就为了将她赐予孙元靖?那孙元靖可……”
萧锦彦本来走在前头几步之外,此时却忽然回转身来,一双眼睛似笑非笑的在李德全周身打量了一下。而后道:“本王的确说过,要将她赐予孙元靖为妾。不过,本王可没说过,送的是死人还是活人。”
李德全很快就明白了这话的意思,他知道自己的试探之意过于明显了,于是浑身一激灵,立时应道:“王爷恕罪,奴才僭越了。”
萧锦彦径直往锦瑟轩的门口走去,也不理会他的请罪。待到李德全一身冷汗地抬起头追上去时,却见王妃曹氏已经一脸明媚地迎到了门口,正粉面含春地笑着与萧锦彦见礼。
次日,苦役司中果然也有几分喜气盈盈。早饭的时候,卢妈妈甚至给大家都派发了一个沾着红色的鸡蛋,说是阖府同庆,沾一沾王妃的喜气。
柔嘉手里拿着这个鸡蛋,眼睛却有些依依不舍地看着卢妈妈。她知道,若自己能够成功,那么至此之后,自己是不可能再见到她了。
一路无话,同行的云儿似有些不太精神的样子,柔嘉与她近乎沉默地分了工,而后便各自蹲在一处小河滩边,开始了繁复的工作。
天上的日头开始渐渐热了起来,一早上的时间过去了,身边的马桶也堆了一大堆了。
柔嘉不时地回头注视那两匹站在不远处吃着草的马匹,她开始有点焦急,虽然之前在心里千算万算了无数次,但到了这个时刻,心中还是充满了疑惧的。
要知道那豆子虽然用水发过了,但是,什么时候膨胀起来,她却无从得知,这一点人算不如天算。
柔嘉洗一只马桶就在心里记一次,额前的汗水冲下来,也顾不得伸手去擦。热辣辣的汗水流进眼睛里,泛起一片白花花的疼痛,就如那日头下哗哗流淌不息的河流。
约莫过了一个时辰,柔嘉只觉得自己两只手麻木成了棍子,小扫帚拿在手里,颤抖得几次差点被河水冲走。
终于听到两匹马开始烦躁的嘶鸣起来,侍卫有点奇怪的走过去看了看,以为马儿是想要喝水了,便将两匹马都牵到河边饮水。
机会终于来了!
柔嘉轻轻咳嗽一声,起身捶了捶自己酸痛的腰身,开始清理手上的活计把马桶往岸边提去。
这当口的功夫,侍卫终于察觉到马儿的异常了。此起彼伏的嘶鸣声还在其次,最特别的是,两匹马都拼命甩起尾巴,似乎想要将背上刚刚套上去的车架给甩下去,挣脱被侍卫牢牢系在岸边柳树上的缰绳,撒蹄疾驰而去!
当然是拼命挣扎的,发了一夜的黄豆被柔嘉之前轻巧地推进了马儿的后门内,这会子不知道如何的膨胀呢。
云儿此时也已经提着几只马桶走了过来,她看着侍卫将才刚套上去的车驾又解了下来,可两匹马依然还是挣扎地十分厉害,不免心里也有些害怕。
她一慌了神,便朝柔嘉伸出手来,大叫道:“这马是怎么了?怎么今日这样的奇怪?莫非是撞了什么邪不成?”
柔嘉便趁势跑过来,趁着侍卫们都在手足无措的时候,一手提着一只洗得锃亮的马桶,一手攀上了其中的一匹马的马背。
她摸出自己之前花了几夜的功夫自制出来的一条缰绳,将其在马背上重重地抽打了两下,只听一声长长的嘶鸣声过后,那马儿终于挣脱缰绳,嘴角带血的扬蹄而去。
“抓住她!别让她跑了!”
很快,就有侍卫发现了柔嘉的意图,并且迅速的地追赶上来。
柔嘉坐在马背上,听着耳畔的呼呼风声,回头看见那一只只想要将自己从马背上拉下来的手……她知道自己此时不能有丝毫的犹豫,于是,在最前面的一个侍卫即将追上自己的时候,她闭上眼睛,用了最大的力气,将手里的马桶重重的朝他的头上砸了过去。
一声闷响过后,仿佛听见有人惨叫了一声。
柔嘉睁开眼,看见站在远处的云儿张大了嘴巴,十分惊恐地看着她。
顺着云儿的视线看过去,天!血淋淋一片嫣红,那侍卫的半边脑袋都染满了血迹,此时已经倒在了河滩边。
再也不能等了!
河滩边其余的侍卫闻讯已经操起佩刀朝这边跑过来,柔嘉惊恐地望了一眼云儿,她不知道自己最后想要跟她说什么,却是近乎祈求地看了她一眼。
跑!
慌乱中颤巍巍伸出一只脚来,往那马屁股上狠命一踢。
马儿疯狂的往前疾驰,周遭的一切风景都在飞快地逝去。这匹无比焦躁失控的马儿,将所有的追兵和侍卫尽数远远地抛在了后头。不多时,便再也听不见身后的响动了。
过了约莫有一盏茶的工夫,那马儿的脚步渐渐放慢下来。柔嘉心知不好,这马是支撑不了多时了,便立即将自己放在袖中的巴豆粉塞进马嘴里,然后伏在马背上,开始寻找下马落脚之处。
恰好前面就是一处河滩的拐弯处,路旁一棵垂杨柳,日头下面绿意盈盈,泰半的枝条都顺水垂进河里,俨然有弱柳临水之美态婀娜。
而这一处河滩再也不像之前那般的清浅,只需往水中迈入几步,便是幽深的河床。
柔嘉快速地环顾了一番四周的景象,隐约听得身后的追兵喊声之后,最后咬牙翻身从马背上滚了下去。
虽然是平安落到了地上,还是疼得半天睁不开眼。要不是想到后头还有追兵,柔嘉也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挣扎着爬起。
倒抽着冷气起了身,腰上是一整片火辣辣的痛,大腿上也有几处地方被磨破了皮。后脑勺碰在地上,眼前只是一片白花花的火星乱串四溅。
暗暗摇头一声苦笑之后,顾不得伸手揉一揉痛处,柔嘉赶紧手脚并用,扑腾着跳进了河里头。
河水微凉,人一投身进去,水声淙淙,仿佛外面的一切都隔断了。
柔嘉憋住气,伸手拽住了一根老柳树的根,悄悄地潜伏在清浅的水面,不时换气看着后面追兵的去向。
这样做比较冒险,不过,也唯有确认对方已经误以为自己骑马逃匿,她才能静下心来想一想接下来的对策。
再则她水性有限,不可能一口气游到下游去,所以,等待是她目前唯一的出路。
也不知道是不是担惊受怕的时候时间过得特别慢,总之,柔嘉是在自己换了三次气之后,才看见那几个气急败坏的王府兵丁的。
在亲眼目送他们往马儿逃走的方向追去之后,柔嘉才深吸一口气,悄然沉入了河底。
这一口气潜了下去,既是因为担心后头的追兵,又是因为不清楚前方的路况,所以游得很慢。还好一顿子折腾下来,并没有什么风声鹤唳的消息跟来。
直到天色约莫快要黑了,耳畔的蛙声渐渐次第响起,柔嘉才手软脚软地从水里浮出来,仰起头痛快地大出几口闷气。
天色已黑,对于一直潜在水中想要摆脱追兵的柔嘉来说,这不啻是一个很好的脱身条件。
终于顺流而下,进了城中东南这一片的青瓦白墙的水榭之中。乍眼一看,原来这偌大的河面都被圈周围的几户大户人家成了好几份。
柔嘉一边寻找这上岸的落脚点,一边环顾四周星星点点蜿蜒如灯河的富贵景象,心中不免感叹:难怪这南齐年年对外征战,萧锦彦有本事挥军四下,好一副所向披靡之态。原来南齐富庶,早已超出大秦想象。可怜父皇被奸臣蒙蔽,至死不知双方力量悬殊之大,生生在亲征路上断送了性命。
想起父皇,柔嘉心中一阵黯然的刺痛。
抬起头,深吸一口气,眼之所见,远处一方水榭灯火隐淡,又正是靠水岸而建。
柔嘉心中一喜,难道这家无人?这一双手脚在水里早已泡得没了知觉,当下费尽力气,总算不顾形象地爬上了伸在水里的一条汉白玉美人靠。
拧了拧身上的衣衫,再看看四周。
这时候暮色四起,一钩新月映照江面,烟笼寒水,耳朵里哗啦啦的流水声终于渐渐寂静。
柔嘉坐在无人的美人靠上,夏日里只觉凉风袭来,冷沁骨髓。
这一天担惊受怕下来,真是疲累极了。因为实在是腹中空空如也,柔嘉这才大着胆子在小径上走了走。此时天色已经暗了,最后没有找到可以吃的东西,靠在坚硬的玉石肩靠上,脸压着一丛绿绒绒的茎蔓草叶,柔嘉也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精疲力竭之后的一梦,真正是无知无觉地睡下去,一晌贪欢不知身在何处。
“你是什么人?居然敢擅闯我家姑娘的禁地?”
昏慵慵地睁开疲惫的双眼,不料迎面被人喝上一句,接着,说话的那人作势就要来拿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