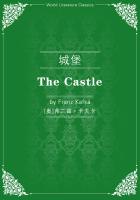在第一次进入李娟身子的时候,黄福稳发现李娟已非处女,这使他颇有美中不足之感。但他很快就释然了。李娟作为很有气质的上海姑娘,无意中成全了黄福稳在十多年前就已做过的“美梦”:能与上海姑娘同床共枕,乐莫大焉。
黄福稳虽然痴迷于李娟的身子,却对中餐馆的日常业务没有丝毫耽误。这也是黄福稳作为商业老板的精明之处。
“左拥右抱”这样撩人遐思的成语,也只有聪明的中国人方能造得出来。三十二岁的黄福稳,就正徜徉于“左拥有抱”之中了。他以前每个星期与妻子玛莎做爱,基本上都不少于两次。但他从三月份把李娟弄成情妇之后,他与玛莎每个星期做爱就不超过一次了。
今年三十八岁的玛莎,从年龄到体貌,完全能做二十二岁的李娟的阿姨了。眼见黄福稳在床上那种仿佛例行公事一样的态度,玛莎幽怨不已,可又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将黄福稳改变过来。玛莎当然不知道,黄福稳的焦点已经转移到李娟的身上了。
黄福稳主动减少与玛莎做爱的次数,说给玛莎的似乎情有可原的理由,是中餐馆的生意越来越好,所以很忙很累。实际上,他是为了养精蓄锐,以便自己在李娟的身上耕耘出更加有力的陶醉。
在第一次进入李娟身子的时候,黄福稳发现李娟已非处女,这使他颇有美中不足之感。但他很快就释然了。李娟作为很有气质的上海姑娘,无意中成全了黄福稳在十多年前就已做过的“美梦”:能与上海姑娘同床共枕,乐莫大焉。
黄福稳虽然痴迷于李娟的身子,却对中餐馆的日常业务没有丝毫耽误。这也是黄福稳作为商业老板的精明之处。
店里晚上的下班时间都是较迟的十一点,黄福稳觉得自己不能在这个时间经常去李娟的住处约会;他很清楚,哪怕是个把钟头的短暂约会,也难免导致自己和李娟第二天上班容易疲倦。除非自己的欲火委实难耐,他才会于硬憋几天之后,慎重选择某个晚上十一点的下班时间,开车赴李娟的住处速速“云雨”半个小时左右;一俟完事,就又匆匆起床穿衣,开车赶回家里,显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睡到妻子玛莎的枕边。至于整晚都在李娟那里过夜的游戏,他是绝对不会做的,因为他有自知之明,在外面过夜,如果提供不了经得起玛莎核实的理由,他的狐狸尾巴就将被玛莎牢牢地抓住了。
不过,黄福稳白昼上街,纵然到外面待了整个上午和下午,玛莎在家里都不会怀疑什么;因为他毕竟是商业老板,免不了要去会计师事务所之类的地方办理各种事情。于是,每逢店里星期一的休息日,若无特殊情况,他都要开车约上李娟,去高档宾馆开一个房间,不慌不忙地玩够整个上午和下午。当他带着一副精疲力尽的样子回到家里,晚上躺在玛莎身旁的时候,玛莎总以为他是被店里与外界打交道的工作操劳致累的,还十分温存地给他做按摩呐。
李娟对自己竟然充当黄福稳的秘密情妇这种状况,深以为怨。因而,她在与黄福稳“二人世界”的时候,或者在店里公开场合的时候,她往往要找一个借题发挥的由头,向黄福稳闹一些没什么作用的小脾气,发泄自己心中的不满。但她看在钱的份上,又不愿一走了之。她已留级一年了。若不趁着这一年留级有空的宝贵时间努力打工挣钱,那她在巴黎的生活费与学费,以及她父亲在上海治病的医药费,都将成为很大的问题。
作为福稳中餐馆洗涤组的组长,李娟却是不脱产的,每天仍需不折不扣地完成洗碗的任务,但她对此并无怨言。不脱产就不脱产吧,劳动毕竟不是什么丑事。何况,“组长”这种头衔,还能使她每月多领三百法郎的职务津贴哩。她感到委屈的是,虽然她在店里其他员工的面前不脱产,可她在私下里却常常要被黄福稳用蛮力脱光衣服,让自己的每一寸肌肤,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黄福稳那强烈的****。正因如此,她总是寻思着要黄福稳在经济上尽量对她有所表现。
又是一个星期一的上午,黄福稳照例趁着店里的休息日,约了李娟来到一家高档宾馆,开了一间客房。
李娟见黄福稳要动手脱衣服了,连忙阻止道:“慢着。我今天先要与你谈清几个概念上的问题。”
黄福稳听了,感到好笑:“不要文诌诌的,好不好?说事就说事,何必咬文嚼字的,扯什么‘概念上的问题’。”
李娟说:“我没心思跟你耍贫嘴。你直接回答我的问题:在你的心目中,我的身份是什么?”
黄福稳说:“这还用问么?你是我的情人呗。”
李娟很干脆地予以否认:“错了。”
黄福稳稍稍愣了一下:“那……你是我店里的员工,这总没错吧?”
李娟说:“也错了。”
黄福稳说:“你简直把我给弄糊涂了……”
李娟冷笑了一声:“那就让我开导开导你吧。‘情人’这个词,确实能够蛊惑女人的心灵。你很精明,为了得到我的身子,就用‘情人’这个词掩饰你强迫的手段。但我现在觉悟了:‘情人’这个词虽然看上去很美,实际上只是‘二奶’的代名词而已。至于‘二奶’这种称呼的含义,你不可能不了解。古往今来,所有在外面悄悄包养‘二奶’的男人,谁能不必专门花上一大把钱呢?我左思右想,只有你这个黄老板,瞒着自己的老婆,在外面悄悄占有我的身子,却不必多花一分钱。你真是‘古今中外第一猛男’啊。”
黄福稳被李娟的一席话臊得脸红耳赤:“阿娟……你……说话不要这样尖酸嘛。无论如何,我是因为喜欢你,才让你到店里打工,又让你当了洗涤组的组长。这些暂且撇开不提。我每月给你提供的租房补贴两千五百法郎,难道不是我专门为你多花的钱么?”
李娟说:“任何企业,一般来讲,老板都应该喜欢他手下的员工。否则,老板既看这个员工不顺眼,又看那个员工不顺眼,怎能保持企业的正常运转呢?所以,你说你喜欢我,等于在说你喜欢包括我在内的店里所有员工们。这当然不能成为你占有我的理由。至于租房补贴,也并非你专门为我多花的钱。因为租房补贴像职务津贴一样,是你安排给店里组长们的岗位福利。烹饪组的组长阿柳虽然得不到租房补贴的现金,但他能在店里免费住宿,也就是享有租房补贴的待遇了。”
黄福稳说:“你绕来绕去,是要我向你支付每次约会的‘服务费’,对不对?”
李娟说:“你又错了。”
黄福稳说:“我更加不明白了……”
李娟叹了一口气:“我让你占有了我的身子,我心里其实很不乐意。可我决不会以此为筹码,向你索要任何钱财。否则,我就成了‘卖身女’了。我虽然十分渴望经济收入,但我只会卖自己的劳动力,不会卖自己的身子。”
黄福稳沉吟了若干秒钟:“那……你刚才曾说自己不是我店里的员工,你又怎样解释呢?”
李娟说:“根据法国政府的有关政策,企业在用人的时候,只有履行了合法的报工手续,那个人方能成为企业真正的员工。阿柳不是‘偷渡客’,而且符合企业报工的条件,你已经给他履行了合法的报工手续,所以他是你店里真正的员工。我呢,也不是‘偷渡客’,也符合企业报工的条件,你却不给我履行合法的报工手续,所以我算不上是你店里真正的员工。”
黄福稳说:“关于这一点,我想请你听从我的安排。我这店里全部的员工之中,只有五个人已经报了工。我本人是其中的一个,我老婆也是其中的一个。我老婆虽然现在没到店里上班,但生小孩以前也是店里的员工。至于我老婆的弟弟费蒙,他是巴黎的居民,我当然必须给他报工。还有澳门人阿乔,作为店里工龄最长的员工,我也给他报了工。说到阿柳,因为是我哥哥的小舅子,我哥哥早就向我打了招呼,所以我不得不给他报工。法国政府对企业征税的税率是很高的。按照你们的月薪六千法郎来算,我这店里每报一个工,每月就得向税务机构上缴用工税四千多法郎。可我即使给你报了工,你的月薪并不会增加一法郎,你何必要求报工呢?”
李娟思考有顷:“你应该给我折衷一下……”
黄福稳听了,一时不解:“折衷?怎么折衷?”
李娟显出一副有理有据的样子:“我可以不要求报工。这样,店里每月就能免交用工税四千多法郎。但我放弃报工,并非因我不符合店里报工的条件,而是为了顾全店里的利益。因此,我觉得,店里应该从每月免交的四千多法郎用工税之中,拿出一半作为奖金发给我。”
黄福稳不以为然:“亏你想得出这样的奖金。你这是变着法子找我要钱嘛。”
李娟坚持着:“但我认为并不过分。对于劳动上的钱,我应该要的,我自然得要。”
黄福稳看李娟这样子,是想拿店里打工的事情做文章,不断为自己增加经济收入。黄福稳作为很精明的温州老板,当然不愿由着李娟的性子,但他又对李娟有些犯怵:如果李娟因失望而生他的气,将他二人常在外面“野合”的事情告诉他老婆玛莎,或者将他店里瞒报用工税的事情告诉税务机构,那不就麻烦了?因此,他感到有必要采取一种出奇制胜的措施,很巧妙地钳制李娟。于是,他使用缓兵之计,暂时稳住李娟的情绪:“你给我一个星期的时间,让我考虑考虑,这总可以吧?”
李娟一边颔首,一边强调:“你考虑几天是可以的,但到时候,我要你作出肯定的答复。”
到了下个星期一,李娟按照惯例,应在早晨七点钟给家里拨电话报平安,然后在宿舍里等候黄福稳。
一般情况下,黄福稳皆于星期一的上午九点左右,开车来接李娟去宾馆客房颠鸾倒凤,共度休息日。
而这个星期一,对于李娟的心理空间来说,又多了一项内容:黄福稳必须作出肯定的答复,每月都向李娟支付两千多法郎的所谓“奖金”。但是,李娟在早晨七点钟,到街边公共电话亭里,用“中文电话卡”给母亲拨电话的时候,遇上了始料不及的新情况。
电话里传来母亲探询的声音:“娟儿,你是不是在用新买的手机给我打电话?”
李娟莫名其妙:“新买的手机?”
母亲的声音有些疑惑了:“你不是新买了手机么?而且是你打工的店里出钱给你买的呀。”
李娟立即猜到一定是黄福稳在自己背后搞了什么小动作,但又不便贸然追问母亲,唯恐引起相隔万里之远的母亲不必要的担忧。
母亲显然已被黄福稳表面的热情给诓蒙了:“你那个店里的黄老板,昨夜专门打电话向我问好。他问清我的身份之后,一口一个‘阿姨’,叫得可热乎了。他说你在店里干活很勤快,就是有些心高气傲,不把老板放在眼里。他要我劝劝你。娟儿,如果真是这样,你可一定要听听我的劝了:为人还是随和一些才好啊。”
李娟十分尴尬,只得顺着母亲的话音,陪上几缕模棱两可的笑声。
母亲如数家珍:“黄老板还说,你的工资待遇在店里属于上等的标准。他让你当了洗涤组的组长,又有职务津贴,又有租房补贴。是不是这样,娟儿?”
李娟对这些情况倒是没办法予以否认,因而支支吾吾地向母亲表示了肯定的意思。
母亲的语气有些郑重其事了:“黄老板说他不仅要向我问好,还要向我告状呐。”
李娟听了,心里一紧,不知道黄福稳那张“乌鸦嘴”要搬弄什么样的是非。
母亲条分缕析:“黄老板说,你的工资待遇每个月都能兑现,不会发生什么闪失。但奖金并不是每个月都有的。你却逼他每个月都得发奖金给你。他请我劝你放弃这种不现实的念头。我认为,如果真是这样,你就应该听从黄老板的安排。你现在回答我:究竟是应该,还是不应该?”
李娟已是啼笑皆非了。她一边深怨黄福稳玩起了“恶人先告状”的把戏,一边又不敢在电话里向母亲披露事情的真相。万般无奈之下,她只好含糊其词地应承了母亲的主张。
母亲耐心叮嘱:“黄老板为了你能方便打电话,决定由店里出钱给你买一部手机。他说,你的年纪比他小十岁,他一直把你当作妹妹看待。他让我和你父亲在上海放心,你在巴黎学习、工作、生活、安全各方面的事情,他都会提供帮助。我觉得,黄老板很是通情达理。你也要很好地把握自己。我们与你相距万里之遥,只能在上海默默地祝福你,默默地感谢你为家庭经济做出的贡献……”
李娟勉强撑起精神,在电话亭里向母亲做了“承诺”、道了“再见”,就返回了宿舍,连门都懒得关了。她对黄福稳已经恨极了。黄福稳在她的身上“得了便宜又卖乖”,甚至利用她那不知情的父母亲的厚道观念,巧妙地约束她的言行。她认为,黄福稳这一招,确实够得上阴损的水平了。
随着一串故意走得很响的脚步声,黄福稳来了。他一见李娟懊恼的样子,就清楚自己的措施已经奏效了。他一边递手机给李娟,一边佯作憨态地搭讪道:“呵呵,怎么生起闷气来了?瞧,我给你买了一部新手机呐。”
李娟愤慨填膺,并不理睬那部手机:“你怎么那样恶毒啊!不就是每个月两千多法郎的奖金么?你不愿给我,我不指望就是。你何必绕那么大的圈子,打扰我的家庭,利用我的父母亲约束我呢?”
黄福稳仍向李娟举着手机:“嗨,言重了、言重了!我是无意中看见你的家庭电话号码,所以忍不住拨了个电话,向你父母亲问个好,顺便也说了说你在我店里工作的情况。你是你父母亲的‘乖乖女’,我向他们报喜不报忧,也是为了让他们在上海不至于过份牵挂……”
李娟把黄福稳的花言巧语打断了:“其实,你肚子里的那几根花花肠子,我已经看透了。你知道我爱我的家庭,我爱我的父母亲,我最不愿因为自己身上的过错,导致他们伤心。你呢,生怕我向你老婆,或者向什么税务机构,检举你的某种隐衷。所以,你就凭借我对父母亲的感情来要挟我。”她终于以“不要白不要”的神态,接过黄福稳一直举着的手机:“现在,你又想拿一部手机来收买我……”
黄福稳显出一副风平浪静的样子:“呵呵,你真聪明,说得很有道理。不过,我们之间算是扯平了,你别再恨我了。”
李娟余怒未消:“我们之间永远扯不平,因为你太坏了。”
黄福稳厚颜而笑:“俗话说得好:‘男人不坏,女人不爱’嘛……”黄福稳说着,一把搂住李娟,不顾李娟的抗拒,使劲吮吻李娟那青春性感的嘴唇。此刻的黄福稳,就像一条形状可憎的大蚂蟥,蛮狠狠地吸附在李娟的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