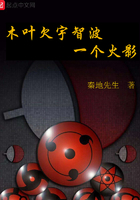电影结束时,女孩的脸便再也无法从我眼前赶走。她是一个邪恶的女孩。时间已是后半夜,她的脸在黑暗中隐隐地藏着,有时在屋角,有时在吊灯旁边,那是一张吊死鬼的脸,嘴角淌着血。
浅茅的家,在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阴郁酒吧。女孩引吉野上二楼,女孩在楼上冲她招手,狭窄的楼梯,幽暗的通道,那种氛围很是吸引人。
浅茅是个邪恶的幽灵,她可以使玻璃在瞬间迸裂、粉碎,尖锐的玻璃碎片飞溅到真理子的额头上,真理子是她的情敌,浅茅恨她。在一个吉野与真理子约会的夜晚,浅茅出现了,她像路边的树木一般,每隔一段距离,她的脸就出现一次。
真理子感到万分恐惧,然后,她的自行车突然失灵,旁边亮起了血红的道路施工标志,真理子连人带车掉了进去。第二个跟吉野好的女孩,也被浅茅害死,她死在火车轮子底下。那场大雨中浅茅分身两处的戏,令人感到阴冷和恐慌,像白日的夜晚,灰色而又凄凉。
日本电影的氛围感是我最喜欢的东西。东方人有一种神秘的、难以言说的意趣,深刻、曲折、多意。跟东方人的性格比起来,美国人的性格就有点像个大顽童,打打杀杀,飞车,爆炸,要不就弄一条大船,船上发生一场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爱情游戏。
日本电影的氛围实在是很好。恐怖电影,一定要有阴森森的美感,我讨厌血腥和杀人的影片,吸血鬼影片,这类电影千篇一律,看过之后连噩梦都不会留下。
《生灵》的后半部分拍得不怎么样,天塌地陷,弄着弄着,不知怎的,倒有些像美国电影了。东方的神秘感没有坚持到底,到后面仙气全无,变成一部标准的“灾难片”。
这部电影如果交给我拍,可能会拍得更好些。小说家就是纸上的导演和演员,一个人能够撑起一个世界的。我的小说表现了神秘的女性世界里奇异的幻想和欲望,我开创了一个世界——幽深的女性世界,我乐意接受这种说法——“梦幻掌门”,我不愿意给别人的小说流派添砖加瓦,因此,就自创一派。我愿是一棵独立的、不依附于任何人的大树。
现在,我的树已枝繁叶茂,有了属于自己的天空。
常常由电影想到写作,因为它们是相通的。但愿有一天,会有一部属于自己的电影。一部女性电影还是恐怖电影?一部纸上的电影还是现实中的电影?时间会让关于我的故事慢慢打开,展现在人们面前。
我等待那一天的到来。
第44节 放下骄傲
写东西的人骨子里总有那么一点孤傲,这在现实生活中显得有些与现实脱节,现实社会纷乱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有的人地位卑微,却是“现官现管”,有一小点点权力握在手里,就觉得不用白不用,过期作废。他们态度傲慢,平白无故翻着白眼,尽量使你的事情办得不顺利,这样他们的心里好快活一些。
我在驾驶学校学开车,每天最头痛的不是太阳晒,也不是挨教练训,最头痛的是上车之前的“电子刷卡”(其实是人工刷)和验指纹。指纹机经常失灵,明明是本人的手指按在那红红的小平面上,却像罪犯一样被揪出来——屏幕上什么也不显示。
这时候,坐在小窗口里面负责刷卡的女人,通常就会先瞪你三个白眼,好像一切错都在你。你想跟她辩解:“哎,这错不在我呀!”可人家不给你这个机会,三个白眼过后,声音冷漠地说:“下一个,快点!”好像在唤她家院里等待喂食的狗。
我只好在一旁将自己的手指在裙子上使劲儿地搓,裙子都快搓出个洞来了,趁着“下一个”的手拿开的工夫,立刻将自己的手指按了上去,但依旧没有显示。脸色蜡黄爱翻白眼的女人,眼睛里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冷笑。
她每天用这种态度工作,我就不明白,他们老板为什么不开除她?
下一个小伙子的指纹也被卡住了,白眼女人还是用同样的方法“白”他,真不知这个坐在窗口里管刷卡的女人,一天要翻多少次白眼。但是没办法,所有的人都得忍着,每天早晨还是得找这个人刷卡。
找队长测试,又是考前的另一难关。队长长得像黑脸包公,态度傲慢,对教练和学员爱搭不理,本来“测试”是他的工作,倒变成对他的一种企求。所有要过关的学员,都想尽办法用好话来“喂”他,求他让自己再试一次,或者,干脆对他软磨硬泡。久而久之,他变得更加傲慢,仿佛他是天王老子一般,每个攥在他手里的学员,都得低三下四地求他,如果你太有个性,太不肯委曲求全,那么,就连参加考试的资格都没有。
有个朋友告诉我,不要在乎别人的态度,为达到你自己的目的,就像说电视剧台词一样,你说几句好话不就完了。
我把好话背得滚瓜烂熟,准备明天一早,去对那个黑脸包公说。后来我知道,好话的确是管用的,我过关了。
第45节 北方的风
北方的风很像一个看不见的人,他想来你家做客,就不由分说举起拳头擂你家的门,擂完了不行就用脚踹用屁股拱,最后办法使完没有达到目的,就索性在楼道里发起脾气来,它叮零哐啷乱摔东西,一会儿把一个好端端的啤酒瓶“砰”地一声从窗台轱辘到地上,一会儿又把楼梯拐角处的玻璃窗“乒乒”拿来摔两摔,那块玻璃一开始还算挺得住,但三摔两摔玻璃表面就裂出冰纹来,最后“哗啦”一声掉在地上跌得粉碎。
在北方,刮风天很多人躲在屋里不出门,就是临时到外面买个酱油散个步也得穿上带帽子的厚外套,小时候我们都管这种外套叫“棉猴”。今天我下楼去散步就穿着这种“棉猴”,因为外面刮着很大的风,我一走出楼门口就被一只巨大的手推着走,我一开始还想抵制,故意站在原地不动,但后来我知道我拗不过风的——自然界的一切神力都不可抗拒,那我索性顺应潮流被风当成手中的一枚棋子,我被它刮得在风中滴溜溜地打着旋,对自己已经失去了控制力,脚不沾地如同在冰面滑行,终于碰到近处有一排铁栏杆,急忙伸手抓住以免被风吹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去。
透过那排铁栏杆,我看到一个盖房子的建筑工地,吊着的灯被风吹得变了形,灯影忽闪忽灭,人影交互叠错,工头哇啦哇啦在大声喊叫着什么。风更大了,我听到北风在空中咝咝打着呼哨,有一绺特别尖细的声音,像是有厉鬼藏在空中,故意憋细了嗓子好迷惑路人。有砖垛被风吹倒的声音,稀里哗啦宛若一罐子碎银元落地,工头气疯了,喊叫的声更大了。可生气有什么用,风又没长耳朵。
说到风我倒想起前一阵子读到过的小说家莫言的一篇散文《会唱歌的墙》,这篇文章的结尾非常奇异,散文都是说真事儿的,这篇却充满幻想,说他们那儿有个老人收集了几万只空酒瓶砌成一道墙,把他们乡和外乡隔开来。那道墙瓶口一律朝着北,只要是刮起北风,几万只瓶子就会一齐发出音色各异的呼啸声。老人砌完墙就坐在那儿死了,后来会唱歌的墙倒了,“几万只碎瓶子在雨水中闪烁着清冷的光芒继续歌唱”。这就是北方人对风的深刻而又自然的印象,北方的风像刀子刻心,强烈而略带一点残忍的味道。
一夜飓风,满地碎片。第二天一早,我踩着碎玻璃碴子上路了。
第46节 最后一页碎片
张爱玲的散文,是那种信手拈来式的做派。她是那种看到什么都有感觉的女人,看到书写书,看到画写画,看完戏就写《散戏》。给一本书写再版的序,她就东拉西扯地乱说上几句,好像什么也没说,又好像什么都说了。她的东西就是这样,所以她的书叫做《流言》和《传奇》。
多么简单的事到了她那里势必琐屑、细碎,纠纠缠缠地像永远不会完。我倒并不觉得她那一两句常常被人引用的“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的名言有多么的好,好多东西一断章取义就别有另外一层意思了。
我最初读到张爱玲是1994年夏天在北京王府井书店。那时位于王府井街口的老店还没有拆,我站在众多架电风扇呼呼啦啦吹起的龙卷风里翻找自己喜爱的书。那时我自己写的书还没有出版,我一边在一大排女作家写的书里流连,一边暗自打算:“等到有一天,我的书也要出现在这家书店。”可是等到两年后我真的出了书,那家全国最大的书店已经被拆毁了。我不知道王府井书店现在搬到哪儿去了,朋友打电话来,说在那里看到我的新书。
现在想来我手头的这本张爱玲的《畸情小说》可能是我在王府井那王府井东方广场。心血来潮时,我爱在街上闲逛,戴粗大的少数民族风格的项链,背一个行军式的大书包。
家大书店里买到的最后一本书了。我不是那种特别舍得自己掏钱买书的人,最好是等着有人送。挑来挑去我挑中两本,一本张爱玲一本老舍,余下那几本就等着生日或者什么不相干的节日开下单子让朋友送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