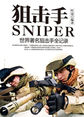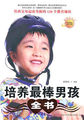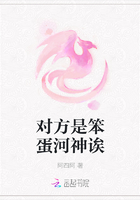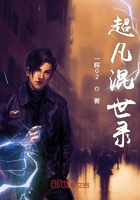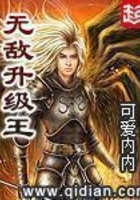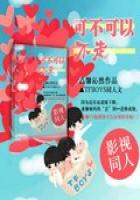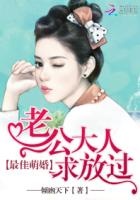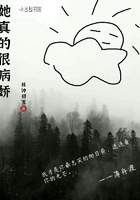人贵有自知之明。这是实在话,不过很多人听不进这句话,因为他不实在。不懂得“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道理,总想文过饰非,总想用嘴巴来弥补自己的不足,而事实上说得越多,自己的无知也就越明显,老子说:“多言数穷,不如守中。”所谓守中,就是把自己的想法放在心中,用心去体会,去思考自己。不过要做到守中也不容易,如果容易,每个人就都能做到了,而事实上真正懂得这个道理,能够做到的少之又少。这个世界上,总是夸夸其谈、鹦鹉学舌的多,很多人因为自己太会说话而最后弄得漏洞百出,笑话连篇,甚至自相矛盾,这就是最会说话的人反而最不会说话的道理。话说多了就是吹牛皮,就失去了信用,老子说:“夫轻诺必寡信,多易必多难。”很容易说出去的话、答应出去的事情,总是很难做到守信的,经常变化,没有定数,总会带来意想不到的困难。
做人和说话是一样的,需要智慧。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强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能够懂得他人的人是智慧的,而能够懂得自己的人才是明白的。能够知人不易,能够懂得自己则更难。很多人对他人总是喜欢夸夸其谈,评头论足,好像天下的事情就他最清楚,而自己呢,却从来都不照镜子,不看看自己是啥样,而且也不能容忍人家说自己。如果有人说了,就会很郁闷,会和说他的人过不去。这种人就是只有他说人家,人家不能说他的人,他的心理就是不敢看自己,不敢认识自己,因为他打心底里怕自己被揭示出来,这样的人心里往往是黑暗的,是不敢见光的。真正有智慧的人,他的心是光明磊落的,是明镜一样的,敢于暴露自己,这也就是老子说的“自知之明”的道理。这里的明可以说是智慧的,也可以说是光明正大的,是包容的。
佛家说:人的一切智慧本来就有,只是人没有发现自己,看不清自己的智慧。而修戒、定、慧,就是要让人打开智慧之门,“明心见性”,这里的性,就是本性,人本身具足的一切智慧,这和老子所说的自知之明,也有相通之处了。他们都是强调自我认识的重要性,也就是对人性的认识的重要性。道家修静虚,求无为而无不为,佛家修自性,讲求一切皆空。空和静虚有着某种联系,都在于人对自我的觉察,对自身的一种舍弃,放下自己,融入到无的境界中。无中生有,有中还无,有和无本身就是对立统一的两面,人在寻找有,寻找智慧的时候,却要通过无来寻找,人要“自知者明”,就要知道自己的本性,懂得道的义理,才能够解释自我,懂得自我和自然的关系,懂得空和有的两面。
“自知者明”,要明,只是认识自我还是不够的,还要克服自我,要看到一些看不到的东西,或者是“空”的东西。这个空在哪里,哪里才是空,这需要静虚,静下来,从无中生有,从空中见到自我;而要空,又要不空,就要人克服自我;要戒,要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做到了戒,就是让人走上了正路,克服了一些自欺欺人的魔障,不再对自我的不足感到羞耻,也不会因为自己的一些智慧而飘飘然起来。人要戒,从戒达到一种智慧,大而化无的智慧,知道一切,懂得所有,却又明白,一切的另一面是更大的世界,是自己的无知。在境界高的人,在懂得“自知之明”的心中,智慧自然而然地存在,他们不会因为有而骄,也不因为无而气馁,有无对他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看见了自己,明白内心中的平淡、平等,还有平静。老子说“不争”,“夫唯不争,天下莫能与之争”。那些没有自知之明的人,就是一个争,和自己争,和别人争,和一切争,而实际上,越是去比较,有差别,越是会处在困境中,“差别心”是人最大的不足,让人无法平淡地对待万事万物,也无法平等地对待自我。有差别,就有善恶、美丑、多少、高低,人也就会失去自我,人也就失去了自知之明。
中国有句老话,叫作知足常乐,不知足则不乐,不乐就会生三万六千烦恼。老子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懂得满足就不会被羞辱,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就不会有危险。在军事上有一计叫作“诱敌深入”,或者说“下了套让人来钻”。那些不知道止的人,就容易堕入陷阱,就会被困住,面临危机。“知人者智,自知者明”。那些富有智慧的人,往往是堕入陷阱的人,就好像掉入陷阱的狐狸一样。这些人虽然“智”,却不“明”,无法认识自我,克服自我,如果说认识他人是小智慧,那么认识自我,并克服自我,不为欲念所左右,则需要大智慧、大胸怀。
人要有自知之明,就要努力地克服自己,老子说:“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要清明,要认识事物的真相,就不能光靠眼睛看,还要用心想,心想事成。如果是无心做事,那是很难见到有成功的,这里用心是关键,心放不正,放不开,放不下,都会影响决断,都会让人不明。有句话叫作:“心有多宽,世界有多大。”心要正,就是要平等,不平等的心肯定是放不开的,也是放不下的,要自我克服、要有自知之明,就要平等地对待一切,要将自己放在低处,就好像人仰望太阳,太阳光芒四射,这就是明,自知者明。知人要平等地去看,用心去看,自知要放低,要接受自己,放下自己。老子说:“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身退,天之道。”要懂得功成身退这个道理很难,汉高祖刘邦建立汉朝后,张良知道刘邦可以共患难,却很难共富贵,于是他就离开了刘邦,而那些功名富贵无法舍弃,不懂得“狡兔死,这狗烹”的人则在后来身首异处,其中以“忍辱负重”出名的韩信就是其中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