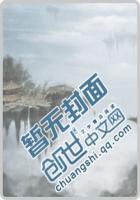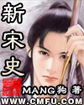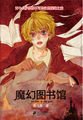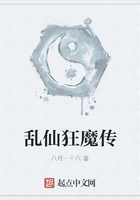汉代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活动,一方面是对先秦风俗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另一方面又为儒家思想熏陶而逐渐呈现出新的面貌。
■神秘主义
秦汉时代在社会风尚方面具有开创意义,但也是对先秦历史的延续。当时社会为“神秘文化”所笼罩,正是上古“巫史文化”的延续,诚如学者所论,“及汉代而巫风更盛”。神秘主义的表现主要有四:一是国家祭祀。当时国家祭祀,主要有郊祀、封禅和明堂祭祀。祭祀的主要对象是天神、人鬼(祖先)、地,其中又以祭天为主。祭祀多杂巫风妖气,郊祀兴盛之时,方士巫师活跃。武帝封禅,听信了方士话语,妄想升仙登天。二是求仙升天。方士们求仙、炼丹药,正是对长生不老的渴求。对生的渴望,对死的畏惧,逐渐形成汉人的生死观念。天界(仙界)、人界(阳间)、冥界(阴间)相通的观念,在墓葬中得以充分表现。汉人崇尚厚葬,特别是贵族官僚的墓室,陪葬品多为日常生活用品,表达出待死如生、冥间享用的观念;墓室中的驱邪镇怪图像、羽化成仙或骑鹿升仙的画面,则表现出对天国的向往。三是民间礼俗迷信。传统的禁忌形式,如选择时日吉凶的活动,依然盛行,为一般民众所普遍接受。四是谶纬盛行。谶纬的内容,不仅仅限于解经述史,更多的是充斥鬼神观念,侧重宣扬神灵怪异、“天人感应”,荒诞不经。
■文娱活动
两汉社会喜闻乐见的文娱活动,主要有蹴鞠、角、围棋、投壶等。蹴鞠,是世界上最早的足球运动,起源于中国。战国时就有,至汉代日渐兴盛,并形成比较完整的竞技活动。当时的“鞠”不是充气的球,而是用皮子裹着毛的实心球。鞠场两端各有6个“鞠域”(球门)仿照弯月形状建造,约有半人高。比赛时,双方各上场12名球员,6个把守鞠域,其余6人在鞠场与对方驰骋争抢。参赛者应遵循比赛规则,裁判人员应公平、公正,不徇私情。对于比赛结果,所有参赛者应“端心平意,莫怨其非”,即不能随便责备同伴或指责裁判员。角最初之时,是角力决胜负的竞技运动,因竞技时两人均是跃跃欲扑之状,又称之为“相扑”。在角的基础上,又产生角戏,或称百戏。角戏规模甚大,成为朝野喜闻乐见的大型文艺体育活动。角戏内容丰富,不仅有角、射箭等项,也有大量的杂技项目,如倒立、走绳索等。围棋和投壶,则是王公大臣、博学儒雅之士喜好的娱乐活动。投壶进行之时,多对酒设乐,歌舞助兴,其乐融融。
■节日习俗
汉民族的传统节日,如除夕、元旦、元宵、寒食、端午、七夕、重阳等,大部分萌芽于先秦时代,汉代则是中国传统节日风俗的定型时期。除夕与元旦,就是延续至今的春节,俗称过年。最初是用祭祀方式庆祝丰年,祈求来年风调雨顺,故有“年节”之称。年俗活动,主要有贴门神、驱傩等。最著名的门神是神荼、郁垒,后世将他们画在桃木板或纸上,置于门旁以驱邪除妖。驱傩,是先秦具有巫术性质的傩祭、傩舞和傩仪的延续,目的是驱除阴气和疫鬼。元旦那天,家长要带着家人祭祀百神和祖先,然后团坐一起,宴饮庆祝。元宵节起源于汉代,最为主要的习俗就是正月十五张灯结彩,人们祈祷、祭奠,以求得祖先神灵的护佑。寒食节在汉代仅有雏形,并没有固定日期,最主要的风俗活动,就是禁火,为了防止寒食冷餐伤身,通常也进行一些体育活动。两汉的端午节及重阳节,巫术宗教色彩浓重,主要目的是祛病禳灾。与之相关的民俗活动,端午节是挂菖蒲、饮菖蒲酒、吃粽子、赛龙舟等,重阳节是佩茱萸、饮菊花酒、登高等。七夕节是在汉代定型的一大节日,牛郎织女的传说对其形成有决定性的影响。每到七夕,人们要看牵牛、织女星,用五色线结“相连爱”,实可视之为情人节的肇端。汉代的节日习俗,具有浓厚的神秘气息,延续先秦以来的驱邪避害思想,也反映出古代中国以农立国的农业文化气息和儒家尊祖敬宗、讲究合和的特点。
■汉代婚姻礼俗
汉是多种文化因素融合的时代,儒家学说逐渐确定主导地位,但是儒家礼制尚未能严格规范所有社会层面。“夫为妻纲”的性别专制格局也还远未定型,妇女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地位,甚至有“妇人尊贵”的说法。其突出表现,便是婚姻礼俗。女性在婚姻上有较多的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择偶,而不是像后代那样由父母包办。后世的贞节观念在当时也十分淡漠,妇女改嫁与再嫁的现象广泛存在,再嫁尤为普遍。寡居的妇女主动择夫,不认为是有失体面;更有甚者,汉家公主可以不讳私夫,天子安之若素,朝野亦司空见惯。武帝的姑母馆陶公主寡居,宠幸董偃,以致武帝尊称他为“主人翁”。光武帝的寡居姐姐湖阳公主甚至在刘秀面前公开表达自己对朝臣的爱慕之心,追求有妇之夫。婚姻离异时采取主动,同样也是汉代妇女的“权利”。西汉名臣朱买臣因为家贫,其妻“求去”,“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当时男子也不以娶寡妇和再嫁之妇为耻,汉初丞相陈平的妻子,据说在嫁给陈平之前已五次守寡;景帝为太子时,纳已经嫁给金玉孙而且生了女儿的妇女为王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