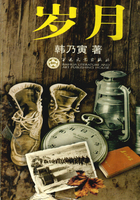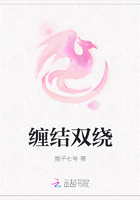很久没有写日记了。
当窗外的树叶因为厚厚的积雪而不堪重负,终于落向冰冷的地面时,莫晓琳似乎打了个冷噤般,脑海里”噌“地一声冒出些许温润酸涩的回忆来。
曾经,母亲便喜欢在有很好天气的冬日,搬把木椅到那吝啬温暖的寒风里,尽可能享受被冷空气尽情剥削后,残留下的那一点阳光的温暖。双手尽管冰凉,也不放弃手中的读物。想必我那爱看读物的毛病也是受了母亲影响罢了。只不过,我却不喜太阳。我宁可蹲在昏暗的炉火旁,也不肯移步到光线明亮的外面的世界里去。
除了怕冷的因素,起决定性作用的,兴许还是我那一颗并不多么光明而充满希冀的心。
无论生活中发生了什么,这一点倒是自始至终都没怎么变过。
于是不怎么乐观的我,很容易对快要失去的东西,或者从来就不属于我的东西失去期望,哪怕是情感也一样,似乎我生来便是一无所有,于是到最后依然一无所有,才是正常的。
“喂,你怎么又在发呆了?这个题怎么回事?‘at’这个介词的用法到底怎样啊?“
坐在桌子对面一脸不耐的张单永远是干扰我静好时光的罪魁祸首。他也在逆客帮忙有一段时间了,磊叔对这个能说会道的家伙很是满意,于是没什么生意的冬季便也准许他偷偷懒了。然而这个家伙,却放着普遍受这个年纪男孩子欢迎的球场网吧电玩城不去,非缠着我给他补习英语,还正气凛然的说绝不白学,用他做好答案的数学卷做交换。
但论谁都知道,抄袭他的卷子那是“自寻死路“。他那及其接近最后答案的答题方式以及95%的答题精确率,放在全校都没几个。所以就算要抄,也只敢抄个没有演算过程的填空和选择,要不然老师一眼就能看出来。但这些题比起后面的问答题却又简易的多了,认真上课了的同学基本都能自己做出来。
而张单这看似最没效果诱惑对于我来说,却又有最佳效果。
我并不擅长心算,有时候要一边用笔演算才能思考出下一步的解题。最重要的是,我很懒。这种不算难、只填个答案还得四处找草稿纸演算的题,我恨不得写个错误答案就推过去。于是我反而更喜欢做问答题。有充足的演算空间,也较符合我喜欢挑战难度的性子。
鉴于和张单的“交易”,就算被干扰了“心灵的平静“我也得忍着。
“'at'的用法有很多,但我不会逐个单一解释给你听,老师上课不是有让记笔记吗,你把笔记拿出来,这个题要用'at'表示地点时的用法来解,要注意和'in'的区分。“
把他的卷子拿过来后发现,他是又犯了语法上的错误,于是一一给他讲解。说到他听不懂的时候,便又是啰啰嗦嗦纠缠个不休了。大多数时候我都会恼了,沉默寡言地把笔记丢给他,让他自己去寻个对错所以然出来。
相反,若是我数学题解不开,基本上他讲解一遍我就懂了。最后证明,他的英语成绩不如我是有道理的。无关聪明与否,努力与否,这是悟性问题。显然,他在数学上的悟性虽高于我,但在英语上,论语感便要输给我了。
常说男孩子比女孩子理性,感性则反而不足。这话是有道理的。大概我俩现在这种互利互进的状态,不是老师们期待的那样,也相差不远了。
我在学校并不怎么与周围的人有接触,更别提一起探讨学习了。不过这种与人交谈的感觉又确实是很奇妙。这让我想起孩提时代与韩欣在一起玩耍的日子,简单而充实。这种交流不同于性情上的了解与磨合,而是各自对这世间丰富而深奥的知识的探索,观念与好奇,就像遇到一个知己一般,两人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互相交流之间则会学到更多。
然而,我喜欢这种交流,却不代表我会是这样一个擅长舌战群雄之人。人生难得的,唯知己而已。而知己当中,可以无话不谈的,又少之又少。
与张单,我只能讲讲学习上的事,与张丽,则多是闲谈,扯不到一块也能继续扯下去的蒜皮小事,与安,我却是什么都可以谈,哪怕是记忆中最痛苦的那一部分。然而,我那一份将了未了的挂念又该与谁谈。
我曾试着与磊叔谈及此事,答案在磊叔的一声叹息里不了了之。
那天磊叔正好进了一批新品种的酒,从外推门而入,大厅玻璃门上的风铃声还在轻轻荡漾,他已经进了吧台后面的隔间,将黑色呢子大衣脱下,挂在了门后样式简单大方的立式衣帽架上,西服外套也被搁置在了书架前的椅背上,然后只着衬衫和毛衣,磊叔在壁炉前的沙发上落座,隔着两米多的距离借着烧着正旺的火光取暖。正在柴火堆里瞎鼓捣的张单咧嘴一笑,“外面好像下雪了。“
“是啊。“屋子里没有开空调,但借着最原始的取暖办法,屋子里还是很暖和的。磊叔稍缓了缓,笑着接话道。他的西装长裤的裤脚在火光的晕烤下有寥寥水雾升起。
这一年夏季生意不错,磊叔便又忙活着,在大厅较空的一角又置办了一架立式空调,还在这小屋里搭了个壁炉。其实不过是比乡下用不起空调的人家冬天里烧的柴火堆多了个看起来很洋气的烟囱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