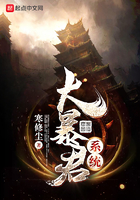何老被枪杀后,尸体在家腾了九天,丧事完全由张玉环一手操持。其间,张大富多次令小儿和自己的孙儿孙女去何家,劝说她回到张家去,甚而自己装病,希望她能回家一次。可张玉环不为所动,且让弟弟传话给父亲说:她现在已经算是何家的人了,公公过世还腾尸在家,婆婆孤苦无依,自己无法分身;如果父亲明理,应当带上兄长及家人,前来何老灵前谢罪,也免日后遭受灭门之灾。张大富此时已得知何奇江在逃,如今听到女儿说出这种话来,真是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却又束手无策,最后终于无法可施,到底还是带着家人,来到何老灵前谢罪,且让儿孙们在何家做了最后三天的孝子。直到这时,张玉环才令发丧。
那些参与谋杀何老的人,而今见张家这种行事态度,真是后悔莫及,纷纷准备逃亡他乡。张玉环得知此事,就出面稳住众人说:“你们事已做残了,逃有什么用,又能逃到哪儿去?不如就在家里,静观事变。奇江没回来,或是回来了没什么作为,那都算了;如果他回来了,并且有一定权势,想要找你们麻烦,到时我一定出面替你们开脱。本来,这事都是我爹造起的,你们不过是受了他的挑唆,如果要担什么罪过,首先得他老人家担。你们还是安心住下来才好。”听了姑娘这番话,人众中除石维义之外虽然大家内心仍是忐忑,但也只好继续住下来,以观其变。
石维义倒不是因为怕死,不敢再在家乡住下去,而是了解了事情的真象后,觉得再也无法与张大富相处,这才决定离开张家坝,搬到长兴屯去住。临走时,他来到何家,拿出张大富送给他的驳壳枪,以及自己分到的两块银元,放置在何老的灵位前面,跪下地来,“咚咚咚”地连嗑三个响头,然后起身对张玉环说:“凶器和银元,我这就交出来了。我并不是怕死,三年后的今天,不要他来找我,我自己会送上门来。”说完,他便立时出门,头也不回地走了。
事情弄到这步田地,张大富真是有苦难言,以至忧患成疾,一病不起。在两年后临终前的几天内,他很想再见一眼两年来一直未曾谋面的女儿,常在迷糊中低呼女儿的名字。于是,家人便多次去何家同小姐商量,求其能再进张家大门一次。可是,去请的人总是劳而无功,张玉环老是托辞,不愿踏出何家院门半步。直到何母实在看不过意,出面说话了,事情才又有了转机。
“玉环啊!当爹的再有不是,总归还是当爹的啊,现在人都快死了,你还记恨什么呢?”何母说话不轻不重。
“妈,我并没记恨什么,只是他们太喜欢讲假话,我担心又弄出什么是非来,所以才不想过去。”
“不会的,这次不会的。听我的话,这次一定要回去看看。不然的话,乡邻们会连我一起都疑成为不明事理的人了。”
“好的,妈,等他们再来喊时,我就同他们一起回去看看。不过,我想让梅花跟我一起去。”
“去吧,应该的。”
其实,何母哪会清楚张玉环的心理?她之所以一直拒绝回家,实际上是在等待她老人家这句话。现在老人金口一开,她就带上吴梅花随着联袂而来的张氏三兄弟,即刻走到了回娘家的路途上。
到得自家门前,想起两年前离家的那天夜晚,再想起事情的种种因果,张玉环不由地悲从中来,还没进到父亲卧室,早已泪水盈眶,当到得父亲病床前,便已声泪俱下了。
“是……是玉……玉环……。”床上躺着的张大富,现在已是血肉全失,只剩一层灰白的薄皮,还包裹着这具佝偻的骨架,虚弱得让人几乎看不见他还有什么呼吸。然而,他头脑倒像是并不糊涂,听到女儿回来的声音,不但口中喃喃自语,而且竟然微扬两只手腕,似乎像是想要让人助他坐立起来。
看到父亲这种状态,张玉环双脚不由自主地跪了下来,哭泣着说:“爹,是……是我,不孝女儿看……看你来了。”
“啊,咳……咳……好,好……”张大富喘息着,在众人的帮助下,后背得以垫高了些,“爹……爹不……不是啊……你……你起来……”
“爹,别说了,只……只求爹能……能体谅女儿……”张玉环从地上立起来,深吸一口气后,又凑近父亲泣说道,“我,我当初那样做……,只是想救奇江一命;现,现在这样做……是,是想救我张家一门啊,爹……”
“爹……爹知……知道,悔……悔不该,当……当初没…..没对你说。”
“爹,你就不要想这么多了,啊,安心养病……女儿,女儿还要求你一件事呢……”
张大富多日不曾落气,就是想见到女儿最后一面,以之求得身后家人生命安全的保证。现在听女儿倒说是有求于自己,他那本已黯褪下去的眼神,忽又现出了一丝光焰。
“梅花现已和女儿结成了姊妹,我想要——要爹多有一个女儿,让她也叫你一声爹。”张玉环已够处心积虑的了。她担心日后何奇江无所作为,自己的兄弟们会找吴梅花的麻烦;又担心何奇江日后有了作为,吴梅花背地里在他身边说张家的坏话。因此来上这一招,让父亲认其为义女,使她两边都挂上关系,将来当不会出什么大的纰漏。
听了女儿的话,张大富闭上眼半晌没出声。大家心里都不免紧张起来。这样过了一会,他终于又微微睁开眼睛,还是带有先前微露出来的那一丝亮光,努力地说:“她……好……做女……”说着,还微微点了点头。
张玉环抓住这个机会,回头对吴梅花说:“我们已是姊妹,现在他老人家同意收你这个女儿,还是当着大家的面,叫他一声爹吧。”
以往,当丫头时的吴梅花面对东家的一屋大小,没有说是不心虚的,如今得老主人认自己为女儿,地位一下子提高了不知多少倍,当然是受宠若惊了。但因处在这种特殊场合,她又不免悲从中来。于是叫了一声爹后,就跪在地上呜咽起来。
吊命多日的张大富,现在一下子说了这许久话,费这么大的神,已到了油枯灯灭的地步。不过,他仍是要说话,就是声音小得要别人把耳朵凑到他口边才听得清:“叫……叫……她起……我……放……”吐出这几个字后,便目光散失,咽下最后一口气。